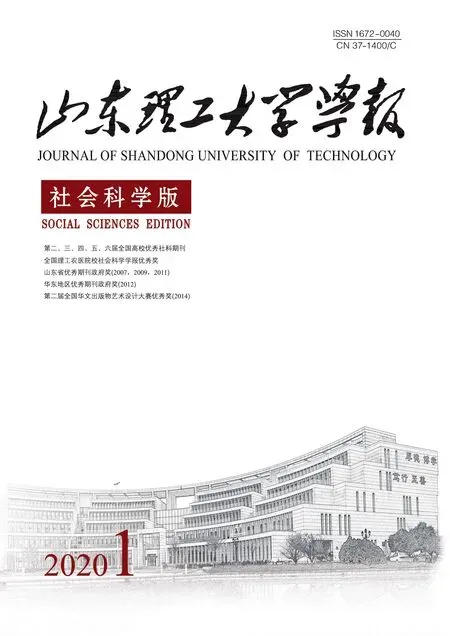“內核與外緣”視閾下中日現代重彩畫比較研究
孫 敬,李心童
一、引言
重彩藝術早在兩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便出現在人類的繪畫中,至今我們仍舊可以在歐洲、西亞、東亞等地見到這些原始洗練的重彩壁畫。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商貿的往來,宗教的傳播、文化藝術的交流也逐漸發達起來,使重彩這種古老的藝術漸漸在世界各地成熟地確立起來。隨著現代思想文化的沖擊以及西方繪畫的不斷影響,中日兩國現代重彩畫的表現形式和審美追求都有所轉變。中國重彩畫要尋求發展的道路,完成現代化的轉型,找到一個有效的參照對象進行自我審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這一點上,同屬東方繪畫體系的日本就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鏡子。
二、中日現代重彩畫的概念界定及其發展脈絡
關于現代重彩的概念界定,有人主張以時間界定,也有人主張以繪畫形態界定。重彩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著名繪畫理論家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書中記有“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吳中之鰾膠,東阿之牛膠。漆姑汁煉煎并為重采郁而用之”[1]。由此可以得出,重彩這一概念是依據所用繪畫顏料的品類而界定的,使用具有覆蓋力的礦物色顏料,或以使用礦物石色顏料為主進行繪制的作品,即為重彩畫。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現代重彩畫脫胎于傳統的工筆重彩畫,也可以說它是傳統工筆重彩畫隨著時代發展變化后呈現出的開放形態。現代重彩的繪畫語言不局限于傳統的勾線填涂,它將寫意畫、沒骨法、“制作”等方法糅合進來,依靠色彩來表現物象,宣泄主體情感。本文研究的現代重彩形態雖不以時間來界定,但也是有時空范圍的限定,按照中日現代重彩畫各自的發展形態,本文將中國現代重彩畫的時間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始點,而日本現代重彩畫則是以明治維新為起始點。中國的重彩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在廣西花山、云南滄源等地的崖壁上;至漢代,重彩已經比較發達繁榮;魏晉南北朝時期,重彩主要吸收了傳入中國的佛教彩繪藝術,尤其在設色方面相較之前有了較大的發展;重彩藝術發展至隋唐一直是中國繪畫的主要形式,此時的重彩人物畫成就是古代人物畫的頂峰,以李思訓、李昭道為代表的金碧山水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唐代的重彩壁畫更是為中國的藝術史添上了濃墨重彩又絢麗奪目的一筆,盛唐之氣魄盡顯其中;重彩花鳥在五代時期發展成熟,可與人物畫、山水畫分庭抗禮;宋元時期先是形成了重彩和水墨齊頭并進的狀況,緊接著水墨一躍而前,成為主流的繪畫形式,重彩則退居其后;進入明清時期之后重彩受到統治者的欣賞獲得一線生機,但也僅僅是得以延續而未完全中斷,依然撼動不了水墨一統天下的局勢。
20世紀以來,由于社會結構、審美觀念、價值標準等因素的變化,中國現代重彩畫在創作觀念、創作方式等方面已然與傳統重彩畫拉開了明顯的距離。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陳獨秀提出,若要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采用洋畫寫實之精神。自此大規模地引進與學習西方的近代文化思潮,力求改變明清以來注重摩古、崇尚水墨的繪畫觀念。80年代的“文化熱”掀起了再一次向西方學習的熱浪,中國畫家重新審視比較中西繪畫,從各個方面思考解讀傳統繪畫。自90年代后半期起,中日美術的頻繁交流與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進入重彩畫的復興時期。時至今日,中國重彩畫依然闊步走在完成現代化轉型的道路上。
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是中國的近鄰,因此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傳統繪畫是受到中國強烈影響而形成的。隨著佛教的東進,重彩這一繪畫形式經由朝鮮半島以及遣唐使的往來渠道傳入日本,在日本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大和繪”。13—16世紀,日本深受中國水墨畫的影響,產生了以雪舟為代表的一大批造詣頗高的南畫畫家,水墨畫風一度盛行于室町時代。17世紀前后,表屋宗達和尾形光琳等人在“大和繪”的基礎上將更具裝飾效果的華麗色彩注入其中,使得日本重彩畫形成了更為鮮明的民族風格特征。狩野派是日本著名的一個宗族畫派,其畫風是在15—19世紀之間發展起來的,長達七代,歷時兩百余年。“從室町時代到江戶時代的狩野派,相當于中國宮廷畫派,比較富麗,是日本水墨畫的另一派風俗水墨畫,它可以說是近代日本畫的前身”[2]。
明治維新伊始西方的藝術理念和技術大量涌入,使日本比中國更早地接觸到西方繪畫的藝術觀念、表現形式和寫實手法。日本民族繪畫在西方藝術的影響下日漸式微,狩野派也在近代風潮的沖擊之下逐漸走向沒落。但在明治維新之后出現了轉機,日本美術復興運動隨之展開。20世紀初,以橫山大觀為代表的日本畫家在傳統狩野派的基礎上吸收印象派的色彩和西方的寫實造型手法,先行一步形成了工筆淡彩、水墨淺絳的現代樣式。二戰之后的日本美術畫壇在重彩“大和繪”這一風格的基礎上,挖掘包括中國敦煌在內的東亞、南亞和西亞重彩壁畫的東方傳統表現潛力,伴隨著觀念的更新和材料的發展,使得重彩畫形式逐漸在日本畫壇居于主流地位并成功完成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使命。
縱觀中日兩國的繪畫史大脈絡,再將其橫向比較后不難看出,同屬東方文化圈的當代中國民族繪畫,有著與日本畫類似的受西方文化沖擊的遭遇。兩者之間不同的是在時間上我國稍后,因而兩國的重彩畫現代進程,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但與此同時,它們在革新的道路上又有所不同。
關于中日兩國現代重彩畫發展軌跡的研究成果大多僅停留在現象表層,鮮少有人追求其背后的深層內因,即便有所提及往往也是寥寥數筆帶過,無法深入剖析造成中日重彩畫現代進程差異的原因,本文將從“內核與外緣”視閾下重新審視中日現代重彩畫的發展軌跡,力求揭示兩者之間異同的內部成因。
三、中日現代重彩畫“內核與外緣”模式的互調
藝術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因此中日重彩畫現代化程度不同的背后實則是兩國整體現代化程度的不同。盛邦和在其著作《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中提出的中心觀點是“內核與外緣”兩重構造論。他在書中指出,世界存在三種主要文化: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工商文化。這三種文化又形成了四個主要的文化區:儒學文化區、佛教文化區、伊斯蘭教文化區、基督教文化區,而每一個文化區又是由“內核”與“外緣”構成,內層核心文化向外輻射,形成文化區的外層邊緣。內核與外緣的殊異造成了文化間的殊異——內核文化是古老的、純種的、自生的文化,外緣文化是年輕的、非純種的、非自生的文化;內核文化具有強大的遺傳傳遞力,而外緣文化則比較便于嫁接新文化,因而實現文化更新比內核文化要輕松快捷得多。在“東亞儒學文化區”內,中國文化屬于古老的內核文化,日本文化則屬于年輕的外緣文化。由于中日兩種文化間的這一差異,使得兩國的重彩畫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早一晚,一快一慢。“文化中心的移動是一個奧秘,而究其實質總是按照一種軌跡作有規律的運行,總是從內核向外緣作滑行轉移,昨日的內核難保‘中心’的地位,今日的外緣必為明日的‘中心’”[3]2。這段話揭示了文化的更新、交替是一種有規律的活動,沒有哪一種文化會保持著永恒的先進性,作為曾經的中心文化會跌落為邊緣文化,而曾經的邊緣文化也會轉化為中心文化。鴉片戰爭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東亞儒學文化區的內部中心逐漸滑移,中國與日本的“核”“緣”位置互相調換。中國失去了內核地位降落為外緣,日本則從外緣位置躍至內核地位,代替中國成為東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新中心”。
英國東方文化研究專家勞倫斯·比尼恩在其代表作《亞洲藝術中人的精神》一書中指出:“日本的藝術史是這樣一部藝術史,它從中國取得了最初的靈感,逐步發展自己的性格,并且接受了新的題材。”[4]同樣,日本學者和畫家中村不折所著的《中國繪畫史》一書中也有類似看法:“西洋繪畫的源頭,是發于希臘羅馬;東洋的繪畫(不含印度方面),以中國大陸為其所生之母。”[5]中日兩國在地理上是隔海相望的近鄰,早在《漢書》中便見關于日本的記載,距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隋唐時期中日來往日益頻繁,在初唐時期,日本便形成了一個“全盤接受中國文化”的局面。至宋元時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高峰期。結合中日兩國美術史我們可以看出,隋唐的重彩畫風傳入日本后發展為“大和繪”,而宋元的文人畫風則掀起日本的“南畫”浪潮。由此可見,在大量接受西方藝術思想之前,日本一直仰望的是中國這片土地。然而日本民族是勤于學習、善于思考的民族,他們會積極地把外民族的先進文化吸收過去,再加以消化。這種寶貴的精神在明治維新后又得到發展,隨著現代文明的進入和日本國內人文環境的變遷,西方現代美術對日本繪畫開始產生重大的影響,日本畫壇終于與中國藝術徹底“絕緣”。自此,東亞儒學文化區的內核與外緣完成對調,過去視中國為楷模的日本,搖身成為中國革新的模板,中國也由原來的文化輸出國成為了文化輸入國。一大批學子赴日學習先進的現代思想文化,在繪畫上,先后便有李叔同、呂鳳子、徐悲鴻、劉海粟、高劍父、高奇峰、傅抱石等藝術家前往日本學藝。
現代化以來,日本繪畫曾兩度陷入危機,第一次是明治維新受到西洋繪畫的強力沖擊致使傳統的日本繪畫走向低迷,而費諾羅薩在明治十五年的演講中抨擊了當時日本美術界出現的盲目崇拜西方的熱潮,直言日本人不應該輕易地放棄自己的傳統繪畫。他的這一演講推動了日本對傳統美術的保護,產生了革新傳統日本繪畫的創造動力。這一時期的日本繪畫與西方現代繪畫之間的矛盾以并存的方式解決,但從總體來看,此時期的日本美術依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無獨有偶,比日本明治維新遲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改革思潮中,康有為等一批有識之士針對中國傳統繪畫的低潮發出改良的吶喊聲。康有為第一次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藝術大師們的杰作時,幾乎被他們的繪畫寫實手法驚呆了,不由得發出感慨:“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國幾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長進耳。”[6]一時間,美術界呈現出了西畫與中國畫并行發展的軌跡。盡管前代學者大都主張學習和借鑒西方繪畫寫實的方法,但是他們并沒有對中國繪畫持全盤否定的態度,更沒有提出以西方繪畫取代中國繪畫的主張,因此中國畫依然拖著沉重的名為傳統的“枷鎖”負重前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繪畫再一次陷入困境。但是屬于戰敗國的日本在恢復、再生的過程中,又一次掀起了現代化的巨大浪潮,再次對傳統文化形成強有力的沖擊。日本美術界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恢復活力,各種美術展覽相繼展開。新舊思想文化在這一時期猛烈碰撞,一時間日本重彩畫受到了激烈的否定。所謂“日本畫滅亡論”“日本畫為第二藝術論”的觀點盛極一時。1948年成立的“創造美術”(后改為創畫會)給當時的畫壇以極大的震動。它以戰后現代思潮為標志,主張解放日本畫的顏料、取材、技巧等方面的限制和畫壇封建性運作習慣。日本畫壇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改良了繪畫材料,拓寬了表現空間。采用天然礦物色結合黏著劑膠來表現的移植并吸收了西畫的造型、色彩及現代主義觀點的厚涂風格的日本重彩畫逐漸發展起來,涌現出像加山又造、東山魁夷、高山辰雄、平山郁夫、市川保道、瀧澤具幸等一大批優秀的現代日本重彩畫家,為日本畫走出了一條現代化之路。與第一次中西文化對沖的潮流相似,中國畫所面臨的第二次沖擊比日本畫晚了四十年。隨著對外開放的節奏加快,加之西方現代文化與藝術思潮來勢洶洶,中國畫再次面臨質疑,20世紀80年代李小山先生的“中國畫窮途末路論”一時間震動了整個中國畫壇。隨著80年代的“文化熱”,在西方現代主義的沖擊之下,中國畫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入了集中的探索期。這促使一部分人將眼光投向了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印象派色彩以及發展迅猛的日本現代重彩畫。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畫家開始注重礦物石色的研究和開發,積極引進日本的顏料生產技術,老一輩的工筆重彩畫家蔣彩萍、王定理等人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近數十年來,也涌現了一大批誠懇的、孜孜不倦的學習日本現代重彩畫的中國畫家,其中像唐秀玲、胡明哲、張導曦、劉新華等都是走在實踐前沿的優秀現代重彩畫家,為中國重彩藝術的復興做出了積極的探索。
中國和日本兩次大規模的思想引進昭示著兩國重彩藝術現代化的相似命運。但在時間上中國卻晚了日本近半個世紀之久,在這明顯的時間差的背后,其實質是兩國對待現代文化接受程度的差異,較之中國而言,日本要更善于學習吸收外來文化,造成此種現象的根源依然是兩國文化的屬性不同。
中日文化由于各自內核文化與外緣文化的特性決定它們在更新過程中出現大相徑庭的歷史命運:前者踉蹌而行;后者步履輕盈,并能夠快速地實現文化更新。盛邦和受生物遺傳理論啟示,認為東方的文化更新的實質意義就是通過“文化嫁接”,改變固有文化形態的一場重大“文化遺傳工程”。那么,影響文化更新的速率及效果的因素便是被更新的文化具有多大的“文化遺傳傳遞力”。遺傳傳遞力的存在使得不同文化的個性得以保存而避免了文化的湮滅。但是當某種文化面臨著更新的重要關頭,這種力量卻成為了阻礙。因此,凡是文化遺傳傳遞力大的文化則出現更新遲滯的特點,反之則出現明顯的“更新便捷性”[3]199。由此,我們可以推出一個結論:即文化遺傳傳遞力弱的那種文化卻具有高強度的“文化更新力”。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古老的、純種的、發育完善的、自生根文化,其文化遺傳傳遞力自然是比日本文化這種年輕的、雜交的、發育不完善的、非自生根文化強出許多;反過來說,就是日本文化的更新能力高于中國文化。至此,我們可以初步了解中國現代重彩畫的發展比日本現代重彩畫遲緩的深層原因。
四、中日重彩畫現代化發展的不同內核及其成因
通過進一步的考察可知,在東亞儒學文化區范圍內,處于內核地位的中國文化是輻射文化,而日本外緣文化則為受容文化。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界中,水往低處流,文化也具有相同特性,即“早進”文化和“晚進”文化。前者比后者要成熟得早一些,后者則因為起步較晚,所以成熟較遲。晚進文化在結構上、系統性等方面都不如早進文化,因此勢必受到早進文化的制約和影響,表現出受輻射性與受容性。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有時候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文化會受到文明程度較低的甚至是野蠻文化的侵襲。所以,文化之間相互輻射是存在的,當高位文化向低位文化輻射時,低位文化也有同時向高位文化輻射的可能。但是,低位文化向高位文化“逆輻射”是微弱的。“許多事實說明日本文化自發源以來一直把吸收外來文化作為自身發展的資本,但反過來說,日本文化給海外諸國以哪些影響呢?……從倭繪屏風輸出并被珍藏于宋徽宗皇帝的御府開始,日本的詩歌、書法、繪畫、工藝、刀劍等不斷傳到中國大陸,令中國人感嘆。日本的畫扇還在朝鮮半島受到青睞。但這些影響都只限于當時,結果是大陸文化的發展似乎沒有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大概以中華自命的中國人沒有攝取作為‘東夷’之一的倭國文化的必要。另外,始終對中國頂禮膜拜的朝鮮擺出同樣的態度也不是不可以理解”[7]。日本著名史學家家永三郎的上述一段話即可表明,總體上說,高位文化總是輻射文化,低位文化總是受容文化。
中國輻射文化與日本受容文化表現出了若干重大性質差異:首先,內核輻射文化具有對外來文化強大的同化力與抵抗力,而外緣受容文化有對外來文化強大的吸收力與消化力。就中日文化關系而言,日本自古以來從中國文化中汲取養分,并通過消化吸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誠如王金林在其《簡明日本古代史》中所說:“日本具有吸收外來文化的特殊能力。他們把他民族的先進文化吸收過去,加以消化,變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不斷地推動著日本歷史的迅速發展。”[8]日本的這一特殊本質與能力在面對西方文明時再次發揮作用,當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亞洲之后,日本是第一個打開國門的國家,積極主動地學習西方先進文明,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跨入了世界列強的行列。這就是日本畫壇為何在二戰后非但沒有長期陷入困境反而蓬勃發展起來的原因,也為日本重彩快速完成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極富生命力的文化環境。其次,內核輻射文化具有強烈的“自我中心”心態與“輻射”心理,而外緣受容文化則具有特殊的以“中空感”為特征的受容文化心理。反映中國人“自我中心”意識的代表學說是“華夏中心說”。與“自我中心”意識相對應的是日本的“自我中空感”。相較于中國,日本的“自我意識”形成較晚。京都大學教授河合隼雄把日本這種獨特的文化形態稱作“中空均衡型”。所謂中空均衡型,就是“允許其他相互的分子同時并存,且能在各種分子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由于‘中空’關系,日本人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東西,而且還不會排斥自己原有的東西”[9]。因此,正是由于這種中空感,日本繪畫在面對西方文化藝術的浪潮時,才能以一種積極學習的姿態兼收并蓄,迅速摸索出一條現代化的道路。
文化的交流與互通,常常按照某種軌跡移動,中日文化之間也遵循著這種規律。中日關系史專家實藤惠秀從留學史的角度出發分析過這個問題,他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中寫道:“中國一直是日本前往留學的國家。……過去日本總是送出留學生的國家,而中國是接受留學生的國家。……現在形勢遞逆,昔日接受留學生的國家變成送出留學生的國家。”[10]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出現過三個高潮,秦代、漢代和唐代,原因在于此時中國文化影響力最強。而作為文化外緣的日本迅速跨入列強行列,完成了近代化;中國文化的輻射力則日益減弱,從內核轉化成了外緣。因此,以繪畫來講,即便許多人的心中仍然抱有大國藝術的姿態,也不可否認中國在日本學習西方繪畫的學子中,有很多畫家在藝術上也沾染了一些東洋繪畫的影子,如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傅抱石等畫家在繪畫上都帶有了一些變革后的日本畫的味道。而中國重彩藝術進入復興期以來,更是有大批學子赴日學習,改良繪畫材料工具、更新繪畫觀念,才使得如今的現代重彩畫發展蒸蒸日上。
從中日現代重彩畫的互動關系看,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國現代重彩畫受到日本現代重彩畫的深遠影響,中國畫家從日本現代重彩畫當中吸收和借鑒的各種藝術元素,深刻地塑造了中國現代重彩畫的藝術形態。中國文化在當代“已成了‘三重疊’外緣文化,即蘇聯東歐、美歐大西洋、亞洲太平洋三大文化同心圓的共同外緣文化”[3]220,這使其在文化更新的過程中出現“三方位受容”的特點。由日本繪畫史可見,古代日本繪畫可以說與中國繪畫同根同源,明治維新后馬上轉向更為新奇的從屬不同體系的西方繪畫。這說明日本在接受文化影響時習慣于單方向受容,因此,日本不論是古代還是當代,其最后形成的文化模式的“歸屬性”色彩總是十分明顯。但中國的受容方式卻不同于日本,這表現在進行三方位復式受容以及形成文化的多元化復式模式。而這種“復式受容”的結果,就是使中國文化區成為世界多種文化交匯激蕩的地區。
五、結語
正如上述所言,當代中國文化的內核地位受到沖擊,而美國、歐洲、亞太作為“三重疊外緣”,成為中國重彩畫發展面臨的現狀。毫無疑問,三大文化都在輻射著中國文化,中國應該采取的態度不是杜絕某方面的輻射,專門選擇其中一方面的輻射,而是使中國的文化受容面朝向三方,如同雷達一般作全方位的旋轉。顯而易見,中國重彩畫想要在這種“復式受容”的環境中徹底完成現代化轉型,就要在繪畫體系更新重建時不絕對偏向于某種外國繪畫形式,而是“揚棄”外來文化,吸收全世界所有的優秀文化藝術養料,同時還要注重對傳統藝術的再挖掘。相信未來的中國重彩畫一定能走出一條不同于日本重彩的具備鮮明獨立性的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