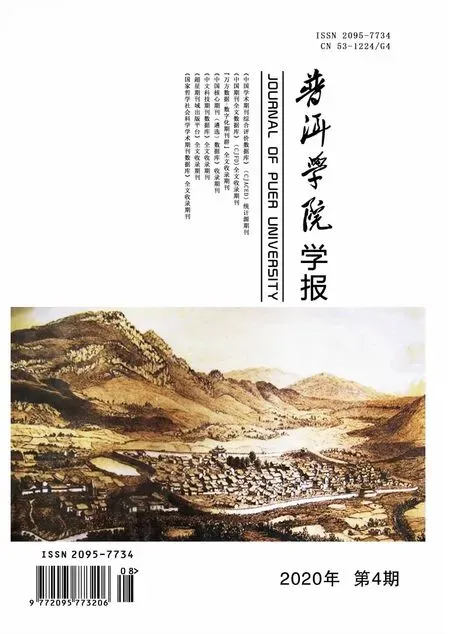明清儒家德性思想研究
宋 麗
玉溪師范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明清儒學家企圖建構一套與正統儒學相異的學說,因此在德性問題上的思考展現出了迥異的風格。我們既可把他們的思想視為儒家德性思想的承繼,也可當作儒家德性思想向近現代社會轉型的開始。對此,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理解。
一、德性形上學的消解
傳統儒學的德性形上學基本都是從天道直貫下來的,如先秦儒學的道器論及宋明理學的理氣論等。首先確立一個絕對先驗的始基,然后以生與被生的關系把先驗本體與經驗世界聯系起來,并指出以先驗本體為代表的“天命”、“天則”是支撐世界的終極法則,也是人安身立命的最終依據。這種德性形上學很容易為人提供一套具有絕對權威性的價值信念,對維護德性價值的普遍性和尊嚴具有積極意義;但過分超越性的表現,也使它極易脫離人性的實際需要,結果成為阻礙人性正常發展的“理障”,如戴震揭露的“以理殺人”現象。因此,明清“異端”思潮都積極地解構這種德性形上學。陳亮說:“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鏈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有其于本質之外,挽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1]!這就明確反對從現實具體事物之外來構建普遍絕對的一般之理。明儒羅欽順說:“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2]。又說:“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2]。理在氣先是宋明理學德性形上學的基本原則。但羅欽順卻認為,理不是一種單獨存在物,而僅是表現在氣化流行過程中的規律。基此,他重新詮釋了一直為宋明理學家津津樂道的“理一分殊”命題。他說:“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3]。在宋明理學家那里,“理一分殊”落腳點主要在“理一”,所謂“分殊”只不過是同一個理在不同情境下的呈現。而羅欽順卻從個別與一般的辨證關系角度來理解“理一分殊”,落腳點放置在“分殊”,所謂“理一”則是蘊涵在具缽事物當中的抽象的普遍本質。這就充分肯定了具體事物獨立的存在價值。如他說:“氣聚而生形,而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于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之者也,若夫天地之萬古如一”[4]。理因物而有,離物則無理,因此具體事物相對抽象的普遍之理具有本然的價值。
明代氣論學派的代表王廷相則進一步取消了普遍之理的存在。他說:“儒者曰:‘太極散而為萬物,萬物各具意義太極。’斯言誤矣。何也?元氣化為萬物,萬物各受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萬萬不齊,謂之各得太極一氣則可,謂之各具一太極則不可。太極元氣混全之稱,萬物不過各具一支耳”[5]。太極是氣的總和,而萬物只是分有氣的一部分而成,因此不能說萬物皆有太極,而應說萬物因分有相互差異的氣而具有不同的本質。退一步說,即便事物原初是相同的,但作為由不斷生滅變化的氣組成,事物彼此的性質也會在未來的發展中產生差異:“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歧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道莫大于天地之化,……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群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6]?道因氣而有,而氣又總是生滅變化的,因此作為氣中之道必然也隨之變化,不存有所謂絕對永恒的道。
王夫之據此提出“氣化日新”的思想。他說:“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視聽同喻,觸覺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也”[7]。天地生滅變化是天地永恒的品質,因此由天地生滅變化而來的萬事萬物其實也是處于不斷“日新”的狀態;至于能夠形成相對一致的認識和理解,主要是由于共同的社會生活所賦予的。人性作為人的根本品質自然也逃脫不了這種“日新”的宿命。王夫之說:“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于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勞勞于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8]。就是說,性即氣化之理,氣不斷地變化,理也隨之變化,人的身心各方面也皆順宇宙大化而日非其故,所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日生日成。可見,王夫之反對將人性視為生而完具的看法,而將其氣化日新的觀念引入了人性論,認為人性是無時無刻不在改變創新之中。他的這種人性思想,不僅否定了自先秦儒學開始就一直提倡的形而上學人性論,也開始把人性問題逐漸引向社會歷史領域。
二、從天理到人欲的轉變
“存天理,滅人欲”是宋明理學最核心的道德命題。它強調道德的至上性、純粹性,但由于極端鄙視人的欲望,導致道德與人欲間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使道德失去感性依據。早在南宋時期,儒學家陳亮就與朱熹進行過一場著名的“王霸義利”爭論。陳亮說:“耳之于聲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與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則必有制之者不可違也”[9]。就是說,人的自然欲望也是人的天性,既然是天性就不可以完全違背。但陳亮并沒有因肯定人的欲望,從而否定道德義理對欲望節制的必要性,只是主張“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10]。明代哲學家羅欽順則說:“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節無節,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縱乎?君子必慎其獨,為是故也”[11]。人性必然包括欲望,所以欲望不可能通過人力強行取消,至多只能對其進行必要節制。他又說:“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系于有節無節爾”[12],欲望不代表著惡,也可以為善,這取決于“有節”與“無節”。但羅欽順依然主張以性制情,在價值序列上性依舊高于情。而明代氣論學派思想家吳廷翰則提出了“性無內外”的觀點。他說:“道無內外,故性無內外。言性者專內而遺外,皆不達一本者也。……以性本天理而無人欲,是性為有外矣。何也?以為人欲交于物而生于外也。然而內本無欲,物安從而交,又安從而生乎”[13]?他反對程朱理學家將天理、人欲二元對立的劃分。認為人欲與人性渾然一體,根本無法簡單區分,性即欲,欲即性。這就充分肯定了人欲本然的價值地位。
明代“異端”的思想家李贄最終提出“私者,人之心也”的命題。他說:“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14]。長期以來,“私心”都是宋明理學家批判的對象,而李贄卻公開承認“私心”的合理性,甚至認為沒有“私心”就沒有人性。更可貴的是,李贄也取消了理學家對“至善”概念的設定,認為善惡必然互為一體:“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即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15]。萬物都是相互對立并存的,而“至善”卻絕對沒有分別,所以也就不存在“至善”,或者說是純粹的虛假概念。這就意味著任何善的行為必然包含惡的因素,或者說惡往往是成就善的必由途徑。
清儒戴震則認為道德原則的完美體現,并不在于凈化人欲:“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16]。道德離不開人欲,人欲本身沒有邪惡,真正的道德就是實現自己欲望的同時,能夠照顧到別人的欲望,最終實現共同欲望。
三、由“德性之知”走向“見聞之知”
從根本上說,“德性之知”代表著對人性的自覺自知,是傳統儒家治學修身的終極目標。但從宋明理學發展理路來看,一般都把“德性之知”作為本然的宇宙精神放置在人性當中,而“見聞之知”往往只起啟發誘導的作用。因此,“德性之知”是宋明理學家闡釋認知論的基點,無論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陽明的“致良知”,還是劉宗周“慎獨”之學,都可清楚地反映這一點。但明清“異端”思想家卻開始改變了這種具有先驗色彩的認知論。王廷相說:“圣賢之所以為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日思慮見聞為有知,不足為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為無知,以為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于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17]。這就把“見聞之知”視為人唯一的認知能力,而把被宋明理學家視作圭臬的“德性之知”斥為禪學“見心明性”之異種。但王廷相并沒有完全否認道德理性的存在:“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于心之愛為仁,出于心之宜為義,出于心之敬為禮,出于心之知為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為之而后成也”[18]。可見,王廷相依然認可仁義禮智等道德理性的存在,只不過把它們建立在“人之知覺運動”基礎上,或者說是人“見聞之知”逐步發展的一種產物。
方以智則把人的認知分為“質測”與“通幾”兩種:前者代表對具體事物的認知,后者則相當于哲學之知或“德性之知”。他說:“考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歷、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19]。“考測天地之家”,即從事具體事物研究的學者,他們從事的工作是“質測”,而“質測”的對象是物理。“宰理”指社會人文之理,其實也從屬于具體事物之理。“通幾”即掌握“所以為物之至理”,即通曉具有普遍性質的哲學之理。關于“質測”與“通幾”的關系,方以智說:“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競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遺物”[20]。作為具體的“質測”之理先天地就內含了“通幾”之理,因此,若想達到對“通幾”之理的理解就必須研究和積累“質測”之理。“言義理,言經濟,言文章,言律歷,言性命,言物理,各各專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數端幾格通之,即性命、生死、鬼神,只一大物理”[21]。可以看出,方以智把關涉“性命、生死、鬼神”等價值之理,當作實證的物理知識來研究。換言之,所謂價值之理只不過是各種具體物理的概括與總結,是作為普遍一般之理蘊涵在具體物理之中。這基本就取消了傳統儒學所提倡的“德性之知”的獨立地位,而使其同化為“見聞之知”。
王夫之也深入地探討了“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內涵與關系。在他來看,“德性之知”就是指:“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萬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于天而即所得以自喻者也”[22]。這說明“德性之知”就是總結天地萬物具體之理后的整體認知,根本離不開對具體事物的理解與認知。因此,就人的認識順序來言,“見聞之知”一定在“德性之知”的前面:“既已為人,則感必因乎其類,目合于色,口合于食,勾非如二氏之愚,欲閉內而滅外,使不得合,則雖圣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覺,但即此而得其理爾”[23]。但這就導致了另外一個問題,即如何保證人從“見聞之知”上升到“德性之知”,而不局限于見聞。戴震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由于心知有“蔽”未能達到“神明”。而“蔽”就是:“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為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也哉”[24]?“蔽”就在于以個人主觀臆斷代替普遍客觀的真理。因此,在認識發展過程中,戴震認為必須不斷去“蔽”。這就基本承認了人具有無限認知的能力。但清儒唐甄沒有延續傳統儒學強調的“見心明性”的反觀思路去闡釋這種“德性之知”,而以“才”這一觀念來構建自己的德性觀。他說:“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于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強于此者。形不為隔,類不為異,險不為阻,天下莫有利于此者。道惟一性,豈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即性之無不能者別謂為才”[25]。所謂“才”即指人改造現實世界的能力,表現在認識上即為把握客觀物理的“見聞之知”。在他來看,“性德”即為“性才”,因為,作為包容萬物的性之德只有通過性之才的努力才能把客觀世界轉變成為“我”的價值世界,無“性才”妄談“具天地萬物”的“性德”毫無實際意義。唐甄又說:“言性必言才者,性居于虛,不見條理,而條理皆由以出。譬諸天道生物無數,即一微草,取其一葉審視之,膚理筋絡亦復無數。物有條理,乃見天道”[26]。天德為虛,必有條理才能顯現,如天道必現于物理一樣。因此,欲知天德必知人倫物理,或者說,天德即為人倫物理的總結與綜合,而這必須借助“性才”才能完成。“智之真體,流蕩充盈,受之方則成方,受之圓則成圓,仁得之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而和同,圣以此而能化,賢以此而能大。其誤者,見智自為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既成,僅能充身華色,不見發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修,皆從智入”[27]。
從根本上說,德的意義在于能創造出現實功用,服務于人的現實生活,這就需要人用智去把握物理、分辨利害,因此,智是德之根本,無智即無德;而這種智,實際上就是把握具體物理的“見聞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