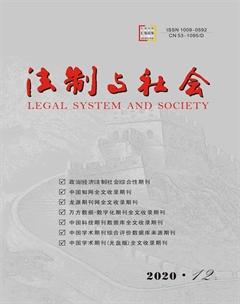“詐賭”后憑欠條軟暴力索債的行為定性
摘 要 準確判斷“詐賭”后憑欠條軟暴力索債的行為定性需將行為分解后再整體考量。首先,通過屆分欺詐性賭博、賭博性詐騙認定“詐賭”本質系名為賭博、實為詐騙,欠條所指向的是虛假債權債務關系而非賭債,后續憑欠條實現虛假債權時才既遂。其次,判斷后續軟暴力索債是否已達足以產生心理恐懼、強制程度以及憑欠條取得錢款須區分行為人實施行為以及被害人交付財物心理來認定構成何罪。行為人實施的整體行為兼具詐騙與威脅恐嚇性質,當被害人同時基于錯誤認識與恐懼心理交付財物時,符合詐騙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最后,綜合分析前后兩部分行為關系系想象競合,應從一重罪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關鍵詞 “詐賭” 欠條 軟暴力索債 詐騙 敲詐勒索
作者簡介:顧霞飛,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研究方向:商法、刑法。
中圖分類號:D92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2.010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詐騙方式手段也不斷更新,其中“詐賭”后憑欠條軟暴力索債的犯罪行為也屢有發生,對此類行為定性在實務中存有爭議,本文試圖以一則案例為切入點,分析此種行為定性的裁判思路。
具體案情如下:被告人許某與馮某合謀以誘騙張某參賭方式騙取張某錢款,許某出資1萬元購買10萬積分百家樂賬戶給馮某并要求其在賭博過程中只輸不贏,后許某在張某操作后謊稱共輸200萬元需分別向許某支付100萬元。許某要求張某寫下78萬元的欠條并制造銀行流水痕跡從而形成虛假債權債務。一個月后,許某等人多次至張某家催討上述錢款,對張某及其家人采用言語威脅、高音喇叭喊話、踢踹鐵門等方式實施恐嚇,期間張某及其家人因不堪滋擾而至親戚家躲避,后其母張某乙被迫還款66萬元。
該案主要爭點在于許某、馮某“詐賭”后憑欠條軟暴力索債的行為定性,存有不同意見,首先,“詐賭”行為屬于賭博還是詐騙性質;其次,后續憑欠條索債取得錢款行為是構成詐騙抑或是敲詐勒索;最后,對于前后兩部分在刑法上是吸收、牽連抑或是競合關系。
現將爭點逐一展開分析如下:
一、“詐賭”后出具欠條的行為認定
(一)“詐賭”的本質系名為賭博、實為詐騙
“詐賭”行為究竟是欺詐性賭博還是賭博性詐騙,須準確屆分兩者的區別。欺詐性賭博還是賭博性詐騙的區別有二。其一是主觀故意要素,前者要求具有營利目的;而后者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二是為取得財物所采用的方式能否實際控制輸贏,前者賭博的輸贏必須取決于偶然事實和個人賭博技藝,即使通過“出老千”等作弊欺詐手段誘惑吸引他人參賭或提高贏率,但輸贏并非行為人所能控制;而后者行為人并非通過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賭博博弈勝負以達營利目的,而系采取形似賭博的方式,偽裝系具有偶然性的賭博從而不法取得他人財物①,即通過暗中串通、弄虛作假實際控制、左右所謂賭局,可以只贏不輸或者以小輸作套誘使大贏,使他人基于“輸”的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②。
該案中許某、馮某事先合謀以誘騙張某參賭、僅以1萬元購買的10萬積分賬戶假裝與張某合樁與對家賭,輸錢后鼓動張某再玩把錢贏回來、假裝向賭博網站老板要賬戶繼續賭博,在張某參與操作后謊稱二人共“輸”200萬元需分別向許某支付100萬元的方式騙取張某錢款。從始至終其二人主觀目的是通過欺詐手段非法占有張某錢款,且系事先共謀、暗中串通、弄虛作假實際控制了所謂“賭博”的輸贏,本質上系詐騙行為,使得被害人陷入“因賭博而輸錢”的錯誤認識。
(二)出具虛假欠條并非詐騙既遂節點
通說認為,財產性利益歸入刑法中的財產罪對象的“財物”概念應限于其內容具有管理可能性、轉移可能性和價值性,行為人取得利益同時導致他人遭受財產損害才行③,債權憑證作為財產性利益之一也首先須符合上述條件,否則不宜認定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欠條作為一種債權憑證,具有證明當事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存在與否的價值,但單憑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欠條并不能同時導致他人遭受財產損害,只有當實施去實現欠條所承載的債權的行為比如討債、訴訟時才能導致他人遭受財產損害,舉輕以明重,那么欠條所指向的債權債務關系是虛假的或者無效的更應如此,并不會因獲得欠條就當然享有財產性利益,占有欠條并不能使得行為人財產得到實質的增加、被害人財產得到實質的減少,須有實現該虛假債權行為。
基于“詐賭”行為,許某要求張某還款并書寫欠條、配合制造銀行流水痕跡形成虛假債權債務。欠條基于被害人被騙陷入錯誤認識形成,雖然被害人誤以為自己在賭博,但欠條所對應的并非賭債,而系虛構的債權債務關系,系基于詐騙不法原因行為導致,亦不具有合法有效性。出具虛假欠條只是詐騙行為一環或者說行為手段,并非詐騙既遂,只有當實現虛假債權且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給付財物導致財產損失時才既遂。
二、后續憑欠條軟暴力索債的行為認定
(一)軟暴力索債方式已達足以產生心理強制程度
“軟暴力”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對他人進行滋擾、糾纏、哄鬧等,足以使他人產生恐懼進而形成心理強制,影響正常生活工作等的違法犯罪手段。④當軟暴力程度達到足以使對方產生心理恐懼或心理強制并符合敲詐勒索其他構罪要件時構成該罪。該案中許某多次電話聯系張某乙稱張某欠款要求還款,后頻繁至張家以“不還錢就打斷張某腳”等言語威脅、高音喇叭喊話、踢踹鐵門等軟暴力方式催討虛假債務,張某乙及其母受驚嚇被迫搬至親屬家暫住,該催討“債務”行為業已威脅到張某乙及其他同住家人的居住和人身安全,足以使張某乙及其家人產生心理恐懼、恐慌,該軟暴力程度已達足以使對方產生心理恐懼及強制程度。
(二)憑欠條索債取得錢款構成詐騙抑或是敲詐勒索
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的關鍵區別有二,一是行為人實施的是詐騙還是威脅恐嚇行為;二是被害人基于被騙陷入錯誤認識還是恐懼心理給付錢款。而實務中往往存在行為人詐騙、威脅恐嚇行為交叉、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或恐懼心理或兼而有之的復雜情況影響犯罪認定。當被害人既陷入認識錯誤又產生恐懼心理進而處分財產的,既符合詐騙罪的構成又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形成兩罪的想象競合。⑤
具體到該案,首先行為人既實施欺騙行為即通過“詐賭”方式誘使與張某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又實施威脅恐嚇行為向張某及親屬施加壓力強索“債務”。其次上門滋擾、威脅恐嚇等軟暴力索債方式已達足以產生心理恐懼及強制程度,張某乙迫于心理恐懼給付錢款;與此同時,許某等人持虛假欠條上門索債,張某等人對于欠條的性質系虛假債務憑證以及形成原因系詐騙系不明知,其等基于恐懼心理的同時又陷入該欠條所指向的債務系“賭債”、系“輸了”的錯誤認識來給付錢款。因此,憑欠條索債取得錢款既符合詐騙罪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騙取財物的構成,又符合敲詐勒索罪使用脅迫手段使被害人或與被害人有密切關系的第三人產生恐懼進而取得財產的構成。
三、前后兩部分行為的關系及罪數評價
對于“詐賭”后出具欠條行為及后續憑欠條軟暴力索債行為在刑法上有何關系以及罪數評價問題,在司法實務中爭議較大。觀點一認為行為人是基于詐騙故意而為的一系列活動,后續憑欠條軟暴力索債應為詐騙行為所吸收,以詐騙罪論處。觀點二認為“詐賭”行為與索債行為系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的牽連,即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的牽連犯,從一重罪以敲詐勒索罪論處。觀點三認為整體行為可評價為系實施了兼具欺騙、威脅恐嚇性質的行為,使被害人基于被騙陷入錯誤認識和恐懼心理給付錢款,同時符合詐騙罪和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應為想象競合,擇一重罪即敲詐勒索罪論處。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吸收犯中前一犯罪行為可能是后一犯罪行為發展的所經階段,后一犯罪行為可能是前一犯罪行為發展的自然結果⑥。本案中軟暴力索債行為并非“詐賭”行為的自然結果,整個詐騙的行為無法涵蓋敲詐勒索行為,兩者作用相當,無法簡單認定吸收關系。其次,牽連犯中牽連關系應具有類型化,即某種手段通常用于實施某種犯罪,或者某種原因行為通常導致某種結果行為⑦。如按此思路理解,采用“詐賭”手段誘使簽欠條的手段行為達到后續威脅恐嚇獲取錢款的目的行為或者說由于“詐賭”簽下虛假欠條的原因行為通常導致軟暴力方式索債的結果行為,然按社會通常理解不具有類型性,“詐賭”簽下虛假欠條的目的是為了讓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自愿”交付財物,而非通過威脅恐嚇手段被迫交付財物,不宜認定牽連關系。最后,“詐賭”行為構成詐騙行為的一部分,當后續憑欠條實現虛假債權即取得錢款時詐騙罪既遂,后續索債被害人亦是在陷入錯誤認識兼恐懼心理的基礎上給付錢款亦為詐騙罪的一部分,但這一整體行為亦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即行為人以基于非法占有被害人錢款的主觀概括故意,通過威脅恐嚇方式使被害人基于恐懼心理給付錢款。綜合看“詐賭”后憑欠條軟暴力索債的整個行為,詐騙過程并非止于詐賭后簽欠條的前半部分行為,而是持續在整個過程,在被告人憑虛假欠條軟暴力索債時,被害人既基于存在“賭債”的錯誤認識又基于恐懼心理給付錢款,并非是詐騙手段行為與敲詐勒索目的行為的牽連犯,而系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的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應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縱觀全文,通過分解“詐賭”后簽署欠條、后續憑欠條索債行為進行分析后整體考量,綜合分析前后行為間的關系,最終得出以敲詐勒索罪論處結論,將復合行為分解后再整體考量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裁判路徑。
注釋:
①②⑤⑦ 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90,1007,1019.
③ 張明楷.財產性利益是詐騙罪的對象[J].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5(03).
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條.
⑥ 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