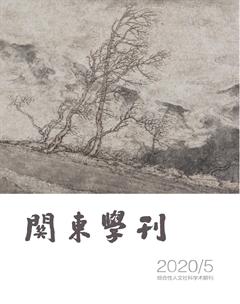新文學發生期舊體詩的歷史考察
[摘要]新文化運動中樹立的以新為貴的價值標準,使得新文學發生以來的舊體詩常處于被遮蔽的狀態,近年學術界對此予以了祛蔽,但成果更多聚集于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若跳出現代學科偏見,以理解之同情的辯證視角審視新文學發生期的舊體詩,則會發現詩歌流派及其個體內質都呈現出了紛繁復雜的狀態。在現代性塑造的社會變遷話語規訓下,舊體詩穩固的結構出現變革的松動,而詩作者雖新猶舊、似舊卻新等復雜多變的文化態度主宰了舊詩的寫作。
[關鍵詞]舊詩流派;文化態度;辯證視角;現代性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基金項目“新詩寫作背景下的舊體詩研究(1917-1927)”(15BZWl77);閩南師范大學校長基金項目“新文學發生期新舊詩學的現代演進研究”(sk19014)。
[作者簡介]周軍(1980),男,文學博士,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漳州363000)。
所謂新文學發生期指向的其實是一個大致的時間范圍,主要是指以胡適、陳獨秀等人引領的新文學風起云涌的歷史時段。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新文學發生期的前后,舊體詩壇的流派也是異彩紛呈,大致而言,有維新詩派、革命詩派、同光體詩派,中晚唐詩派、漢魏六朝詩派等。但這些流派的劃分也往往只是站在舊詩壇的角度來審視舊派文人舊體詩寫作的情形。如果站在新文學發生期的視角來考察舊體詩的細部則會發現,舊體詩的文化守成與現代性語境的渲染,新舊文人并作及新舊文人的交往等諸多文化現象共同構成了色彩斑斕的現代中國詩學風景。應該說,新文學發生期前后時期的舊體詩因詩作者文化意識的流轉,創作出來的舊體詩內質情況也較為復雜,因此,沖破舊有學科劃分的束縛,從文化變遷的歷史立場予以辯證考察就變得很有必要了。
一、上溯下引:時代書寫與文化承襲
毫無疑問,新文學發生前后舊體詩寫作的大本營在舊派文人之中,而詩歌流派在此時期的發展形態顯然為宏觀考察舊體詩提供了便利。從詩歌內質的時代流轉看,開啟舊體詩向現代轉向的當首推維新派的詩歌。可以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邁與灑脫讓維新派詩歌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深深印痕。該派詩人基本上都是那個時代積極向西方學習的士大夫文人,嚴復、康有為、梁啟超成為閃耀的詩人,而黃遵憲、梁啟超等人推動的詩界革命也蔚然成為詩壇一股新的生力軍,并且在新文學發生后仍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革命詩歌領域。該派詩歌有著良好的內在革新意識,詩作中多描寫新事物,輪船、火車、電報、西方政治制度多有涉及。康有為周游外國時就寫下了大量具有異域風情的詩歌,盡管這些詩歌寫作不在新文學發生的時間段,但康有為的影響力決定了其新派風格的詩作在此后很長時間段內都仍然有很多人閱讀與模仿。
第二個流派是因追求民族獨立而崛起的革命派詩歌,也在當時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代表性詩人在民國也多有詩作,他們是章炳麟、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章士釗、劉師培等。當然這一流派的文人大多成為了南社核心力量,尤其是南社專門刊物《南社叢刊》更是刊出了大量舊體詩詞,開民智、移風俗、鼓斗志、宣民主成為南社詩文的主色調。可以說,正是因為承載了反帝反封的革命理想,該派詩人寫作的詩歌從形式到內容較之以往的革命詩歌都有了較大的創新,尤其是現代民族意識大量涌人詩歌寫作中,這是古之詩人所沒有的,南社的革命詩歌將古典詩歌引向了現代文明的多樣化寫作之中。如柳亞子的“何當北伐成功日,畫出放翁團扇妍”,“應為鼓鼙思將帥,北征心愿幾時酬”等詩不僅深具詩史特色,而且在典雅寫作的同時詩人又通俗地將現代革命的心弦波動以革命鼓蕩之勢引人了詩歌之中,所發所感與民族、國家等現代文明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宋詩派在近代詩歌領域影響較為深遠,該派以杜甫、韓愈、黃庭堅等為宗,代表詩人有程恩澤、祁藻、曾國藩、鄭珍、何紹基、莫友芝,后演化出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有陳三立、陳衍、鄭孝胥、沈曾植、沈瑜慶、林旭等。同光派詩歌主張不墨守盛唐,以宋為宗,以新為貴,以奇險為上,提倡文氣與學理相結合的詩歌創作。同光體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表現可圈可點,先是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專門訪問著名舊體詩人陳三立,而直到30年代國際上舉行筆會,邀請中國代表仍有陳三立。學者袁進也指出:“不要說20年代的舊體文學的創作數量大于新文學,1936年,‘英國倫敦舉行筆會,邀請中國代表參加,其時派代表二人,一胡適之,代表新文學,一陳三立,代表舊文學。可見當時舊文學的社會影響。一直到40年代,文言作品依然在報刊和著作中時有出現。”當然,同光體內部又有分別,從整體上說其詩風宗宋。按照錢仲聯先生的劃分,同光體詩人大致分為三派。一派是以陳三立為代表,該詩派主要以南京為活動中心,王瀣、陳隆恪、胡朝梁等皆屬此派。一派是以鄭孝胥、陳衍為代表。該派的活動場所以福州、上海、武漢、北京為中心,沈瑜慶、陳寶琛、林旭、何振岱等屬于此派。以陳衍的詩學來看,陳衍提出三元說,認為不必強分唐宋詩或抑唐糾宋,應該將唐宋詩平等待之,同時注重宋詩對唐詩的突破與創新,所以他說:“余謂詩莫盛于‘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余地耳。”縱觀陳衍詩學,不難發現其變風雅、興詩教、重現實的詩學指向,不過陳衍的詩卻喜歡用典,顯得生澀。最后一派是浙派,代表詩人是沈曾植。該派以北京、武漢、上海為中心,主張沈曾植的“三關說”,袁昶、金蓉鏡、馬浮等屬于此派。當然,宋詩派也隨著同光體詩人內部的糾偏以及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其影響也開始大減。
隨著社會運動的潮落,一些文人陷入思想的沉積期,在詩歌風格上出現了擬古一路,漢魏六朝派就是近代以擬古詩風為特征的詩歌流派,以王閩運、鄧輔綸等為代表人物,高興夔、程頌萬、陳銳亦屬于該派。新文學發生前后該派以王閩運、程頌萬在詩壇的影響較大。王閩運不滿清代宗宋詩的風氣,因此力倡漢魏六朝詩。陳衍認為王闿運的詩“湘綺五言古沉酣于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辯,不必其為湘綺之詩矣。七言古體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諸作,七言絕句則以為本應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為訓,蓋其墨守古法,不隨時代風氣為轉移,雖明之前后七子無以過之也,然其所作于時事有關系者甚多。”可見,即便在文化保守陣營的陳衍看來該派詩歌效法漢魏古風并不值得提倡。
中晚唐詩派作為近代重要的詩派在新文學發生期前后也有很強的影響力,其代表詩人首推樊增祥、易順鼎。該派近中晚唐元白溫李之詩風,作品大多工巧對仗、辭藻華麗、喜用典故,詩作以才氣見稱。但也因其遺老的文化癖好,其詩又顯得詩品格調不高,例如易順鼎的捧角詩與樊增祥的香艷詩均受人詬病。汪辟疆雖對二人有微詞,但他也認為:“實甫才高而累變其體,初為溫李,繼為杜韓,為皮陸,為元白,晚乃為任華,橫放恣肆……樊山胸有智珠,工于隸事,巧于裁對,清新博麗,至老弗衰。”柳亞子在談到自己舊詩寫作時也談及民國詩壇的狀況,在他看來,“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做舊詩的人,大概可分為三派:甲派是王闿運,乙派是鄭孝胥、陳三立,丙派是樊增祥、易順鼎。”可見,在柳亞子心中這幾位在舊體詩詩壇的份量正如上文梳理,他們對舊體詩壇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此外,一些社會賢達在彼時詩壇也是有一定地位的,比如民國四公子:張學良、溥侗、袁克文、張伯駒;成都五老七賢:趙熙、顏楷、駱成驤、方旭、宋育仁、龐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從恩、劉咸滎、曾鑒、吳之英、交龍等等,這些社會賢達在舊詩寫作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詣。比如趙熙,有譽稱“晚清第一詞人”,陳衍比之唐代詩人岑參,夸贊其“詩才敏捷,下筆百十韻或數十首立就。造詣在唐宋之間,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猶人語”,在巴蜀詩人圈中享有很高聲望,汪辟疆視其為西蜀派之領袖。
二、變與不變:社會巨變下的文化書寫
流派的演進會有一個緩慢的過程,但舊體詩詩人的個體寫作則能具體而微地展示時代新變,因此,找尋新文學發生期的舊體詩樣本來考察就很有必要。應該說,晚清以來的舊體詩寫作在新文學發生的十年中仍然得到了延續式發展。持保守主義立場的文人更多保留了舊詩的本色當行,而努力革新民族精神面貌的文人則在引現代性人舊詩方面有了更多的探索,不過,無論舊體詩的“變”或是“不變”都是社會轉型時期文化書寫的寫照。所謂“延續式發展”其實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延續”乃薪火傳承自不待言,而“發展”則表現為兩種詩學路向:其一,晚清以來,新名詞、新事物、新意境已經通過新派詩的大力宣傳進入詩詞寫作,成為具有時代影響力的詩學范式;其二,隨著器物層面的浸染以及西學思想層面影響的深化,現代思想的表達在舊體詩寫作中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尤其是以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為代表的詩作。此外,在此期間后起的詩人,不論舊派還是新派,從其傳統詩學教育背景來說,這些詩人寫作舊體詩的國學根基都較為深厚。舊派文人之間的詩歌酬唱不必多言,即便是新派文人之間也多有舊詩酬唱,例如,即便是新文學發生已經過去十多年以后,周作人五十大壽引發的胡適、劉半農、沈尹默、林語堂等新派文人詩詞唱和在文壇也引發了一場風波。風波另當別論,但新派文人的祝壽唱和選用了舊體詩卻別有一番意味,尤其是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無獨有偶,在新文化運動過去將近十年的1926年,蔡元培寫給胡適的一首詩也是如此,茲錄如下:“何謂人生科學觀,萬般消息系機緣。日星不許夸長壽,飲啄猶堪作預言。道上兒能殺君馬,河干人豈誚庭貊。如君恰是唯心者,愿與歐賢一細論。”應該說,白話文學的興起其實與晚清民初宋詩派的影響有著莫大關系,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從白話詩運動的主將們浸潤于中國文化,諳熟中國古典詩歌這個事實中,從當時盛行宋詩這一背景中,我們應當看到白話詩恰恰與他們反對的中國古典詩歌有某些似反實正的淵源,在這里,我們尤其要拈出的是白話詩運動的精神與宋詩‘以文為詩趨向的微妙關系。”所以,新舊詩之間的界河看起來很是分明,而實際上新舊文人之間的內在聯系實則非常緊密。胡適許多白話新詩的舊詩印痕明顯其實都是在自覺意識的推動下做出的文化選擇。總的來講,舊體詩寫作的時代烙印還是比較強烈的,試觀如下幾首詩:
1917年《紀事》胡漢民
辮子軍來萬象驚,六師不整石頭城。御書有分傳南海,寶璽無緣送北兄。
獨使董公稱健者,誰教殷浩負虛名?求人熏穴何辛苦,自有降王孺子嬰。
1918年《滬江重晤秋枚》黃節
國勢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數人心力能回變?廿載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為棲棲在亂離!
1919年《洞庭舟中感懷》陳隆恪
洞庭波暖草如煙,一夢驚回二十年。慟哭九原傾漢室,煩冤三戶戴秦天。
云心不亂游風外,春色難成落照前。此日君山同寂寞,獨分眉黛下樓船。
1922年《壬戌九日》鄭孝胥
十年幾見海揚塵,猶是登高北望人。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樓何地數星辰。
晚途莫問功名意,往事惟余夢寐親。枉被人稱鄭重九,更豪誼語壓悲辛。
1924年《偶憶湖樓之一夜》俞平伯
出岫云嬌不自持,為風吹上碧玻璃。卷簾愛此朦朧月,畫里青山夢里詩。
1925年《釋疑》聞一多
藝國前途正杳茫,新陳代謝費扶將。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豈堪爭棄馬,補牢端可救亡羊。神舟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萬丈長。
1926年《大雪中寄劉三》沈尹默
漫斟新釀寫新愁,苦憶杭州舊酒樓。欲向劉三問消息,不知風雪幾時休?
1927年《寄映霞》郁達夫
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上面引的幾首詩是從各種詩選中輯錄出來的,寫作或發表時間都在1917—1927年時間段內,如果有挑選標準的話,那就是希望能避開詩壇流派的門戶之見,盡量讓挑選變得具有隨機性。從作者身份來說,既有新文學家聞一多、俞平伯、沈尹默、郁達夫等,也有遺老鄭孝胥、政治家胡漢民、著名教授黃節、社會名流陳隆恪等,這足以說明新文學第一個十年間舊詩寫作的人員具有社會身份多元化與知識背景差異化的特征。而當時時代焦慮的催化,舊詩寫作也多指向了對于國事的關注,而與古代相異的是,“歐風美雨”侵襲下的中國面臨的危機以及時代催發出來的現代社會文明,都不是古代文人所能經歷與體會的。更為重要的一點則是,這些文人士大夫的詩詞寫作都是有感而發。不僅如此,與古人相比,這些文人在進入現代文明之后,獲得了古代文人所沒有的獨立人格,他們可以跳出一朝一姓的喟嘆,獨立地為時代、為現代國家、為普羅大眾而呼喊。胡漢民詩中對于辮子軍張勛復辟的嘲弄,黃節詩中呼喚人們面對亂世要“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為棲棲在亂離!”陳隆恪“慟哭九原傾漢室,煩冤三戶戴秦天”,都深刻折射了當時社會的悲痛現狀以及進入現代文明之后的反思。雖然古代詩歌面對時代變遷也有相應的變化,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所引導的現代性規訓并非古代所能比,所以,新文學發生期的舊體詩在現代性的書寫方面已經跳出了古代意義上的士大夫對王朝與黎民的悲思藩籬。
當然,傳統文人似乎更易發悲秋之聲,新派文人則在“人的文學”中多了一份現代人的精神探索。例如,不論是鄭孝胥的“晚途莫問功名意,往事惟余夢寐親”,還是黃節的“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其悲涼意蘊的深透、沉郁有如姑蘇城外的古鐘之音,但這些音色顯然多了一份詩人的自況;沉溺愛河的郁達夫,其“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則顯現了詩人放達于熱戀之中的自我意識的舒展。俞平伯與沈尹默詩中“卷簾愛此朦朧月,畫里青山夢里詩”以及“欲向劉三問消息,不知風雪幾時休?”彰顯了新文人在新文化意識驅動下,大膽啟用新詞新語,化平民之語于古典詩意之中,用語新奇、格調清新,一下子使得他們的詩歌在新文學發生期的舊體詩中顯得卓爾不群,為新派文人的現代舊體詩實驗書寫提供了新鮮樣本。
上面引述的八首詩體量有限,顯然無法代表整個現代舊詩的風貌,但他們作為時代分子卻擁有折射那個年代舊詩風采的能力。這些新文學發生期的舊體詩一個明顯的特質是,現代性的時代因子讓舊體詩因寫作者的文化立場相異而閃耀出了明顯不同的藝術光芒。舊詩中田園氣息的隱曲表達在現代都市中依然回響,閑適心境的現代文明讓人的意識凸顯出來,現代國家語境下的赤子情懷令人熱血賁張,這一切都仿佛一襲襲華貴的旗袍,風姿綽約挺立于亂世之中。讀此時期的詩就會發現,與西方文化走得近的現代文人,舊詩顯得平實而沉郁,其中現代文明中國家、民族、人的意識得到了彰顯,而舊式文人在現代舊詩中傳達的更多是懷舊情緒與郁結之痛的表達。沈曾植1922年所寫的一首詩中有“年年心緒凋殘盡,念我桓山鳥失群”之句,該詩句化用《孔子家語·顏回》中所敘恒山鳥母子別離之痛,來勾勒詩人身處離亂之際空有一身本領卻無處可用的個人郁悶之語,但這種苦痛何嘗又不是時代之痛隱射在詩人身上的反映呢?當然,悲秋之外,舊體詩又仿佛一貼慰安劑,諸如郁達夫“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之類古詩中的中國經驗,毫無疑問在對抗現代性的單調、乏味時,又為焦慮的國人提供了宏闊的精神后花園。不僅如此,火車輪船等現代文明提供的社會景象,也讓舊體詩多了時代因子的顏色,尤其是革命詩歌在當時的廣泛書寫,為黃遵憲以來的“新詩”寫作帶來了舊體詩的新變可能。例如以柳亞子為首的南社就高舉革命文學大旗聚集了一大批文人知識分子投身民族解放事業。1917-1927年間柳亞子所作的“制禮庖犧邁等倫,耶穌平等宜堪珍”,“勞農革命羅森堡,民族犧牲秋鑒湖”,“各有頭顱要珍重,犧牲來祭自由神”等詩句站在現代文明的角度來看就非常符合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觀,很有舊瓶裝新酒的實驗味道。而從新文學發生的角度看,也很是值得期許的詩歌探索。而同時期汪精衛、郁達夫等有域外風情體驗的詩歌,更是與前文所引的時代弄潮詩歌形成了現代文明的共振,語詞雖是舊的,但有感而發的眼前之境已進入現代文明。
三、以新觀舊:文化態度左右了舊詩寫作
值得重視的是,舊體詩寫作者身份雖是新舊雜陳,但從歷史考察的眼光看,無論寫作者的身份立場如何,所共有的舊體詩框架、規則大致是相同的。但囿于新舊文人之間的歷史門戶之見,研究者又往往因學科藩籬而容易落人諸如新派詩不足觀,遺老詩頑固等老套的新舊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誤區。因此,跳出歷史恩怨與學科偏見,站在現代性的視野去觀照舊體詩就能更為客觀地祛除新文學發生期舊體詩身上的歷史雜塵。應該說,詩人持有的文化態度成為舊體詩特質彰顯的關鍵要素。事實上,即便遺老的詩也未見得就代表守舊,而且他們對新時代的態度并非鐵板一塊。所以,辯證地以理解之同情看待舊體詩寫作者及其詩歌尤為重要。例如在對待新文學的態度上,有些遺老確實比較保守,比如像陳夔龍曾言自己一生可以欣慰的事有三件:“一不聯絡新學家,二不敷衍留學生,三不延納假名士”,這種鮮明的保守態度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有的遺老則與新文學家時有來往,他們往往與新舊派文人都有交游。比如鄭孝胥日記中就有“胡適來訪”“訪胡適,不遇”等多條記載,而且交往的時間就是在新文學發生期的1924年。此后還有高夢旦、徐志摩等與之交游的記載。學者袁進就指出:“‘同光體詩人民國建立后被目為遺老遺少,被視為‘頑固派,其實都是很片面的,‘同光體詩人當年大都是改革者,并不是‘頑固派,他們在文化上大都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并不反對引進西學。”
當然,不容回避的一個問題是,遺老對新文學態度的差異其實也與他們自身對現代文明的隔膜有關,錢鍾書先生的一段回憶文字就證實了這一點:“不是一九三一、就是一九三二年,我在陳衍先生的蘇州胭脂巷住宅里和他長談。陳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學的專科是外國文學,以為準是理工或法政、經濟之類有實用的科目。那一天,他查問明白了,就感慨說:‘文學又何必向外國去學呢!咱們中國文學不就很好么。”不過,寫作舊體詩的文人不論對新文化持何種態度,他們大多對民族危亡之事記掛心懷,以黃節之詩為例,寫于1919年的《春風城南花為麗云作》,本是為佳人所作,但詩中憂患之思就不絕于弦:“世事十載間,滄海幾回異。且如改革初,豈為帝議貳。再造失紀綱,大權落將帥。是非賞罰間,顛倒混淆備。賢豪迥心力,士夫自貪肆。一國在飄搖,與汝共遺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黃節也寫下《書憤》抒發心中悲憤憂思:“危城昏語夜堂堂,輟講程門有去方。不惜此身離亂際,北風猶說第三章。”張中行先生回憶黃節先生在北大課堂為學生講授顧亭林詩文時的情景,當念及亡國之痛的詩句“名王白馬江東去,一片降幡海上來”,黃節仿佛要陪顧亭林痛哭流涕一般,讓在場的學生深受教育與感動。可以說,這種時代之痛的赤子情懷在舊體詩人中是比較普遍的文化共情。比如詩人陳衍是典型的舊派學者、詩人、詩論家,當年與林紓聯名上書與朝廷抗爭《馬關條約》割讓領土之行為,而在其主導《求是報》期間,《求是報》內容涉及中外新聞、中外法律、小說連載并譯介西方科學,其社論針砭時弊,一時風行南北。
事實上,許多文化保守的舊體詩人大多參與社會變革,并且有著投身報業、翻譯界以及支持革命的經歷。“晚清第一詞人”趙熙在袁世凱網羅清廷舊屬之際避居上海,支持熊克武等人討伐袁世凱稱帝,為其提供巨額擔保;“寒廬七子”的詩人易順鼎兩渡臺灣海峽,協助劉永福抗戰保衛寶島臺灣;以林紓、惲鐵樵為代表的翻譯文學直接推動了古老中國的革新。因此,從大巨變的時代背景下來看遺老,其文化心態呈現出了較為復雜的面貌。
因此,很有必要辯證看待遺老的舊詩創作。從某種程度上說,遺老的舊體詩也是現代中國文學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雖然保守是其底色,但是士大夫的情懷卻是他們詩歌吟詠的母題。當然,囿于身份意識的一些束縛,他們中的守舊派一方面對新事物保持戒備,而另一方面又受文化慣性的束縛無法真正接納現代文明。還有一些遺老詩人早年實際上比較有新派作風,可是到了晚年,其詩風卻日趨保守,比如蔣智由就是一個典型。蔣智由早年思想革新、力主變法,也曾與蔡元培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與梁啟超一道創辦《新民叢報》宣揚君主立憲,在詩歌創作上敢于創新,是詩界革命的典范詩人,梁啟超對其評價非常之高:“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云為近世詩界三杰。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云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云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近觀云以其四長篇見貺……讀竟,如粘腸得灑酒,圓滿欣美!”可以說,蔣智由早年的詩充滿了革命氣息,極力頌揚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反抗封建專制的壓迫。可惜辛亥革命之后,他的詩歌開始日趨消沉,走向了封閉與保守,寓居上海的蔣智由最終“墜人”遺老階層,這種由新至舊的變遷恐怕也并非蔣智由一人。康有為亦如此,其詩歌自辛亥革命以至逝世大多成為了“遺老之詩”“復辟之詩”與“清王朝的挽歌”。20世紀20年代康有為在觀看杭州劇團演出《光緒痛史》時,因臺上飾演自己的角色而失態痛苦,其后賦詩十八首。《壬戌年正月十四夜,自滬來杭,道過戲園,有告以今夕演光緒皇帝痛史者,下車觀之。甫入場,即見面扮現老夫冠帶地臺上,觀客指而議論嘆息,不知老夫之在場也。感嘆傷心,口占得十八章記之,后之讀者應有感也》頗值一讀,十八首茲選其一與其三錄下:
其一
君臣魚水庶明良,戊戌維新事可傷。廿五年來忘舊夢,無端傀儡又登場。
其三
猶存痛史懷先帝,更復現身牽老夫。優孟衣冠臺上戲,豈知臺下即真吾。
應該說康有為的組詩非常形象生動地將其復雜的沉痛感受傳達了出來,令讀者不免也產生理解之唏噓。追往昔的輝煌徒增撫今之痛大概也很能代表遺老們的普遍心態——對于前朝的眷念如影隨形!但轉換歷史考察的視角讀遺老舊詩,也許需要用更包容的眼光來看待,畢竟時代變遷讓許多人難以很快就轉換適應過來。尤其在大時局變動之中,一些人階段性歷史任務的終結也意味著被時代拋棄的開啟,原因無他:他們在思想上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繼續革新的節拍,時代發展的阻礙形象也就生成了。康有為就是其中典型:當年推動中華大地維新變法的新派人物,到了晚年卻站到了新文化的對面成為保皇派的中堅。難怪胡適1919年說:“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事實上,這樣的歷史人物還有許多,例如,嚴復當年也是積極呼吁西學以革新中國之士,早年他認為西方強盛在于“言學則先物理而后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而中國的教育“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因此富強之路需棄學詩詞等無用之學。而至晚年嚴復思想出現了大踏步的回轉。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無論遺老對新文化的態度差異有多大,他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西潮涌動的文化浪潮作出的文化反應,實際上也構成了中國詩學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他們寫作的舊體詩更是現代舊體詩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余論
總的來說,在新文學的擠壓之下,舊體詩的創作空間確實出現縮小的趨勢,但需要辯證看待舊體詩“進”“退”的問題。現代傳播的興起并非只對新文學有利,也有論者認為題材的表現出現了很多局限,但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物質景象顯然也觸及了中國人的精神鏡像。新文學發生期,有過良好古典文學功底的作家在小說創作中也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鴛鴦蝴蝶派小說家在其白話小說的寫作中舊體詩也比較多地得到了應用,舊體詩的“自由穿行”不僅在現代白話小說中產生了互文效應,而且還提升了現代小說的審美品格。另外,舊體詩的創作在令中國人驕傲的國畫領域有著獨一無二的契合感,詩畫一體的“詩”多為舊詩,若換新詩配國畫則往往令新詩一籌莫展,畢竟違和感太強烈了。此外,就詩歌形式的革命演化路徑來看,以胡適為代表的新詩誕生經歷了新學詩、新派詩的詩學累積,白話新詩沒有舊體詩詩學的變革累積則無法完成質的飛躍。就文壇變遷而言,無論新派詩人還是新文學詩人如何形成與舊體詩的對峙,以同光體詩人為代表的舊體詩仍然占據著詩壇的正統,柳亞子也曾說過:“辛亥革命總算是成功了,但詩界革命是失敗的。梁任公、譚復生、黃公度、丘滄海、蔣觀云……的新派詩終于打不倒鄭孝胥、陳三立的舊派詩,同光體依然成為詩壇的正統。”此外,舊體詩在詩學特征上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分野,從創作身份上看大學教授、文學團體的新舊色調都會對詩歌異質產生影響,但無論思想層面的新舊差異有多大都很難深層次影響舊體詩的創作。
不容忽視的是,現代傳媒的興起也為舊體詩在新文學發生期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各種新興報刊媒體仍然在刊登舊體詩,而且舊詩話常以連載的形式牽動大眾的閱讀視線,甚至還引發了社會熱議,形成一股文化熱潮,比如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在《甲寅》連載引起的轟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新文化運動在爭取拯救民族危亡以及向西方學習社會思潮助推下,新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開始占據國內文壇以及學術界的顯要位置,而且新的文化價值體系也正逐漸消解舊有的文化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新與舊并非截然對立的價值評判標準,而且白甲午戰爭以后真正純粹的守舊派是不存在的,新文學發生時期寫作舊體詩的遺老,面對西學的態度存在巨大的分化;另一方面,舊文學耆宿在舊有文化心理優勢的前提下占有了大量的大學文化教席以及文化資源,他們或教書育人或潛心學術研究,例如王國維、陳寅恪、汪辟疆、林庚白、黃節、沈曾植等,在舊體詩以及詩學的傳授方面都留下了精深之作,為現代舊體詩的薪火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與此同時,新文學家加入舊體詩寫作的隊伍也為這一文體的延續與發展帶來了現代性的思考與文體更新的動力。而新詩在格律探索以及就格律問題與舊詩學進行的反復爭辯,恰好說明了舊體詩美學的重要性。所以朱自清在給俞平伯《冬夜》所作的序言中就談道:“我們現在要建設新詩底音律,固然應該參考外國詩歌,卻更不能丟掉舊詩、詞、曲。舊詩、詞、曲底音律底美妙處,易為我們理解、采用;而外國詩歌因為語言的睽異,就艱難得多了。”因此不論新詩舊詩,都是中國人的詩歌寫作,二者在讀者接受、審美心理等方面都“暗通款曲”,彼此之間有著詩學的流動。
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顯然,時代之更替誰也無法阻擋,而承接晚清大變革的民國處于新舊文學交替之際,這種不新不舊、不中不西的中間態文學生態使得舊體詩在此階段表現出近乎巋然不動的姿態,但這種姿態在新的時代語境下也出現了松動,正如曹聚仁所言:“時代環境,迫著現代的中國文人,要產生一種新的文體、新的詩體;于是‘舊的詩人在變,新的詩人也在‘變”,所以,無論舊有文化的輻射與傳承力量有多強,舊體詩在強大的現代文明規訓下,內部的分化已經很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