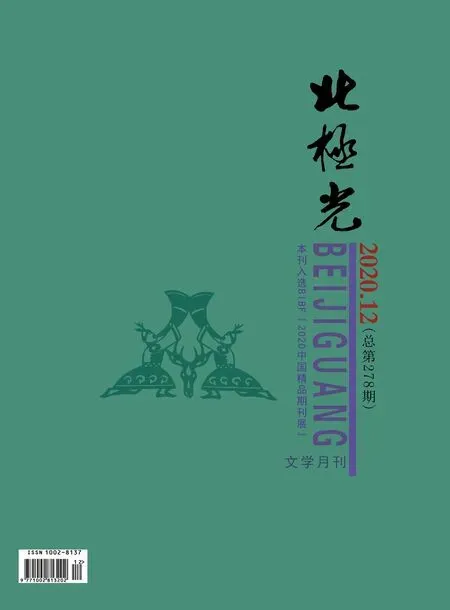晴朗的日子(外一題)
季大洪覺出那兩個男人不正常。
大熱天,那兩個男人,高個的穿著棕色西褲,矮個子穿著牛仔褲,上身穿著夾克衫,拉鏈都拉到了脖子下面。
季大洪真想上前說一聲,你們不熱呀?
但那兩人已經注意到了季大洪,同時看了他一眼,就把目光轉向了別處。
季大洪肚子有些不舒服,出門前喝的那碗涼茶,對他的腸胃發起了攻擊。他看看表,離兒子放學還有十分鐘,應該來得及,就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幼兒園旁邊的公廁走去。幼兒園門口圍著好多家長,他走路的樣子,引起了無數人側目。他早已經習慣了這種目光,挺直了胸脯,旁若無人地從他們面前走了過去。
季大洪從廁所的隔段里走出來時,正好看見那兩個穿外套的男人進來,他們看到季大洪,相互對視了一眼,猶豫了一下,各自走到一個隔段里,面朝里撒起尿來。
季大洪覺得,這兩個人肯定有問題。廁所內,只有他們三個人,靠墻的一長溜小便器都閑著,這兩人卻要到解大便的隔段去撒尿,這太奇怪了。
那兩人從廁所出來后,季大洪便躲到一個角落里,不錯眼珠地盯著他們。
季大洪從小就思維活躍,對周圍的事物比一般人敏感。上高中的時候,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考上警校,畢業后當一名警察。但高考時,他卻落榜了,分數低得讓他喪失了復讀的信心。后來,他應征入伍,當了一名武警戰士。不幸的是,當兵第三年,在一次訓練中,他意外摔折了左腿,是粉碎性的骨折,落下了殘疾,部隊就讓他提前轉業,并把他安排在一家國營企業的傳達室。
幼兒園放學了,一隊隊的孩子在老師的帶領下,有序地走出教室,向大門口走來。
那兩個男人相距兩米左右,漸漸向門口靠近。
不好!季大洪忽然意識到,這兩人極有可能要行兇。前不久,他在報紙上看到,一男子放學時在小學門口行兇,砍傷了多名學生。從那時起,他就時時牽掛在幼兒園的兒子,也許,正是這份牽掛,讓他多了幾分警惕。他左右環顧了一下,看到不遠處一家小超市的門口,堆放著很多木把的拖布,就快步跑過去,選了一個把兒較粗的拿在手里,邊往回走邊把那些布條踩在腳下,用力拽著木把,三五下就將拖布上的布條全部踩了下來。
第一隊孩子走出幼兒園門口時,那兩個男人忽然從衣服里各抽出了一把砍刀,刀刃雪亮,季大洪隔老遠就感覺到了一股寒意。
那兩人揮刀撲向人群!
季大洪大喝了一聲,站住!
那兩人同時回過了頭。
發出喊聲的同時,季大洪的木棍已經朝離他近些的矮個子橫抽了過去,矮個子剛回過頭,木棍就抽到了他的左腦門子上,啪的一聲,木棍斷為兩截,那人晃了晃,眼珠上翻,栽倒在地上。
高個子男人嚎叫了一聲,揮刀向他撲了過來。
季大洪將手中的半截棍子奮力投了過去,趁高個子躲閃,彎腰將矮個子的砍刀撿了起來。
人群已經亂了。家長和老師帶著孩子們四下逃散,哭聲喊聲驚叫聲連成了一片,有人邊跑邊掏出手機報警。
季大洪揮著砍刀,邊抵擋著高個子男人瘋狂的砍殺,邊快速地往后退,慢慢地退出了人群。高個子男人體力大減,動作明顯慢了下來,季大洪瞅準機會,猛然由退變進,上前一步,一刀砍在高個子的右臂上,頓時鮮血飛濺,刀也掉在了地上。季大洪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奮起一腳,踹在高個子的前胸,高個子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矮個子不知何時爬了起來,手里握著一把匕首,跌跌撞撞地向他沖過來。
季大洪剛制服了一個,豪氣頓增,揮刀迎了上去。
忽然,他聽到有人大喊,放下武器!放下刀!
季大洪四下里一看,周圍已經布滿了警察,他沒有停下來,繼續向矮個子走去,他一定要親手將這個家伙制服。
砰!季大洪聽到了一聲槍響,同時感覺左肩被人重重地擊了一拳,身不由己地仰面摔倒在地,砍刀飛起,落在他的胸前,他聽到一個童聲,那是我爸爸!爸爸……同時還有一個聲音在喝叱,是誰開的槍?無邊的黑暗將他包圍起來……
朦朦朧朧中,季大洪感覺到被人抬上了擔架,一個人趴在他的臉上喊,大洪!大洪!你能聽見嗎……他聽出來了,是他的戰友康力寶,他想回答他,卻怎么也發不出聲音,一著急,頭腦一陣迷糊,又昏了過去。
季大洪和康力寶是戰友,關系很好。他受傷回來后的第三年,康力寶也轉業了,被招到了特巡警支隊,當了特警。知道這個消息后,他先是替康力寶高興了一陣,后來,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他們在一起時,無論是射擊、投彈,還是越野、散打,康力寶都是他的手下敗將,而因命運的不同,康力寶現在是國家公務員,特警中隊長,而他只是個門衛。老戰友重逢,兩人都喝了不少酒,后來都有些喝大了,互不服氣,竟然在小區院子里比試起來,結果,仍然是季大洪占上風。康力寶帶他參觀了特警的武器裝備。看到那些槍械,久未摸槍的季大洪,手癢了起來,當特警的欲望更加強烈了,但他知道,以他的條件,這將是一個永遠也無法實現的夢想了。
季大洪從昏迷中清醒過來,是在被推出手術室的時候。一群人圍了上來,有妻子、兒子、康力寶,還有一大堆的警察、記者……
主刀大夫用不容置疑的口氣喊,病人身上的子彈剛剛取出來,失血過多,必須靜養。幾個醫生和護士奮力攔住這些人,不讓他們靠近。
季大洪努力睜開沉重的眼皮,在人群中尋到了兒子和妻子的目光,笑了笑,就閉上了眼。一種從未感受過的累和困,使他很快又沉入了夢境。
季大洪真正清醒過來,是在第二天的早晨。
他睜開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趴在床邊的妻子和兒子,還有在床尾站著的康力寶。他掙扎著想坐起來,左肩的傷口一陣劇痛,不由咧了咧嘴。
旁邊的護士說,您現在千萬不能動,一動就會影響到傷口的愈合。
妻子和兒子的眼睛都是紅腫的,在他昏迷期間,不知道已經哭了多少次。
兒子說,爸爸,你是英雄,為什么警察叔叔開槍打你?
季大洪拿眼睛看康力寶。
康力寶說,我都解釋很多遍了,孩子還是很糾結。
原來,那兩個行兇的歹徒都是剛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出獄后,處處碰壁,事事不順心,覺得活著沒意思,就想借行兇揚名,報復一下社會,然后自殺。警察趕到的時候,季大洪正握著和高個子犯罪嫌疑人相同的刀,叫他放下他不但不聽,反而提著刀向人群奔去,開槍的那個特警以為他要行兇……
最后,康力寶說,你放心,支隊會給你一定的補償,政府還要獎勵你這個見義勇為的英雄……
季大洪說,我沒想過什么獎勵補償,孩子們沒事是最要緊的。
一個月后,康力寶開車來接季大洪出院。
康力寶進了病房,就興沖沖地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支隊要破格特招你為散打格斗教練,打到局里的報告,現在已經批下來了。
真的?季大洪一家三口同時發出了驚喜的疑問。
康力寶點了點頭說,等你的身體完全康復后,就可以去特警支隊報到了。
季大洪站起來,在房間里來回走了幾步說,我這不是已經康復了?我已經沒事了,說完,大踏步地走出了病房。
門外,天氣晴朗,陽光燦爛。
殺牛
收了麥子后,生產隊忙著分糧食,先分口糧,后分工分糧,分完后,余糧全部存放到生產隊的倉庫。這樣忙了幾天后,地里的玉米就半筷子高了,該鋤草間苗了。
鋤草間苗是個累活,主要是累腰,一天下來,收工的時候,大家都邊走邊用鋤把背在后腰上抻腰,這樣能當時舒服一些,但第二天早上,一下炕,還是酸痛不止。
這一天,生產隊的鐘聲響過三遍后,人們才懶洋洋地從四面八方聚到隊辦公室門口,有些人還在用鋤把抻著腰。
不過,人們很快就被一個消息振奮了,隊上的牛病了一只,已經一宿沒有“嚼磨”(反芻)了。
消息很可靠,因為傳播這個消息的,是本村唯一的屠夫“閻老西”。
閻老西說,早上隊長大江問他了,以前只見你殺過豬宰過狗,殺牛行不行?
對呀,殺牛你行不行呀!會不會呀……
人們當即七嘴八舌地問起來。
閻老西得意地哼了哼,用手做了個砍殺的動作,然后說,小菜一碟。
正說著,大江開始安排活計了,全村七十多個勞動力,全部去村西的玉米地里鋤草。
大家扛著鋤頭,浩浩蕩蕩地向村西開拔。
今天的陽光很好,社員們的心情也很陽光。天有些熱,但沒有一個喊熱的,大家都是在一種期待中進行勞動的。他們在玉米地里鋤著草,隔一會兒就往西邊的大道上瞅瞅。有時候目光不小心碰在一起,就心照不宣地笑笑。西邊的大道直通公社,大家都在盼著公社畜牧站上來人。牛是生產隊的寶貝,也是公社領導眼里的生產力,平日里,除了大面積的耕地用公社的拖拉機,這耙地、播種、犁地、運肥、運糧等重活兒都得指望牛呢。所以,牛生了病,生產隊不能擅自作主,得經過公社畜牧站核準,寫了屠宰條子才能殺。整整一個上午,大家既盼著畜牧站上來人,又怕來人。去年就有過一次,一頭牛病得不輕,大家眼巴巴地把畜牧站上的人盼來了,沒想到,獸醫小馬來了扒開牛眼看了看,大粗針管子往牛身上一插,不到半天牛就緩了過來,讓大家空歡喜了一場。
不是生產隊的社員們覺悟低,實在是那年月生活太清苦,幾個月聞不著肉味兒,還有很多人家里早就斷了油。好不容易有了這么一個解饞的指望。
中午收工的時候,公社畜牧站到底是來了兩個人,一老一少,一前一后,騎著大金鹿自行車。大家都認得,老的是站長老于,少的是獸醫小馬。社員們又驚喜又忐忑,還有的低聲笑罵,這個工夫來,混飯吃哪!
社員們各回各家,該做飯做飯,該吃飯吃飯,吃的是大鍋貼餅子,喝的是玉米粥,有些人家粥里放了紅著,有的沒放。菜就是自家腌的大白蘿卜,家家都一樣。大家極力想把這件事忘了,省得攪得人心亂。
下午上工后,社員們都再也無法“忘記”那件事了。
大江沒來,是會計大牙負責分配活計。大江不來不重要,他可能是在陪畜牧站的人喝酒,可是閻老西也沒來,這就有琢磨了。閻老西是沒資格陪公社領導喝酒的,再有手藝,不過是個屠夫而已。
大家干得都很帶勁兒,計劃干半天的活計,半個下午就完成了。會計大牙便讓大家在地頭坐著歇會兒,他先回村問問隊長是不是收工。沒想到大江騎著他那輛破車子來了,后面跟著畜牧站的老于和小馬,都騎在車子上東倒西歪的,但誰也沒有真的倒下。
大江下了車子,沖老于擺手,走吧走吧,再喝你也不行了!
老于舌頭已經不打彎了,嘟囔著說,記住啊……記住,牛鞭一定給我留著……
大江不耐煩地揮揮手說,記住了,說八百遍了……
看老于和小馬走遠,大江回過頭來,發現所有社員都在看著他。
大江忽然就笑了,說,看什么看,每人再鋤一分地,傍晚回去分牛肉!
社員們“哄”地一聲炸了,幾個年輕的后生尖叫著跳了起來。
這每人鋤一分地,平時磨蹭兩個鐘頭,今天半個鐘點就干完了。
大家有說有笑地趕到隊辦公室門口時,門前的場院上,已經擺滿了一堆堆的牛肉,每堆牛肉上都貼著一張白條子,上面寫著數字。場院的南墻根下,一張牛皮胡亂地堆在那里,旁邊是一攤鮮紅的血水。閻老西忙得滿頭大汗,上身穿的舊“的確良”背心都被汗浸透了,泛著一圈圈的汗堿。他正忙著將一些牛雜碎往各個牛肉堆上勻,一方方大塊的牛肉紅通通的,旁邊放著一小堆牛肚、牛腸、牛肺、牛肝兒,雖然是生的,好多人也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大江喊,閻老西,你把牛皮展開晾晾呀,這樣捂壞了。
閻老西用手背揩了揩臉上的汗說,放心吧,捂不了,展開招蒼蠅。
會計大牙很快做好了紙鬮,然后組織大家按組排隊抓鬮。
大江站到辦公室門前的一塊方石頭上,粗著嗓門吆喝,抓鬮是聽天由命,抓著哪堆是哪堆,誰都不能挑肥撿瘦……
這次社員們配合得出奇的好,平日里分東西時的攀東比西,全都不見了,大家都樂呵呵的。
全生產隊四十多戶,家家分到了牛肉和牛雜碎,都興奮得臉上冒光。有男人吩咐女人回家拿家什的,也有要強的女人,喝叱男人,就知道傻笑,還不回家拿個盆來!
于小玲也端了個瓷盆來了,會計卻不讓她抓鬮。她男人米老師是避雨屯唯一的右派,除了口糧,隊上平時分什么東西都不給她家。避雨屯生產隊共有兩個“四類分子”,除了于小玲家,還有地主分子于長生。每回隊里分東西,于長生家從來不來人。有時是分口糧,應該有他的一份,他家也不來人,每次都是會計或隊長給他送到家去。只有于小玲,分什么她都來,每次都悄悄地來,站在人群外邊,等東西分完了,看到確實沒有她的份,才懨懨地一個人離開。
大牙和隊長忙著分肉,閻老西在隊辦公室的房檐下,用三摞磚呈三叉型支了個簡易的灶,放上了一口十印的大鍋,下面用一些干樹枝點燃了火。然后,他把還帶著好多肉的牛腿骨、大梁骨、肋骨、牛尾巴全扔進了鍋里。
人聲漸漸地稀了,不知不覺中,天已經擦黑了。這時,大鍋里冒出了騰騰熱氣,香氣隔老遠都聞得到。
閻老西的老婆小花過來問,你還回家吃不?
閻老西說,我走了,誰伺候隊長他們?
小花笑嘻嘻地說,那你在這伺候隊長吧,省了家里的一頓。
說畢,提著肉,哼著誰也聽不明白的小調兒走了。
見小花走遠,閻老西對還在一邊站著的于小玲說,你還不回家做飯,三個小崽子還餓著呢。
于小玲看了大江一眼,扭頭走了。
大江望著她的背影說,這個娘們兒,脾氣夠怪的,不過,也真是不容易,唉……
會計大牙和婦女主任米秀芹在門前擺上了一張矮桌子、四只小板凳,把雪亮的汽燈也掛在了門框上。
這工夫,閻老西將一個濕漉漉的尼龍袋子提過來,遞給大江說,隊長,這是那寶貝。
不是給畜牧站的老于嗎?
大江不屑地“呸”了一口說,給他?老子還沒享過這口福呢。
閻老西說,你不是已經答應人家了,人家問你要怎么辦?
米秀芹將話接過去說,這還不容易,就說讓狗吃了!
大江咬牙切齒地在她屁股上狠狠擰了一把說,狗吃了,誰是狗?
米秀芹轉身一腳,踢在大江的下身。
大牙笑著說,還沒喝呢,就掐上了。
這時天已經黑了,社員們已經走光了,幾個人都有些隨便了。
大江提出來一個大塑料桶,倒出了滿滿四碗酒。邊倒邊嘟囔,娘的,中午讓老于這王八蛋喝了不少,前天剛打的一大桶。
四個人坐下喝酒吃肉。肉正熱著,酒是60度的地瓜燒,三口下肚,三個男人全脫了光膀子,豆粒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順著前胸后背往下淌。
米秀芹的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了,貼在了身上,明亮的汽燈下,身體的曲線更加凹凸有致。
大江說,秀芹,你干脆脫了吧,這大晚上的,也沒人看見。
秀芹剜了他一眼說,你不是人哪!
大江說,我又不是沒見過,去年春天你喝多了那次,不讓你脫,你偏要脫……
話沒說完,一塊帶肉的骨頭便堵在了嘴里。
大牙端起碗來,碰了碰閻老西的酒碗說,老閻,咱們什么也沒聽見,我敬你一碗吧,你辛苦了。
閻老西不屑地哼了哼說,敬就敬吧,還說什么辛苦了,弄得自己像個領導。
兩人都端起碗,一仰脖干了。
秀芹對大江說,你好歹也是個隊長,以后少在嘴上耍流氓,我先敬你一碗!
大江一仰脖將酒干了,對閻老西和大牙說,你們聽見了嗎?這可是她自己說的,不讓我在嘴上耍流氓,她要讓我在身體上耍流氓呀!
說完,三個男人一陣壞笑。
秀芹將碗里的酒根兒潑到了大江的臉上,罵道,真不要臉!
一只黑狗湊了過來,圍著那張牛皮轉了幾圈,嗅了半天,最后竟撕扯起來。
畜生!滾!
閻老西罵著,順手從桌子上抓起那把剝皮的尖刀,一揚手甩了過去!
刀正插在狗的屁股上,狗一聲哀鳴,突地跳了一下,落荒而逃!那把刀在狗身上抖了幾抖,掉在了地上。
大江不滿地瞪了閻老西一眼說,如果擱舊社會,你真能當軍閥,對一條狗,也下這種黑手!
閻老西趕緊拿起塑料桶,把大江的碗倒滿,然后再滿上自己的,賠著笑臉說,我是怕它弄壞了牛皮,那也是集體財產哪!我敬您一碗!
說完,先一氣將酒干了,拿起一根牛骨啃起來。
大江斜了他一眼,也一口氣將酒干了。
大牙見大江不高興,也將酒倒得滿滿的,敬了他一碗。
大江因為中午喝了不少,幾碗酒下肚,舌頭就大了,翻來覆去總想說去年春天秀芹脫衣服的事兒,但每次秀芹都不讓他說完。他上了犟勁兒,每次被打斷,總要從頭重新說起,醉態越來越明顯了。
那只狗轉悠了一圈,又回來了,它邊走邊不斷回頭舐自己屁股上的傷口,嘴里嗚嗚咽咽地叫著,極委屈的樣子。
看著那狗又往牛皮那邊湊,閻老西急了,大喊一聲,畜生!
那狗竟聽懂了般,回過身來,邊搖著尾巴,邊湊了過來。
閻老西將手里的骨頭扔給它,那狗飛快地叼起來,向遠處跑去。
桶里的酒喝光了,幾個人都有些暈了。大江反而比剛才清醒了些,他搖搖晃晃地進了辦公室,拿出一個尼龍袋子來。然后,他徑直走向大鍋,把鍋里的骨頭一塊一塊地撈了出來,撈了多半袋子。他把袋子提在手上,嘴里嘟囔著,散了吧,散了吧,明天一早還下地呢……晃悠著走了。一陣風吹來,從大江的方向飄過一縷奇異的香味兒。
大牙醉眼矇眬地說,當隊長就是好,一個人吃肉,全家管飽。
沖兩人擺擺手,也搖搖晃晃地走了。
秀芹站起來,親切地問,老閻,還用我幫你收拾嗎?
閻老西大度地擺擺手說,你回家睡吧,炕上有人等著呢。
秀芹也不計較,拍了拍閻老西的肩膀說,那可辛苦你了老閻,今年的先進我投你一票。
閻老西把桌子平端起來,連同桌子上的盤子、碗筷、牛骨頭,一塊兒端進了隊辦公室,又把幾個小板凳也扔了進去,然后將門鎖了。
他把那張堆在一起的牛皮抻開,露出一塊足有十斤的牛肉塊。他雙手將牛肉塊捧起來,小聲說,出來吧!
于小玲從黑暗中走了出來,雙手端著那只瓷盆。
閻老西將肉放到她的瓷盆里。
于小玲剛想說什么,閻老西說,快走,我可什么都沒做,今晚也沒見過你。
他叔,難為你了……
于小玲的淚一下就盈滿了眼眶,明亮的汽燈下,晶瑩的淚珠閃閃發光。
閻老西看也不看她,到門框上取了汽燈,晃晃悠悠地向家走去。
夜已經深了,也有些涼了。村子里一片漆黑,閻老西提著汽燈行走在街上,引來了一片狗叫聲。
一只狗忽地從黑暗中竄了出來,嚇得他差點將手里的汽燈丟在地上。那狗卻并不咬他,在他面前搖著尾巴,低低地嗚咽著。他抬頭看了看,已經到了于長生的家門口了。他踢了狗一腳,正想離開,忽然聞到了一股香味兒。那狗忽地撲到大門口,仰起臉,沖大門的上方汪汪直叫。閻老西走近大門口,把汽燈往高處舉了舉,才發現大門上方的橫梁上,掛著一只尼龍袋子。空氣中那股熟悉而奇異的香味兒,更加濃郁了。
院內傳來了開啟屋門的聲音,閻老西放輕了腳步,趕緊離開了。
快到家門口時,閻老西聽到麥秸垛里傳出震耳的鼾聲。他打著燈湊近,見是村長大江扎在麥秸堆里,睡得正酣。
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涌上心頭,閻老西忽然很想哭,這時,汽燈的燈光抖了抖,一暗,熄了,滿天的星光隨即灑了下來,他扔了汽燈,撲倒在大江身邊的麥秸里,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