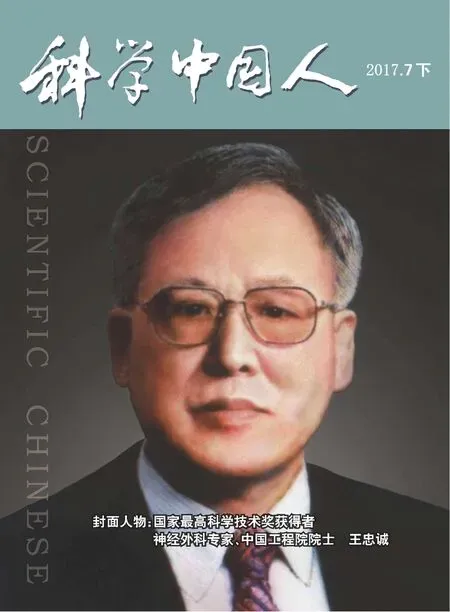宇宙星河 心之所向
——記廣西大學廣西數學研究中心教授張曉
肖貞林
1990年4月24日,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用“發現者”號航天飛機將哈勃空間望遠鏡成功發射到太空,使人類對整個世界的探索,包括對地球、對宇宙、對地球與星系之間的關聯,以及對星系的形成、對物質和能量的認識,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彼時,在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工作的張曉一邊體會所學數學知識用在工程上的樂趣,一邊在思考——為什么真正用于工程中的數學,常常不符合數學的嚴格邏輯推理體系?工程中,數學到底是按什么樣的機理起作用的?這些疑問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幾十年。
為了進一步找尋數學王國的奧秘,這位愛思考的青年3年后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人們常說,愛笑的人一般運氣都不會太差,張曉便是如此。他成為一個“幸運兒”,偶然之機得以投在“數學大師”丘成桐門下。自此,宇宙星河任逍遙,快意人生心所向。
以數學的視角看事物本質
馬克思曾說:“一門科學只有當它達到了能夠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發展了。”今天的技術科學,如信息、航天、醫藥、材料、能源、生物、環境等都成功地運用了數學。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張曉開始從事應用數學的研究,“就是用幾何的方法去處理一些工程問題,具體而言是建一些數學模型,編程序在計算機上運行,看和實際的數據是不是擬合得很好”,“到這一步還屬于紙上談兵階段,最終的目標是待數學模型成熟后做出產品,這些產品能有效地用到工程中去”。談及這段工作經歷,張曉表示:“這段實際工作經驗讓我對數學的作用又有了不一般的了解。”從書本的基礎數學到工程應用數學其實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張曉告訴記者,“工程中的應用數學是很神奇的事,有時并不像基礎數學那樣需要去證明一個猜想、解決一個難題,但是當用數學成功解決實際問題時,常常不是用嚴格的數學論證推導出來的,而是根據經驗‘連蒙帶猜’湊出來的。它的難處在于打破數學原來的基礎理論。”既要運用,又要打破,這是充斥在數學理論與應用中的“矛盾”問題。
帶著對知識的渴求,張曉再次走進校園,開啟自己為期3年的求學之旅。這次,他走到了數學物理的交叉路口,想一窺宇宙星河的神秘。這“一眼”便是20多年的漫漫科研之路,這一路走來,他一直覺得,之前學的微分幾何學和理論物理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自然規律。“根”是一樣的。
如果說20多年的科研訓練是打下扎實的基礎,那在數學知識的基礎之上,讓他覺得更重要的則是數學研究的思維方式。

張曉(左4)與學生合影
人們常說,數學作為現代理性文化的核心,提供了一種包括抽象化、運用符號、建立模型、邏輯分析、推理、計算在內的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維方式,數學促使各門學科的理論知識更加系統化、邏輯化。當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數學家又是怎樣考慮的呢?張曉告訴記者,每個人的數學研究風格都不一樣,習慣也不一樣。一些人可以想出辦法解決很多困難的問題,另一些人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理論體系。
“我自己的習慣是,試圖對每個問題都去想清楚其本質是什么,在大腦里構建一幅圖像,圖像對了,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張曉解釋說,這可能是后來受物理學的影響。物理學家思考問題就經常會構建一些圖像,就像蓋房子一樣,思考怎樣用最少的材料搭好房屋的整體。他坦言,這是自己學生時代學到的數學研究的方法。
從當初相對閉塞的科研環境到如今國際、國內學術交流已成常態,時間轉眼已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對現代數學的理解和認知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張曉的足跡也從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輾轉到廣西大學廣西數學研究中心。“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和廣西大學的目的是希望將學校從教學型轉變為科研型。”在數學方面,既要提升廣西地區數學的整體科研、教學水平,又要打開與世界數學界學術交流的大門。
盡管從2019年4月他才來到廣西大學,但按照既定的目標,他一邊推動數學中心建設,一邊組織開展學術活動。目前,已經舉辦了兩個學術會議——2019青年微分幾何論壇和2019幾何分析與雙曲方程國際會議。在第二個會議上,來自劍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很多該領域的國際學者都應邀到場并開展交流。
受到疫情影響,現在很多科研工作都無法正常有序開展。但在他看來,“用自己畢生所學,為數學科研建設添磚加瓦、為學科的發展而貢獻一分力量,都是科研人員必須去承擔的責任”,這項工作還將在未來穩步推進。同時,他也表示,希望通過這些會議為國內數學界優秀青年人才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也希望吸引一些人才落戶廣西大學,為廣西地區的數學科研、教育事業添磚加瓦。
大師的光輝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香港中文大學依山傍海,樹木鳥類繁多,人文氣息濃郁,被譽為全亞洲最美麗的大學校園之一,也是一所亞洲頂尖、享譽國際的公立研究型綜合大學。1993年至1996年間,張曉有幸在此攻讀博士學位,這為他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他對這段經歷深有感慨。
那是1991年臨近圣誕的日子,此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進修的張曉遇到了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先生。當時丘先生在哈佛大學執教,趕巧在休學術年假期間答應為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一門微分幾何的數學課。“他住臺北,每星期都會從臺北飛到香港來講課,就這樣我很幸運地成了他的學生。”這段時期對張曉而言,機會難得,收獲也非常大。很自然,當1993年1月正式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時,丘成桐便成了他的博士生導師。
香港中文大學不像張曉之前的母校復旦大學,系別的規模相對較小,老師才二三十名。“小而精”,這些老師基本上都是香港培養的優秀本科學生,然后在英、美等西方國家獲得博士學位。學校的培養風格也沿襲了英國的體系,博士讀三年。期間,學生的自由度很大,任憑自由思考、研究一些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離開內地去香港留學的學生非常少,特別是當時香港還沒有回到祖國的懷抱,張曉說,在那兒不同專業的內地研究生才10多人。徜徉在靜謐的校園,對年輕的張曉來說是一種享受,更是一個思考的絕妙場地,“那兒比較適合我的個性,我不是特別喜歡熱鬧,喜歡自己靜靜地思考一些問題。我非常喜歡校園的環境”。
“當年的系主任鄭紹遠教授本科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的,他是丘先生本科和研究生的同學。他來中文大學任教前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數學教授,他們兩人都是微分幾何領域的領袖。我同時跟隨了兩位這樣的導師實屬幸運,雖然累但是學到了很多知識。”
近年來,丘成桐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我們學數學不單是要學數學上的基本功夫,物理上的基本功夫也要學,這是在大學時就要學的。力學、電磁學我們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因為物理跟數學這幾十年來的發展越來越接近,很多問題是從物理上提供的。我們假如對這些基本的觀念完全不認得的話,我們看到題目就比不上其他懂得這方面的數學家,能夠很快地融會貫通。”他就是依照這種方法培養學生的,張曉也因此與物理結下不解之緣。
那個年代,丘先生培養學生可以說是耳廝鬢摩的“魔鬼”式訓練。“學期期間,丘先生人在哈佛,就寄給我們一些論文讓我們自學,美國的大學放假了,他就來香港召集我們開討論班。討論班是每天從上午9點開到下午5點,只留午飯的時間,幾乎沒有周末,強度很大。我們幾位研究生一個學期研讀的論文,常常在兩個星期內就在討論班上講完了。然后就是每天晚上研讀新的論文,再在第二天的討論班上報告。丘先生在討論班上隨時提問,我們經常因回答不出而‘掛’黑板。”張曉回憶說。
開研討班是培養學生的慣常做法,但是強度如此之大卻也是不常見的,張曉對這種緊張至今記憶猶新。“我記得那時候丘先生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些問題,都弄不懂的時候,丘先生就讓我們馬上去查資料,為了節約時間,我基本都是跑步來回。”在丘先生的研討班,張曉覺得自己不光學到了很多知識,更重要的是學會了怎么去做數學研究,怎么去尋找一個好的數學問題。“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一直影響著我隨后20年的數學研究乃至整個思想方法。”

2019年微分幾何青年論壇
在廣義相對論延伸的路上行進
愛因斯坦建立廣義相對論的時候,對時空有一個哲學的思考,就是物理規律需要滿足等效原理,同時要能推導出那些在牛頓力學框架下已經成功的結論。廣義相對論的場方程,一百多年來經歷了各種實驗驗證,理論都是和實際吻合的。
很多研究數學的學者對廣義相對論都非常感興趣,數學大師丘成桐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為之著迷。他提到自己曾考慮一個問題,在赤道上有兩個人,分別沿著經線朝北走,一開始他們是相互平行的,但一直走到北極點,他們相遇了。直觀上好像兩個人之間有引力。這實際上就是愛因斯坦將引力與空間彎曲等效的思想。受廣義相對論啟發,丘成桐曾經考慮微分幾何中沒有物質的空間是否會發生彎曲?以及如何把這個問題推廣到復流形上,這導致他完成了卡拉比猜想的證明。緊接著,又解決了廣義相對論的“正質量猜想”(物理學家稱為“正能量猜想”)。
丘成桐的思想來源很大部分來自廣義相對論,作為他的學生,張曉的一個重要發現也建立在廣義相對論領域上。“20世紀70年代末,我的老師丘先生和他的學生證明了正質量猜想。很自然,我念博士時就接觸到了這方面的工作,自己也非常喜歡。從博士開始到現在,一直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他告訴記者,丘先生證明的正質量猜想,是指宇宙的總能量不小于總動量。地球、太陽系、銀河系在移動時也在旋轉,整個宇宙有移動和旋轉兩種效應,分別由總動量和總角動量刻畫。而他最早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在考慮旋轉效應的情況下,證明了宇宙的總能量不小于總動量和總角動量的和。
20年來,沿著這個研究方向,張曉的研究工作還包括證明類光無窮遠的正能量定理并以此給出引力波Bondi能量正性的完整數學證明、證明正宇宙常數正能量定理和證明負宇宙常數正能量定理。使得物理時空正能量問題得以全面了解。
當廣義相對論成功解釋天體現象的時候,有人曾問愛因斯坦,假如你觀測到的現象和你的理論有不同的時候,你會怎么想?愛因斯坦說,“我會替造物者惋惜,居然不懂得用到這樣漂亮的理論。”為什么漂亮呢?因為用了等效原理,同時能夠解釋天體運行的問題。愛因斯坦后來多次講到,數學的美是很重要的,甚至比實踐還要重要。通過思想的實驗,也通過數學的思維,才能夠得出結論。這個過程有思想實驗般的思考,同時要有哲學的思想,還有數學的思維。這一路走來,張曉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很好地詮釋了這一研究過程。
仰望“星空”
進入數學界后,張曉了解到國內外數學家在研究的一些數學問題。在他看來,有人要發展一套理論,有人要解決某些難題。但是理論的目標還是希望能解決問題,所以解決重要問題是發展一般理論中很重要的一環。
他談到,理論物理學家可能都普遍關心怎么把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結合在一塊。量子力學是研究微觀世界的理論,廣義相對論是研究包括宇宙在內的宏觀世界的理論。這兩個理論依賴的數學理論完全不一樣。形象地說,量子力學是代數,廣義相對論是幾何。量子力學的數學語言是無限維空間上的線性代數,廣義相對論的數學語言是微分幾何。
怎么把這兩種理論融合起來?幾十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研究,提出了各種理論,也產生了很多非常困難的數學問題。張曉的另外一項研究也由此展開,從2006年開始,特別是2008年以來,在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引力場論的經典理論與量子理論”的支持下,張曉和代數學家、物理學家一起,應用早年物理學家、數學家發展起來的形變量子化工具,開展了量子空間彎曲理論的研究。他們提出一種量子愛因斯坦場方程并找到了真空場方程的精確解,同時,經過嚴格的數學推導發現與時間無關、不可蒸發的量子黑洞數學模型。
人們都知道,引力是維系宇宙的四種基本物理力之一(還有電磁力、弱核力和強核力),我們生活在地球的引力之中,時時刻刻都在體驗它。從更大的尺度看,引力是宇宙中一切可見結構的“搭建工”,太陽系、銀河系和整個宇宙都離不開引力,而黑洞是廣義相對論特有的宇宙天體。
張曉告訴記者,物理上認為當星體塌縮形成黑洞過程中,巨大的引力將使整個時空產生波動,這樣形成的具波動性質的時空度量,稱為“引力波”。在廣義相對論對引力波的研究中,人們通常都假定宇宙常數為零,這時在弱場近似下對愛因斯坦場方程的分析發現引力波以光速往外傳播。另外,引力波在傳播過程中將攜帶能量,并以引力輻射的形式將能量向外輻射,這是大家認為引力波應該具備的一個重要特征。
1937年,愛因斯坦和羅森首次找到了場方程柱面波精確解。20世紀60年代,英國物理學家Bondi大力推動了引力波的研究,他導出引力波所應該滿足的波形時空度量的一般形式,并定義了Bondi能量,即在光線無窮遠探測到的時空的剩余能量。Bondi證明了Bondi能量是單調遞減的,表示時空經引力波攜帶走的能量越來越多、時空的剩余能量越來越少。理論計算表明引力波非常弱。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曾花巨資探測引力波,終于在2015年9月14日首次探測到了引力波信號。
張曉和同行合作研究了宇宙加速膨脹、宇宙常數為正時的引力波問題,這種情形符合天文觀測數據。他們發現,正宇宙常數Bondi波形時空度量的情況出乎意料,正宇宙常數對光線無窮遠處的時空度量結構產生了非常強的制約,這些制約在宇宙常數為零時并不存在。通常認為光線無窮遠處的數據是能被引力波探測器測量到的,所以需要研究這種制約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值得慶幸的是這種制約并不影響引力波探測中至關重要的Penrose量的性質”,張曉近期的一個研究工作表明。“這時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發生,不知是不是和暗能量有關?”
此外,張曉還對廣義相對論中擬局部質量進行了新的定義。定義擬局部質量是為了理論上測量宇宙有限區域的質量,例如太陽系的質量。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已經給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義,但是至今還沒有一種定義能滿足物理上的所有要求。例如其中一個要求就是要滿足對區域的單調遞增性,區域越大,質量應該越大,否則理論計算出來太陽系的質量就會比太陽的質量小,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我們的定義能滿足物理上的其他要求,雖然現在還不能在數學上證明其單調性,但從定義的物理機理上可看出是單調的,對一些例子的具體計算也表明是對的。”
“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數學上需要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張曉說。
數學是奇妙的,其科學發現也是時間沉淀的智慧,只有鍥而不舍才能探求其中的真諦。對數學的思考是無窮無盡的,張曉的研究還在繼續。他說,自己每天會靜靜地思考這些很奇妙的問題,并且樂在其中。對于張曉來說,這種探求不但是人生的意義,也是人生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