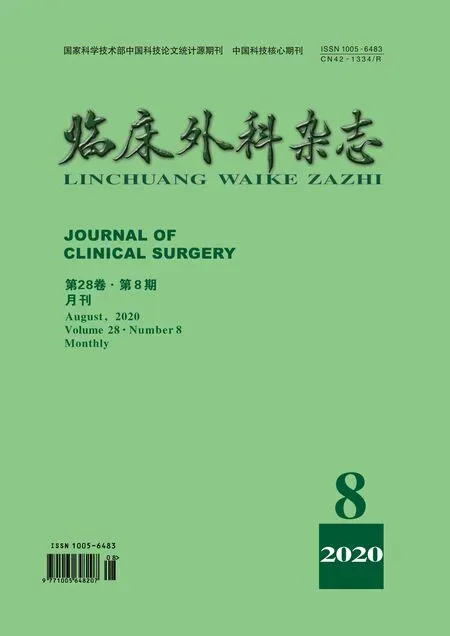腹腔鏡肝門部膽管癌根治術的現狀和爭議
陳勇軍
腹腔鏡肝門部膽管癌根治術(laparoscopic radical hilar cholangiocarcinomectomy,LRHC)是腹腔鏡技術在肝膽外科應用的拓展,主要由中國醫生開創和發展。由于手術復雜性和HCCA預后不良的現狀,使得LRHC極富挑戰并充滿爭議。焦點集中在LRHC的適應證、安全性、根治性以及開展的價值。本文針對上述問題,對LRHC現狀和關注點進行述評。
一、LRHC現狀
腹腔鏡技術對于肝門部膽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HCCA),最早用于術中探查和腫瘤分期。LRHC始于2000年的中國學者,國際認可的第一篇報道是吉林省前衛醫院的陳德興醫生,他于2003年報道了36例病例,包塊17例BismuthⅠ型和19例Ⅱ 型[1],其后文獻逐漸增多,手術適應證從Bismuth Ⅰ型、Ⅱ型擴展至Ⅲ型和Ⅳ型。文獻數據的主要目標在于論證LRHC的安全性和根治性,對比研究非劣于開腹手術。但全部研究均為回顧性小樣本;絕大多數為手術難度較低的選擇病例,選擇偏倚較重;手術者都是大通量膽道外科中心極富經驗的外科醫師;只有陽性結果才能發表的發表偏倚導致在手術時間、術中出血、術后并發癥等參數上優于開腹手術的結果[2]。由于LRHC技術的巨大挑戰性,以及HCCA不理想的預后,爭議和質疑一直伴隨著LRHC發展的整個進程,爭議的焦點是基于LRHC的安全性和根治性的擔憂而引發的開展LRHC的必要性。因此,從技術學和病理學的角度,都如van等[3]評價的一樣,LRHC現階段處于“嬰兒期,Infancy”。
二、LRHC的安全性
盡管對切除范圍和部位還存在分歧,從BismuthⅠ型到Ⅳ型,HCCA現代手術策略都建議聯合肝切除包括全尾葉切除[4]。因此,LRHC術中的安全性主要是對于大體積肝切除的出血控制。肝臟外科腹腔鏡手術主要通過以下三點實現,并證實了具有術中失血少的優點[5]:(1)預切除肝臟入肝血流阻斷:阻斷第一肝門的Pringle Maneuver;阻斷肝上及肝下下腔靜脈,也稱無血切肝術;半肝入肝血流阻斷,也稱Half-Pringle Maneuver,半肝入肝出肝血流阻斷;肝下下腔靜脈聯合半肝血流阻斷技術(陳孝平院士的改良入肝血流阻斷)等;(2)控制性低中心靜脈壓;(3)入肝出肝血管的解剖性結扎。腹腔鏡具有放大效應和盲區穿越性,LRHC借鑒腹腔鏡肝臟外科的經驗,有以下優勢:更加清晰地顯露第一、第二和第三肝門;有利于入肝和出肝血管的高選擇性游離;鑒別變異肝動脈、門靜脈和膽管。能充分保障手術的安全性,尤其是全尾葉切除較開腹更加易于實施。
三、LRHC的根治性
陰性膽管切緣和淋巴結轉移分別是HCCA預后的獨立危險因子[6]。關于陰性膽管切緣,爭議認為由于腹腔鏡手術缺乏觸感,從而導致陽性切緣率增高。但是現代外科理念更加強調“精于術前,嚴于術中”,應該在術前利用各種評估手段,如增強磁共振聯合灌注成像、彌散成像能很好地評估腫瘤縱向浸潤長度和橫向深度;術前通過3D重建規劃手術方案;術中腹腔鏡超聲、切緣的快速冰凍切片病理檢查,以精確的客觀判定代替手術醫生的主觀判斷。
HCCA的淋巴結轉移率約為27.1%~42.7%,淋巴結切除的數目和轉移狀態對HCCA預后至關重要[7]。常規淋巴結清掃的范圍包括肝門區、肝十二指腸韌帶、肝總動脈周圍以及胰頭后的淋巴結(12組、8組、9組、13組)。有學者提出擴大淋巴結切除術(14和16組),以解決腹腔鏡下缺乏觸覺難以確定淋巴結是否受侵犯的主張[8],這種觀念尚在循證探索之中并存在爭議。對于第二站如13、9組淋巴結陽性者,可以擴大至14、16組,以決定手術方案是否需要更改。已經發表的數據顯示,腹腔鏡和開腹HCCA根治術的淋巴結切除數目和檢出率無差異。腹腔鏡下淋巴結清掃對于常規肝十二指腸韌帶內的淋巴結清掃和“骨骼化”不是難點,而對于胰腺后緣及腹腔干淋巴結清掃比開腹更具有優勢。
四、腹腔播散和穿刺孔種植轉移
由于肝門部的狹窄解剖位置,手術中很難達到no-touch標準;超聲刀使用過程的汽化作用;術中氣腹高濃度CO2環境的促腫瘤細胞生長效應,是否導致腹腔播散和穿刺孔種植轉移備受關注。目前在LRHC中的報道極少,僅有Yu等[10]在2011年報道了2例穿刺孔種植[9]。異見者的觀念主要來自膽道的另外一種腫瘤,膽囊癌中2000年之后仍高于10%,從而也佐證了這個擔憂。但是應該認識到,肝門部膽管癌屬于富纖維腫瘤,較之肝細胞癌,膽囊癌,脫落幾率小;超聲刀在汽化的同時,也具有熱殺效應;同時在手術中,不應該偏執于整塊切除而導致含有腫瘤的標本在腹腔內長時間駐留和反復組織摩擦,建議術中預置標本袋,對術中標本進行合理分解后早期納入;另外,采用蒸餾水加化療藥物術中灌洗,從而殺滅部分脫落細胞。
針對該爭議,美國肝外膽管惡性腫瘤聯盟(US extrahepatic biliary malignancy consortium)統計了2000~2015年10家聯盟醫療機構的266例意外膽囊癌手術病例,47例在根治術同時行穿刺孔腹壁組織常規切除,146例未行穿刺孔腹壁組織切除,結果顯示,常規行穿刺孔腹壁組織切除不改變預后;NCCN(2019版)明確提出不推薦常規行穿刺孔腹壁組織切除。這些數據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穿刺孔種植不成為影響腹腔鏡手術根治性的因素[11]。
五、膽腸重建
腹腔鏡下膽道重建的精細操作技術要求極高。現階段,從吻合的質量、用時、術后膽瘺率都劣于開腹手術。根據肝切除部位和范圍不同,保留側肝斷面可能存在多支膽管殘端,常見為2~4支,最多可達8支(中肝切除、擴大左半肝切除,“啞鈴狀”肝切除等)。對于1~3支膽管殘端膽腸重建相對容易,而對于殘端較多、直徑較小的膽管,難度較大。我們認為,對于分散的直徑<1 mm膽管殘端,予以縫扎不予重建;直徑>1 mm者,盡可能通過膽管成形至1~3個殘端,進行分別膽腸吻合或者肝腸吻合法。隨著學習曲線的安全度過、技術積累,腹腔鏡下膽腸吻合技術的“瓶頸”一定能夠被克服。
六、血管切除重建
HCCA的解剖位置毗鄰肝動脈和門靜脈及其分叉,導致肝動脈和門靜脈易受侵犯,主要是肝右動脈,其次是門靜脈右支,而門靜脈主干較少見。對于切除腫瘤同側肝臟及受累血管(如Bismuth Ⅲa侵犯肝右動脈行右半肝切除),不需要血管重建;而對于需要切除右半肝但是左半肝FLR不足,并且PVE失敗者,可以采用左半肝切除+肝右動脈切除重建的策略以獲得R0切除,則需要血管重建,不重建增加肝功能衰竭和肝膿腫的并發癥發生率。腹腔鏡下血管切除技術成熟,但是血管重建尤其是動脈重建是困難的。LRHC中門靜脈楔形切除修補已在多家中心開展, Liu等[12]報道了1例門靜脈切除重建,他們總結腹腔鏡具有良好的視野,利用放大效應可以精確地操作,更好地控制針距和邊緣間距。腹腔鏡下肝動脈切除重建也有學者開展了個例探索,預計在近期會見到相關報道。但總體來講,現階段對于術前評估需要血管重建的HCCA病人,不建議選擇腹腔鏡手術。
七、LRHC適應證
經過20年在關注和爭議中的發展,現階段LRHC適應證包括:(1)病人全身情況對于手術耐受性同開腹肝門部膽管癌根治術;(2)可切除性評估同開腹肝門部膽管癌根治術:如腫瘤侵犯深度未達到預保留側肝臟的二級膽管、足夠的FLR、無腹腔或遠處轉移;(3)不需要肝動脈、門靜脈切除重建;(4)滿足上述條件的各型Bismuth肝門部膽管癌。需要認識到的是,手術適應證是一個動態范疇,隨著整體外科技術的提高,學習曲線的平穩度過,適應證會隨之擴大,如現在被認為禁忌證的血管切除重建也有可能逐步納入適應證。
八、LRHC的優勢和存在的困難
LRHC的優勢主要在3個方面:(1)術中再評估:盡管有多種術前評估手段,但是術前和術中可切除評估誤差仍然高達21%,通過腹腔鏡術中探查和再評估,可以避免不可切除病人開腹創傷和不充分的切除;(2)手術精細性:通過腹腔鏡的放大效應、盲區穿越性,使手術更直觀、精細和安全;(3)微創性:通過手術的精細性,可明顯減輕創傷程度、應激反應和細胞免疫損傷;(4)快速康復:LRHC顯著減輕以疼痛為主要癥狀的術后不適,使病人在加快術后康復(ERAS)上獲益,繼而縮短住院時間使綜合治療時間窗前移。
現階段存在的問題:由于LRHC處于起步期,世界范圍都位于學習曲線中,導致手術時間比開腹手術更長,手術的安全性、根治性以及并發癥在各個中心由于技術偏差存在顯著差異,技術上缺乏統一標準[13]。而關于HCCA術后生存率,應該主要寄希望于對于該病分子生物學的深入研究基礎上的綜合治療策略,腹腔鏡手術只是技術上的拓展,不能承擔對于改善預后的期望。
九、結論
LRHC的挑戰性主要在于技術方面。通過大通量膽道外科中心、有豐富手術經驗的膽道外科醫生在相對選擇性的病例中的實踐證實,LRHC在安全性、根治性具有可行的,并且使病人在術后快速康復(ERAS)方面獲益;但是存在適應證拓展、手術時間縮短,遠期結果有待進一步評估等問題。最有科學價值的RCT研究,由于LRHC技術偏差巨大,難以在多中心開展;單中心研究因為病例數量少的限制,因此需要更大的努力獲得科學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