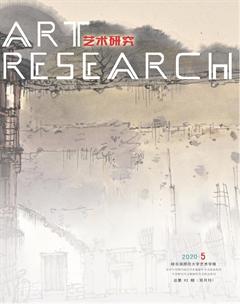魯南民間鼓吹樂班的“開放與堅守”
吳蕾

摘 要:棗莊崔家班因嗩吶吹奏在國內享有盛名,近年來備受學界關注。筆者對樂班一直進行走訪調查,發現其演奏的音樂不僅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時展現出時代文化的變遷。因此,本文通過調查崔家班的生存現狀,試圖探討其音樂文化的變與不變,評述樂班音樂發展現狀的得失,以此為例思考傳統音樂在當代的發展。
關鍵詞:魯南鼓吹樂 崔家班 變遷
幾年前,筆者著手在“嗩吶之鄉”①進行魯南鼓吹樂的考察,在田野調查中認識到,隨著歷史變遷,傳統鼓吹樂班在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為求生存也悄然發生著變化,故本文以魯南鼓吹班——“崔家班”為研究對象,觀察傳統音樂在面臨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飛速發展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壓力之下,其自身是如何調整、變化的,并從中找出其原因所在,通過其傳承、變遷的軌跡,試圖發散開來,審視中國傳統音樂發展的歷史規律。
一、儀式文化背景
1.羊莊鎮概況
滕州是棗莊地區的“平派”嗩吶三大中心之一。羊莊鎮隸屬于棗莊滕州市東南部,相傳因越國大夫范蠡曾隱居此地牧羊,故得此名。面積約128平方公里, 轄89個村,人口8.1萬人。
羊莊,良好的自然條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歷史,為這塊熱土保存了綺麗的邾婁文化和文物古跡。這里有7000年的化姑庵文化遺址,有昌慮故城、陶山經石等名勝古跡;還有西施牧羊、聚寶盆等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和傳說。明朝洪武年間,羊莊已發展成為交通和商業重鎮,物產豐富,經貿活躍,商賈云集。現在的羊莊,交通便利,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十分優越。
2.樂班概況
羊莊鎮共有十余個嗩吶班②,其中最著名的是羊南村“崔家班”鼓吹班。據“崔家班”的“班主”崔懷義老人介紹:“‘崔家班祖輩曾師從‘曹家班,當時“曹家班”已經有四、五輩的歷史,在滕縣(現為滕州市,筆者注)有很大的影響。但‘曹家班后繼無人,‘崔家班就成為了曹家嗩吶班的延續。”③由此可以推斷,如果上溯到“曹家班”,這支嗩吶樂班已有二百余年的傳承歷史。
在魯南民間,婚喪嫁娶都離不開嗩吶班,尤其是喪葬儀式中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當地最為著名的嗩吶班——崔家班,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間重要儀式中。樂班里的樂師們吹拉彈打樣樣拿手,技藝之嫻熟令人嘆服。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民間藝術的重視,崔家班從民間走向專業學院,從民間儀式風俗吹奏走進了錄音棚。1987年,他們受邀到北京錄制專輯、唱片發行到全國;2009年,赴中國音樂學院舉辦了銅桿嗩吶演奏會,并代表魯南“平派”嗩吶錄制音響資料;2013年,在文化部舉辦的“第十屆中國文化藝術節”中國民族器樂民間樂種比賽中,獲非職業組“優秀演奏獎”等。崔家班跨越了傳統文化的圍墻,將棗莊地區的民間鼓吹樂作為區域傳統文化向社會做以傳承和展示。
二、傳統的堅守與順應時代的變遷
筆者在田野中發現,崔家班在樂隊配置、曲目編排和傳承等方面發生變化。
1.樂隊配置的變遷
長期以來,鼓吹樂主要應用場合是婚禮、葬禮。樂班所使用的樂器至今保留了傳統配置,主要以銅桿嗩吶、笙、板胡、號、二胡、笛子和銅鼓等組成,其中嗩吶是主奏樂器。
在當代樂班中,銅桿嗩吶、笙、板胡、號、二胡、笛子和梆子、鈸、鑼打擊樂器等傳統樂器盡管依舊保留,但面對社會發展,人們的審美情趣必然也會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為了順應聽眾的需求,崔家班在保留傳統配置的基礎上,增加了架子鼓、電子琴、木管、薩克斯、長號、小號等西洋樂器,體現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有機融合,新加入的這些樂器多由年輕樂師演奏。葬禮時,傳統樂器與西洋樂器可以混合搭配,一般在演奏傳統曲目時多用傳統樂器,而演奏流行音樂時主奏樂器也兼有嗩吶等傳統樂器的參與;但在婚慶用樂時,樂隊基本保持西洋樂器的配置。
2.表演曲目的變遷
樂班仍保留傳統樂隊的配置是崔家班能夠演奏眾多傳統樂曲的重要因素,樂曲演奏聲音效果也非常豐滿。為與民間儀式程序相配合,演奏傳統樂曲是必不可少的,如葬禮時悲痛欲絕的《哭長城》,婚禮時純樸熱情、民風濃厚的《百鳥朝鳳》等。崔家班因此傳承了較多的傳統樂曲,如《五六五》、《凡調五六五》、《雅調五六五》、《十樣景》、《將軍令》、《天下同》、《清河令》、《老少同音》、《采花歌》、《一支花》、《集賢賓》、《大開門》、《全家福》等。
當代演奏曲目的改變不僅是因為樂器變化,同時是為迎合聽眾的審美需求,與百姓的喜好緊密結合。尤其是多年來創編的一些曲目,融入了對當地生活和民俗的真切感受。早些年根據當時流行的戲曲唱段,創作改編了《朝陽溝》、《七品芝麻官》、《李二嫂改嫁》、《打虎上山》等曲目。《沙家浜》中“智斗”的惟妙惟肖,《朝陽溝》中“上山”的生動逼真在“咔戲”吹奏方式下表現得淋漓盡致。
再者,在這一樂種的發展過程中也可以看到許多新的融合,比如,在喪葬儀式中,演奏流行歌曲仍以吹打的形式表演,曲調也常用嗩吶的滑音、打音、氣頂音等傳統技巧來表現等(在婚慶儀式中則往往用西洋樂器來演奏流行歌曲)。
另外,在傳統樂曲的演奏技巧方面也做了積極探索,例如崔家班在其《百鳥朝鳳》的演奏中,惟妙惟肖模仿了雞叫、蟬鳴以及各種鳥叫聲。崔懷義的《百鳥朝鳳》中還可以模仿獸類的聲音,這些都已經不知不覺突破了傳統的定義。
3.傳承方式的變遷
崔家班以家庭傳承為主兼有收徒。老藝人崔懷義的曾祖父崔鳳錚,師從曹姓師傅,并將吹奏技藝傳授給了其祖父崔寶振,崔寶振傳授給其父崔星海,崔星海傳授給崔懷義。崔懷義現收授徒弟多人。可以說,崔家班最主要的傳承方式就是家傳。當然這里主要指嗩吶演奏傳承,其實對整個崔家班來說亦是如此。目前,都是靠傳統的口傳心授傳承。受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傳男不傳女”的現象筆者覺得還可以從其他方面來思考。如果家族掌握的某項技藝有嚴格的傳承“家規”,也從另一角度表明了它的珍貴性。
樂班現有成員12人,列表如下:
如上所述,崔家班是一個家族性的傳承。誠然,這種謀生手段在曾經很艱難的歲月里讓“老崔家”比其他人家多了一條生路。時至今日,鼓吹,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是作為傳家之寶——凝聚著幾代人的心血。“傳統是一條河流”,在這樣一個傳承嚴密的樂班里,尤其是年長如崔懷義老人,絕不愿意讓祖輩手把手傳下來的鼓吹技藝在自己手中斷送。這其中已不再只是鼓吹技藝的傳承,應該還滿含著對祖輩的尊重 ,那些傳統演奏方式的保留也正是這種情愫的體現。
三、傳統鼓吹樂班生存現狀的思考及建議
魯南鼓吹樂雖為本文的研究對象,但它只是中國傳統音樂的一部分,在當今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中國傳統音樂所面臨的遭遇幾乎是一樣的。因此,放眼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
首先,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傳統音樂的傳承,并不是要“墨守成規、一成不變”,任何想要“原汁原味”地保護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改變——只是時間的問題。盡管改變是必然的,但如若任其自流,也許,傳統音樂的消亡將是我們所看到的唯一結果了。因此,要加大力度弘揚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處理好繼承、保護、發揚三者之間的關系。
其次,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始終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忽視了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近年來,雖然“傳承文化”已經是一個熱門的字眼,似乎與經濟發展之間產生了一定的關系,但在和諧的外表之下,仍然沒能脫離“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實質。因此,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快提升傳統文化的發展步伐,適當做到“經濟搭臺,文化唱戲”,使經濟能夠反哺傳統文化。
再次,重視對樂人的保護。樂人是音樂的載體,一個樂人能帶活一個樂種。崔家班就是例子,因為有了崔懷義等老一代樂手,傳統才會被大量的保存,崔懷義和他的傳統曲目就是崔家班的旗幟。如今,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對傳統音樂的堅守與傳承,并不是每一個樂班都能做到,正是崔懷義為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者們,使大量優秀傳統曲目和民間技藝得以保留。另外,對于民間樂人的保護,還應關注其后代的培養,現年63歲的崔家老二崔懷金,6歲學吹嗩吶,從小爺爺背著出去接活,因個頭不夠高,需要站在椅子上表演。而年輕的樂師,如29歲的崔建,17歲開始彈電子琴、吹笙,兩代人從起步就有十年的差距,在傳承上也一定會存在缺失,面對這種現狀,理應采取相應的措施。
“魯南鼓吹樂”這一傳統樂種,在當地民間儀式中占據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傳承這一樂種的“崔家班”,在生存、發展過程中的開放與堅守,終將使魯南鼓吹樂在社會復雜的鏈條中為民間習俗的傳承與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注釋:
①以棗莊為中心的魯南鼓吹樂“平派”嗩吶于1992年被文化部命名為“嗩吶之鄉”.
②另外有些樂班是崔家學徒們自己組織的小嗩吶班,在組成上與崔家班并無太大區別,演出人員及規模也是相似的。以崔家班作為研究對象頗具代表性.
③2012年5月17日采訪錄音.
參考文獻:
[1]項陽.當傳統遭遇現代[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
[2]山東省滕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 滕縣志[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3]山東省滕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 滕縣志[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4]張振濤.葬俗中的嗩吶樂班——榆林地區喪葬儀式的調查現狀研究[A].
[5]曹本冶.中國傳統民間儀式音樂研究(西北卷)[C].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注:本文系山東省藝術科學重點課題項目,項目編號:20170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