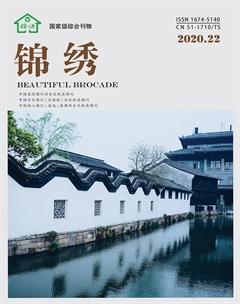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下科學紀錄片的美學特征與理論困境
科學紀錄片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段漫長的探索歷程,早在紀錄片誕生之前,科學與影像之間便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密切的聯(lián)系,數(shù)字技術(shù)的出現(xiàn),讓科學紀錄片的應(yīng)用場域不斷的擴大。在數(shù)字技術(shù)方面,雖然國內(nèi)學者在對電影技術(shù)研究的關(guān)注度要大于紀錄片層面,但是已經(jīng)有少量學者開始重視“真實再現(xiàn)”和“虛擬現(xiàn)實”這種技術(shù)手段對科學紀錄片所帶來的影響。
紀錄片作為一種視覺藝術(shù)形式,其藝術(shù)效果的呈現(xiàn)也離不開數(shù)字技術(shù)的支持。在電影領(lǐng)域中運用的任何數(shù)字技術(shù)與特效都可以在科學紀錄片中使用,但是要與其本身屬性與特征相結(jié)合,才能讓科學紀錄片的數(shù)字化之路走得更遠。
一、科學紀錄片呈現(xiàn)的技術(shù)美學特征
“紀錄片除了要向觀眾傳達教育意義還要表現(xiàn)創(chuàng)作者對生活的審美意識,要有形式美,并給觀眾帶來審美感染作用,這才是真正好的紀錄片所要承擔的責任。”1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出現(xiàn)后其美學特征主要體現(xiàn)了形式美的塑造,它能把抽象的科學紀錄片理論,變成可以看到的紀錄片影像,用電腦技術(shù)把科學紀錄片想要表達的內(nèi)容變成可見的世界,技術(shù)與藝術(shù)的結(jié)合讓觀眾獲得觀看快感,帶來一定的審美愉悅。
技術(shù)美學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是針對于某些特定領(lǐng)域中的特定事物進行研究,最主要的一個觀點就是要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建造事物,這個建造最開始是在工業(yè)領(lǐng)域,隨著技術(shù)美學這一學科被廣泛應(yīng)用,也適用在了影視視覺文化領(lǐng)域中來。最開始的技術(shù)美學探討的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符合多種審美要求的勞動環(huán)境,提高生產(chǎn)效率,而應(yīng)用在影視領(lǐng)域轉(zhuǎn)變成為如何在影視創(chuàng)作中,滿足受眾所需要的多種審美要求。根據(jù)不同時期技術(shù)對于藝術(shù)的介入程度,技術(shù)美學可以呈現(xiàn)出不同樣態(tài)。高鑫教授曾經(jīng)將技術(shù)美學分為自然技術(shù)美學、融合技術(shù)美學和介入技術(shù)美學三種類型。數(shù)字技術(shù)在科學紀錄片中的應(yīng)用,體現(xiàn)的是一種介入式的技術(shù)美學,數(shù)字技術(shù)的作用在科學紀錄片中凸顯出來,顛覆了傳統(tǒng)的紀實美學視覺觀念。
技術(shù)美學的產(chǎn)生是隨著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興起的,現(xiàn)在的技術(shù)美學已經(jīng)與受眾審美層次,審美品味的提高有關(guān)。科學紀錄片在采用數(shù)字技術(shù)的同時,首先要完成科學紀錄片的基本功能,即傳遞科學知識;其次才上升到審美價值。實用功能與審美價值是相互滲透、影響和制約的,不能割裂。
科學紀錄片中的藝術(shù)和技術(shù)絕非對立,它們是互補互動的。數(shù)字技術(shù)的出現(xiàn)拓展了科學紀錄片的形式與種類,它讓科學紀錄片的探索精神發(fā)揮到一定高度,大到探索宇宙,小到探索細胞,肉眼可見的客觀事物過于平淡,不能帶給受眾視覺沖擊,產(chǎn)生新的審美感受。數(shù)字技術(shù)的變革是未來科學紀錄片不斷創(chuàng)新與轉(zhuǎn)型的一個重要支撐,數(shù)字技術(shù)與科學紀錄片的交流與互動,是未來科學紀錄片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的趨勢。
二、虛擬美學與紀實美學的爭辯
紀實是紀錄片的本質(zhì)特征,傳統(tǒng)紀實美學有兩大理論奠基人,一是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另一位是德國電影理論家齊格菲利德·克拉考爾,傳統(tǒng)真實觀是在他們的理論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1945年,巴贊在《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中,指出攝影與繪畫的不同,同時他在紀實美學中提出了“影像中的時空必須和現(xiàn)實中的時空保持一致”這一重要觀念。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過程就是客觀真實事物的再現(xiàn)過程。克拉考爾與巴贊一脈相承,要求電影要真實的反映現(xiàn)實生活。
傳統(tǒng)的紀實美學主張直接拍攝客觀事物,不應(yīng)受任何技術(shù)或者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巴贊的真實理論的基礎(chǔ)就是影像真實與現(xiàn)實性的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也體現(xiàn)在時空的統(tǒng)一性上,弱化了技巧的作用,避免主觀加工。隨著數(shù)字技術(shù)的應(yīng)用,虛擬影像不斷的在紀錄片中出現(xiàn),這種通過技術(shù)生產(chǎn)出來的“現(xiàn)實影像”,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美學觀——“虛擬美學”,此時巴贊的觀點“影像與客觀現(xiàn)實中的被攝物同一”已經(jīng)不能適用于新興的虛擬影像相關(guān)理論,傳統(tǒng)的紀實美學被后來的虛擬美學不斷沖擊。美國學者林達·威廉姆斯表示“真實與虛構(gòu)之間過于簡單化的二分法從根本上使我們在思考紀錄片的真實性問題時陷于困境。我們的選擇不應(yīng)該局限于真實和虛構(gòu)這兩個完全分離的體系,相反為了接近絕對的真實,我們可以在多種虛構(gòu)的策略中進行選擇。”2許多提倡虛擬美學的學者將虛擬影像的出現(xiàn)看作是可以替代真實再現(xiàn)的一次全新探索。
三、數(shù)字技術(shù)下的真實邊界
數(shù)字技術(shù)制作的虛擬影像與傳統(tǒng)紀實影像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前者是現(xiàn)實生活的二次加工,而后者是現(xiàn)實世界的直接呈現(xiàn)。即使虛擬影像是以實物或者現(xiàn)實生活作為參照模型,但它完全擺脫了攝像機的鏡頭,它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guān)系,和傳統(tǒng)紀實鏡頭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完全不同。數(shù)字技術(shù)讓現(xiàn)實真實和虛擬真實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因此引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科學紀錄片真實性的討論。
探討科學紀錄片中虛擬影像的真實性問題,需要先討論藝術(shù)與科學的關(guān)系問題,有學者指出藝術(shù)與科學的互動關(guān)系代表著一個傳統(tǒng)美學的命題,即美與真的關(guān)系問題。幸小莉在《數(shù)字紀錄片中的動畫美學與紀實美學之悖論辨析》中指出,“如果用符號學來分析,由影像構(gòu)成的形式屬于符號體系,而影像形成的影片內(nèi)容屬于符號指涉的意義。意義象征的客體為物質(zhì)現(xiàn)實。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shù)作品,它由形式和內(nèi)容兩個維度組成,內(nèi)容對物質(zhì)現(xiàn)實具有象征作用,而形式又代表著物質(zhì)現(xiàn)實,可以說形式與內(nèi)容共同構(gòu)成了與物質(zhì)現(xiàn)實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這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的契合程度體現(xiàn)了紀錄片對物質(zhì)現(xiàn)實把握的程度,即真實性的程度。”3從符號學角度來講,客觀對象與虛擬再現(xiàn)是一種象征與被象征的關(guān)系。因此我們不能從單一的角度去考慮科學紀錄片的真實觀,要從內(nèi)容和形式兩種視角去重新審視。傳統(tǒng)紀實美學與現(xiàn)代虛擬美學所探討的真實性,都是在探討紀錄片的形式真實。數(shù)字技術(shù)雖然制作了脫離物理鏡頭的虛擬影像,但它所代表的事物仍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從內(nèi)容角度來講這種虛擬影像仍是真實的,是運用數(shù)字技術(shù)去輔助呈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的客觀事物。
參考文獻:
[1]周菲菲《新虛構(gòu)紀錄片的美學特質(zh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2009年,第14頁。
[2]單萬里《紀錄電影文獻》,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第576-593頁。
[3]幸小莉《數(shù)字紀錄片中的動畫美學與紀實美學之悖論辨析》,載《電視研究》,2013年第10期,第40-42頁。
作者簡介:李嬌(1992-)女,滿族,遼寧錦州,碩士研究生,工作單位:四川傳媒學院(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