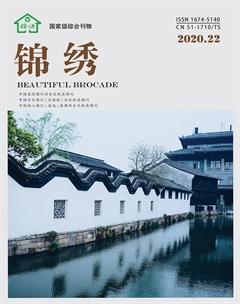《新唯識論》之《唯識》章初探
石芮
摘要:熊十力先生融會中西、學貫古今、融易入佛,歸宗于儒,形成自己獨特的治學風格。其代表性的哲學著作《新唯識論》從體用不二的本體論、翕闢成變的宇宙論、天人不二的人生論三個維度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語體本的《新唯識論》中《唯識》章在駁斥窺基“境空識有”的基礎上提出“境空識空”闡明唯識之含義,揭示吾人生命與宇宙大生命元來不二的天人合一之境。
關鍵詞:熊十力;唯識;境空識空;體用不二
“平生學在求真,始而學佛,終乃由疑而至于攻難,然對于釋尊及諸菩薩之敬仰則垂老不渝。”1 熊十力深感從世親迄護法諸師學說的懸空構畫以及出佛教出世精神之流弊,以《易》入佛,又受到西方哲學的熏染,著成《新唯識論》一書,總言其“體用不二”的學術思想。此書行文流暢,邏輯緊密,但成書頗有波折,幾經刪定修改,主要有文言文本和語體文刪定本兩個版本。本文主要以語體本為研究對象,分析《唯識》章對唯識的解讀。
一、以“境空識空”批駁“境空識有”
熊十力辯證地看待無著學派說境空識空的主張。窺基大師在《成唯識論序》中將唯識二字理解為:“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2認為唯識就是境空識有,否認有離識而獨在之境的存在,卻說識是有。熊十力則不然,他在肯定無著學派“外境非有”的同時,斥破其“識有之論”,主張“境空識空”。《唯識》章從“境不離心獨在”、“妄識無自體”兩個方面進行論證。
(一)境不離心獨在
熊氏主張沒有離心獨存之境,破外道、小乘對心外境、物的偏執。他觀其流、究其源將此種偏執歸結為應用不無計和極微計兩類,逐一駁斥。
1.破除應用不無計
應用不無計借用西方哲學上的經驗論來解釋,感知到的即為實存。此計以其參照對象的范圍大小被劃分為別計和總計。
熊十力先生分別斥破別計、總計。別計誤將經驗到的具體事物判定為離心實在。熊氏反駁:“殊不知這種境若離開我的心便無此物”。他以瓶為例,正是由于意識的作用才有瓶的實存,可知沒有心外之具體事物的存在。總計執著宇宙物質之離心實存,以外境為識之因證明外境實存。外境為識之因是熊先生所認可的,但這個境離心獨存確實妄言。在他的學說中,境、識是相對而名的兩方面,境代表物質是有差別對待的;識象征精神是無對礙的。
2.破除極微計
至于“極微計”《唯識》章有言:“此實從前計(應用不無計)中別出言之,乃依所計立名,曰極微計。”3極微計因推究外境為實有的依據較特殊,而從應用不無計中分流出來,單獨立名。極微是構成宇宙的最小單位,類似于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原子、電子,通過極微的實存判定宇宙萬物實存。
《唯識上》篇中大乘與小乘圍繞極微進行的辯論以時間為線索進行動態梳理。
(二)、妄識無自體
上一節斥破離心自存之外境,本節斥破妄識。“妄識”即說“妄心”。在印度佛家看來,即是“緣生法”。妄識為因緣會和而現起,隨緣流變而無自體,無自體故空。
熊十力籍重新勘定四種緣說明妄心的現起:一因緣為識本身具有的能動力用;二等無間緣,指前念的識能引起后念的識;三所緣緣乃是由所緣境引起的思慮識;四增上緣是對前三種緣的補充,可看做是所得果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對上述諸緣分析可知,諸緣之間互有關聯,由其所生之妄心也就并非一一獨立的實在,而是有所依托,也就念念起滅不住,剎那生滅,無有自體。
二、“境空識空”而非“境無識無”
“夫妄心空而仍非無心,外境遮而仍非無境”。4熊十力雖否認離心獨存之外境以及有自體之妄心,卻不主張“境無識無”。外境非離心自存故而為空,境卻非無,依心而存之境為實有。妄心無自體故而為空,妄心雖空,本心之發用畢竟不空。
“唯識”極力斥破心外之境,卻不說境無。心上所現之影像無論是依托前境而起,還是純從心上所現者,必然有一個境的誘因存在。即便是后者,雖無現前境物為所托,也須得依靠過去經驗為誘因。可知,物(或境)絕不是虛妄的,只是心、境不能分開而言。二者對立得名,物無法脫離心而單獨存在,心(或識)之發用離不開物的誘因。心有作而境隨轉,境有激而心即覺。5心境一體兩面,心是能了,境是所了,互資交感。
“唯識”明妄識亦空,不說識無。識本身是一種固有的自動的力,實際上是性智的發用,有本心、習心之分。如陽明所說,本心是“自然靈昭不昧”,妄識興發于“應物”,感官接收境的刺激。前者之發用畢竟不空,后者無自體故空。
三、指向“天人合一”
眾所周知,熊十力的學術“貴在見體”6,“體用不二”貫穿于其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的方方面面。《唯識》章最終也回歸于“天人合一”、“體用不二”。
《明宗》章開門見山:“今造此論,為欲悟諸究玄學者,令知宇宙本體非是離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識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實證相應故。”7宇宙與心一體,對本體的追求只能反求諸己。中、西哲學一大分別就在于此,西方哲學強調理性、思辨,于自身之外推求本體,分隔主客。中國哲學講求涵養,消除主客界限。先秦孟子講“萬物皆備與我”,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都體現著中國哲學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特點。“唯識”主張物不離心,心能感物,二者皆為本體之發用流行,究不二。宇宙無物我、內外可分,吾人之生命與宇宙大生命本來無二。
小結
“唯識”闡明吾人生命與宇宙大生命元來不二的道理。“唯者殊特義,非唯獨義”8只是駁斥有離心獨在之境,并非否認物、境的存在。相反,正因有心,才有境,心境二者相對存在。雖是確有物、境之存在,但須知此境為識所變現,不可脫離識而自外在。“識者心之異名”9心識同謂,隨義異名,同指精神、意識現象。心有本心、習心之分;識也有妄識之流。妄識依因緣匯聚生,隨緣而轉,因而無自體。綜合來看,“唯識”乃是強調心之殊特義,境是由心變化出來的影像,心物相對有分,而心為物主究不二,彰顯《新唯識論》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根本要義。
參考文獻:
[1]熊十力. 新唯識論[M].上海古籍出版社.
[2]孫改明. 論熊十力與唯識學[D].吉林大學,2011.
[3]黃敏. 《新唯識論》儒佛會通思想研究[D].武漢大學,2010.
[4]郭齊勇.論熊十力對佛教唯識學的批評[J].世界宗教研究,2007(02):40-50.
[5]宋志明.試論熊十力“新唯識論”思想的形成[J].學術月刊,1987(08):37-4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