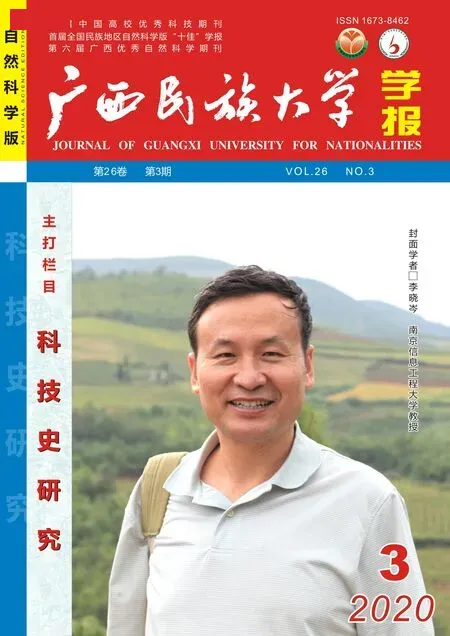20世紀上半葉生命起源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侯 琨
(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
0 引言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期間,隨著達爾文進化論的傳播和分子生物學的興起,[1]生物學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都發生了深刻轉變.其中,學界對于生命起源問題的思考和研究就深受這種轉變的影響,其標志性成果是1953年的米勒實驗.[2]20世紀上半葉生命起源研究長期處于科學界的邊緣位置,[3]在1950年能為學界所公認的成果屈指可數,但以國際生命起源研究協會的官方意見而言,這一時期奧巴林(Oparin,Alexander Ivanovich,1894-1980)和霍爾丹(Haldane,1892-1964)的工作都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4]
對于中國而言,19世紀末期與生命起源問題相關的內容即已散見于學界,如《熒惑新解》中對于火星生命的討論[5]和《格致匯編》中對于“巴斯德學說”的介紹,[6]但這些內容只是在側面上觸及生命起源的相關問題,真正有目的地、系統性地、專業性地引入相關學說要到20世紀上半葉.隨著租界《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英文報紙的報道、傳播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留洋熱潮的興起,生命起源的各種理論伴隨著西方最新的生物學知識被引入中國,并在中國傳媒界、學術界廣泛傳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在廣東學術界爆發了一場以“自生說”為焦點的學術爭論,[7]其參與人群之廣、社會影響之大都與同時期西方學術界的蕭條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目前,生命起源理論在中國的傳播這一主題尚未有人展開系統、深入地研究,前人工作多以介紹前沿成果為主.生命起源問題在近現代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與地外生命探尋、宇宙早期演化等當代科學的重要內容有著密切的聯系.文章借助《瀚文民國書庫》和《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等最新開發的圖書、期刊、報紙數據庫,對民國時期《字林西報》《科學》《東方雜志》等重要報紙及雜志中與生命起源相關的科學類報道和論述進行了詳細檢索,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文本.通過這些文本,筆者梳理了生命起源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可分為隨租界報紙傳入的西方本土的討論和中國學者主動介紹、傳播的相關理論兩個階段,并從微觀的生命起源研究和宏觀知識傳播兩個角度對于這一時期生命起源理論的傳播和影響進行解讀.
1 隨《字林西報》傳入中國的生命起源知識
《字林西報》創刊于1850年,是當時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其發行量是遠東其他地區出版的英文報紙的兩倍,且在它的讀者群中,中國讀者的訂閱比例高達26%,它在上海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擁有極大的影響.[8]
1912年9月12日,《字林西報》報道了一則消息:英國科學促進協會植物學與動物學部開展了有關生命起源問題的討論,并且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9]這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討論生命起源問題的報道.自此之后,《字林西報》開始刊載一系列關于生命起源討論的報道.從1912年9月12日-1935年8月27日,《字林西報》及其周報《北華捷報》共計15次報道生命起源問題相關的講座、專家意見及讀者來信,①《北華捷報》是《字林西報》的周報,故其內容與《字林西報》高度重合,在此不再列出.在此列舉數例(表1).

表1 《字林西報》及相關英文報紙中關于生命起源的報道Tab.1 Reports on the origin of life i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related newspapers

續表1 《字林西報》及相關英文報紙中關于生命起源的報道
綜合來看,從《字林西報》傳入的生命起源知識基本反映了這一時期英國學術界對于生命起源討論的原貌,在這一傳播過程中呈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傳播內容的多樣性.在《字林西報》的報道中,不僅有傳統的“自生說”“神創論”等關于生命起源的早期觀點,也有19世紀下半葉興起的“胚種說”和20世紀逐漸形成的“化學起源論”,甚至還有聽起來頗有無稽之談的以物理學中的“波”來解釋靈魂的觀點.這反映了此時期英國學術界在該問題上思想不統一的狀態.由于權威解釋的缺位,生命起源問題實際上成了學術演習場,各種不同觀點、不同學派都有自己的聲音,頗有百家爭鳴之意.但實際情況正如1933年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在英國科學促進會上所言:“(關于生命起源)我們唯一可以確信的就是我們一無所知”.[10]
第二,傳播主體的多元化.按照一般的觀點,生命起源問題是生物學家該研究的內容,但在《字林西報》所構建的傳播體系中,我們看到了更多社會群體的參與.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生命起源問題的廣泛影響.其中既包括了生理學家、英國科學協會主席謝弗教授,也包括了生理學家、神經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成員查爾頓·巴斯蒂安,還有物理學家奧利弗·勞治,以及宗教界人士和熱心讀者.多學術群體的參與給生命起源問題的研究帶來了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其中最具啟發意義的莫過于宇宙學上對星際物質的研究和化學進化論的視角,[11]這些前期不同領域的工作積累,為20世紀50年代的生命起源問題的突破性進展提供了思想和方法準備.
第三,傳播質量高水平化.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解讀:一是報刊所介紹的知識的即時性;二是讀者來信中所體現的思考水平.從知識介紹的角度看,在“胚種說”相關的報道中,相關學者給出了星際傳播理論的兩條困境,即低溫缺氧的環境中微生物休眠以及紫外線對生命體的殺傷,這都體現了當時研究的最新水平.在化學起源論中,試圖將達爾文學說微觀化、以蛋白質起源為核心思考生命起源問題,這也與后來的米勒實驗不謀而合.從讀者的角度看,1935年8月27日,約翰·切斯特從上海的來信中,他對于“胚種說”的困境——只是將起源問題轉移而未加以解決以及生命起源的化學理論中對于最初生命解釋的乏力,都有著深刻的認識.
2 中國學者主動翻譯、引進的生命起源學說
《字林西報》雖然介紹了大量的生命起源的相關理論及其討論,但由于其受眾群體的限制,這種討論很難被中國大眾所了解.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隨著如《科學》等科技類雜志在中國生根、[12]大型綜合類期刊《東方雜志》編纂內容以“科學精神和民治主義”為價值判斷發生轉向[13]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科學啟蒙浪潮,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為代表的近代重要出版機構開始成為這一階段相關知識傳播的主要渠道,[14]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主動在中文報紙、雜志以及書籍中傳播相關知識.在這一階段,上海得風氣之先、區位之便,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都是中國科學傳播最重要的前沿陣地.直至20世紀40年代,由于中國形勢的變化,關于生命起源知識的傳播中心開始向西南大后方轉移.同時,一大批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中國知識分子如費鴻年、周太玄、胡先骕等不僅主動引進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還將西方的理論與中國本土的傳統觀點相結合,以一種中西貫通的新視角向中國讀者普及相關知識,取得了顯著效果.在這一時期,生命起源理論之豐富、爭議之巨大、社會影響之廣泛都要遠超前一階段.
2.1 “百家爭鳴”的傳播內容
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主動翻譯、引介生命起源相關理論后,相關理論逐漸多樣,且歷史性、細節性都有所豐富,可以說呈現出一種“百家爭鳴”的局面,按照具體內容來看,大致可分以下幾類.
一是胚種說.可能是受《字林西報》的影響,至今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文文獻正是“胚種說”,而且時間、地點都與《字林西報》的報道相差無幾.1922年,健孟在《東方雜志》撰文《生命的星云的起源說》,在該文中他不但介紹了物理學界以開爾文為代表的“隕石傳播論”和以阿倫尼烏斯為代表的“光壓理論”,還介紹了生物學界艾倫·阿普沃德(Allen Upward)類似的觀點,“生命的胚種是宇宙初創的時候下來的,他的生命雖被吞在行星的火里,生命卻并不被毀滅的.”[15]1925年蔣丙然翻譯的《原生》一書中,也對“胚種說”進行了介紹,“承認宇宙空間,遍布種子,一遇情境適合之世界,即可因此發育.此說創自利剌德,主張生為永久……”.[16]
二是自生說.“自生說”以巴斯德鵝頸燒瓶實驗為界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胡先骕曾對其做過區分,“普通之人所信仰之化生說與自然發生說,已經芮第、司巴闌巉利、巴斯德諸人證明其非.然生命之起源終出于一種方式之自然發生.此種生命之秘密,當由光之作用與膠質物之天演中求之.”[17]概括而言,“自生說”觀點在前一階段認為生命均可從無機界自然生成且至今仍在進行,后一階段則認為生命僅可一次自然生成,之后則按照達爾文進化論演變成不同物種.
中國學術界對前一觀點基本持否定態度,其認識水平多以介紹從亞里士多德到巴斯德時期觀念的演變和實驗的探究為主,代表性的著作有1922年胡先骕《生命之起源與生命之特性》、1925年法國派茄姆《原生》、1933年朱洗《化生說的進化》,[7]等等.而中國學界對后一觀點認識普遍較少,僅在胡先骕的介紹中見到,對于查爾頓·巴斯蒂安所做的自生實驗,他評價“此公之試驗或亦有可信之理也”,[17]581而對于巴里(E.C.C.Baly)和奧斯卡·鮑迪施(Dr.Oscar Baudisch)所做的有機合成實驗,他也評價“生命自無機物自然發生之說,并非不可信也.”[17]582至1948年,《開明新編高級生物學》一書中,將這些零散的實驗概括為“新自然發生說”,認為“在地球的歷史上,一定有一個時期各種情況適宜于碳、氫、氧、氮各種元素巧合而成膠狀的化合物,益以物理化學的變化,轉變成有代謝作用的物體,這就成為原始的生物.”[18]
三是蛋白質學說.此時期,另一種帶有濃重化學起源意味的“蛋白質學說”開始在學術界廣泛流傳.此學說要點如下:(1)蛋白質在生命活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催化功能正逐漸為學術界所認知.孫君立曾在《東方雜志》發文指出,“凡屬有生命的物質,都要吸收,都會同化,都能排泄,這就是有新陳代謝和能力遷移的作用了.此被視為生命之最初證據……他們始終是蛋白質的分子.”[19]這種觀點與20世紀上半葉科學界對于蛋白質功能、結構的研究相適應,早期的生命起源研究也以合成蛋白質為中心任務.(2)蛋白質膠質溶液形態學上有成團傾向,被認為與早期細胞的形成有關,“從杜諾愛氏的研究,就可以證明細胞或許只是一個或多個蛋白質分子,成立于力學平衡傾向的推理的結果.”[20]88正是在此思想氛圍下,中國學者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引介“蛋白質學說”的文章屢見不鮮,如1929年孫君立《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演化在化學上的概念》、1931年朱鳳美《生命之起源》、[20]1934年張明哲《化學的生命起源觀》、[21]1947年張璣《生命的起源》[22]都對蛋白質學說進行了引介.
四是人造生命的嘗試.1930年《北辰》雜志上蒙福翻譯的《生命之起源》一文中,對于英國人在20世紀初進行的兩次人造生命實驗進行了記載.
1905年,英國人伯爾克自信可以用鐳體制造原始生物.……不久伯爾克自認其非,其言曰:培養液上層之浮體非他,實膠水受鐳之影響而分解時所生之氣泡耳.1906年底,法國南特(Nantes)醫學教授施德蕃盧渠(Stephane Ledue)氏,報告制作細胞法于科學博士院.據言,此種細胞能實現生活作用之大半數.……不久由其他學者證明盧氏所得之現象,非生物之自然生殖,此乃物理實驗上所常見之阿時磨時(Osmose)景況.[23]
這兩次實驗一次是因為產生氣泡、另一次是因為滲透現象而被誤認為是生命跡象,雖然是因為缺乏常識所導致,但是此類事件在國外并不是孤例.1929年,《學生雜志》刊文《生命起源論的新研究》,報道了美國農學院墨西哥部生物系主任赫勒拿教授的研究成果:他用礦質與有機物質,已能造出假細胞與假原形質,模仿生命的本體……他將橄欖油和石油的混合液體,盛在平底的磁碟里……他再用小吸管吸取小量的黑蘇打溶液,注入橄欖油和石油的混合液體表面以下……那黑滴變成了生活的東西,開始膨脹、震顫、自己搖動……[24]
這些實驗以現代科學的角度看,似乎荒誕不經.但在20世紀上半葉,由于生命起源研究在整個學術界處于邊緣位置,從事嚴肅科學研究的學者很少,發文者多屬于業余愛好者,再加上遺傳物質尚未被發現,從形態學入手試圖解釋生命現象的嘗試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甚至當我們考察奧巴林團聚體假說時,他也認為蛋白質膠質成團傾向與細胞起源有密切的聯系.[25]這種思考也是一種從形態學入手的思路.所以這種基于擴散、皂化反應等不同類型的形態學改變均可以看作是從 “機械論”的角度來解釋生命起源的結果.
2.2 隨時局演化的傳播特點
從傳播區域和傳播群體來看,《字林西報》由于總部在上海,所以其傳播影響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而此時隨著傳播媒介的擴展,生命起源理論的影響逐漸擴大,其傳播區域也有了變化.在此以1921-1949年報道或刊載過生命起源類作品的報紙、雜志、書籍為例進行分析,中國知識界主動吸收、傳播生命起源相關知識的過程相較于第一階段,也呈現出新的局面和特點.
首先,從傳播的區域來看,上海在生命起源知識傳播的過程中得風氣之先,加上它完善的出版體系,在抗戰爆發以前的20世紀20年代-30年代一直是傳播重鎮.但隨著時局的進展,在20世紀40年代之后,西南大后方成為新的傳播中心,相關文章在大量的科學雜志上頻繁出現.從數據統計來看,20世紀20年代共有9篇文章,20世紀30年代有7篇,而20世紀40年代則高達15篇,呈現出一種戰局越吃緊、越有更多人關注到這個問題的景象.而在解放戰爭尾期,東北解放區的東北書店甚至專門出版了《地球上生命的發生》[26]一書,介紹蘇聯學者奧巴林的生命起源理論.這一點是格外值得關注的.因為東北書店是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領導的出版發行機構,具有濃重的政治宣傳色彩和意識形態意味,這也給新中國的生命起源理論傳播的新特點埋下了伏筆.
其次,從傳播主體的角度看,民國時期生物學領域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很高,各個分支學科都從不同角度傳播過相關知識.其中,畢業于法國的生物學家周太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先后翻譯了3本法文原著,向中國引進相關成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應.宗教界人士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相較于西方人數較少、影響也有限,這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從傳播來源來看,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法國、英國、日本學界的學術成果是中國學者翻譯、引介的主要來源,進入20世紀40年代后,蘇聯成了新的重要的傳播渠道.
再次,從傳播載體和途徑來講,中國重要的綜合性刊物、科技類期刊以及大型出版機構成了這一時期生命起源知識傳播的主要媒介.20世紀20年代-30年代,上海的《科學》《東方雜志》《學生雜志》各有3篇專門文章加以討論,商務印書館在這一時期出版了7本學術性著作,或全文、或重要章節對生命起源問題展開論述.進入20世紀40年代,重慶更是出版發行了一系列具有科學普及性質的雜志,其中《學習生活》《青年與科學》《科學與生活》《科學時代》《中華少年》等多本雜志中都有專門文章介紹生命起源問題,對于整個西南大后方的科學普及、科學教育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3 生命起源知識傳播的影響
客觀來看,20世紀上半葉是世界范圍內生命起源研究的低潮期,中國在這一時間段對該領域知識的傳播無法脫離這個大的時代背景,所以很難以學術上的高要求來衡量這種知識傳播.但在這一過程中,“羅廣庭事件”引發的爭論和“奧巴林學說”的引介還是能夠反映中國學術界知識傳播的突出特點,即重理論、輕實驗與哲學觀點先行的特點.這種學術引介的氛圍也對20世紀中國的科學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
3.1 “羅廣庭事件”的爭論焦點
羅廣庭①羅廣庭(1901-1982),廣西北海人,1928年在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后在法國巴斯德學院、廣州中山大學生物系、廣州光華醫學院工作.曾于1932年在《科學》雜志發表《生物自然發生之發明》、[27]1933年在《東方》雜志發表《用真憑實據來答復進化論學者》[28]等文,宣稱自己已經通過實驗證實了生命可以自然發生,推翻了“巴斯德學說”,并使得達爾文進化論失去了依據.這種論調在社會上尤其是在科學界引發巨大爭議,大批生物學家開始在媒體上公開發聲,與羅廣庭展開論戰.1933年,中山大學理工學院生物系編纂《現存生物自然發生說之批評文錄》一書,對批判羅廣庭觀點的文章加以匯總,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薛攀皋和王凱曾分別對該事件展開論述和分析,薛攀皋側重于從科學主義的角度批判羅廣庭;[29]而王凱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于不同時期參與到羅廣庭爭論中的各家觀點進行分析.[30]但二人的分析之中對于生命起源這個大的學術背景涉及有限.筆者從內史的視角對“羅廣庭事件”爭論集中的“自生說”“進化論”兩個維度進行分析,以期能夠深化前人的研究,闡發生命起源的傳播影響.
第一,從“自生說”的角度來看,羅廣庭的自生理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特定的背景.“自生說”按照基本觀點的不同可分為“舊自生說”和“新自生說”.巴斯德時代之前,學者們認為生命普遍從無機界自然產生的觀點可稱為“舊自生說”.而巴斯德之后,由于受進化論的啟發,一些學者認為生命曾經至少有一次從無機界自然產生,然后按照進化論的觀點分化成不同物種,這種自生觀點就是“新自生說”.以羅廣庭事件來看,不論是當時學界還是今天的研究者,多從“舊自生說”的角度來否定羅廣庭,很少有人關注到當時“新自生說”思潮的興起及其對羅廣庭的影響.“新自生說”的觀點在當時就已經傳播到中國學界.胡先骕曾在1927年《化生說與生命之起源》一文中介紹了“自生說”的兩組實驗.從這個角度看,羅廣庭產生“自生說”的想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并非毫無根據.但“羅廣庭事件”的爭論雙方,對于這些已經傳入中國的新式學說的實驗竟然絲毫沒有觸及,甚至其就“自生說”所進行的實驗多為巴斯德時期的翻版,這一點上足以證明中國學界對于科學實驗的漠視程度.
第二,從進化論的角度看,羅廣庭對達爾文的質疑所遭受的批判要遠遠超過其因“自生說”而導致的批判.在中國,達爾文進化論科學性的一面影響力遠不如其社會性的一面.經改造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廣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嵌入到20世紀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中.正如浦嘉珉所指出的“達爾文在中國填補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真空,并在方方面面都中國化了”.[31]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氛圍和意識形態下,羅廣庭對于進化論的攻擊無疑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彈.關于這一點,翟象謙的觀點講的最為透徹:就退一步說,羅先生的自然發生說能成立了,也不能據此來打倒進化的事宜.羅先生總以為生物可以自然發生便不須有變異式的進化了,然而他卻不曾想到生物自然發生和進化并不是兩相矛盾的事情,就是進化論學者也有承認生物是自然發生的.因為生物的發生是一件事,而生物的演化又是另一件事,進化論解釋了物種的起源,卻沒有解釋生物本身的來源.[7]16
生命的自然生成問題確實是此階段科學界從邏輯上尋找到的填補進化論真空的唯一解釋.翟象謙的觀點也向我們表明了這樣的態度,即羅廣庭對于“自生說”的實驗盡管有失誤之處,但這并不構成對他批判的核心理由,他對于達爾文進化論的質疑才是學界所無法接受的.對于中國知識界而言,達爾文與進化論不僅是科學上的真理,更是從意識形態層面已經深入中國人骨髓的信仰.從這一點來看,“羅廣庭事件”與其說是一場科學爭論,倒不如說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更為貼切.
3.2 “奧巴林學說”在華流行
蘇聯生物學家奧巴林曾于1924年將他關于生命起源的觀點匯總成小冊子出版,1936年他寫作完成《地球上生命起源》(第一版),[32]1938年該書被翻譯成英文版本而被傳播到西方學術界.[33]但總體來看,該書在西方學術界影響有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引發廣泛關注,[34]直至1953年米勒實驗的結果發表之后,“奧巴林學說”才被普遍認可.
與西方學界對“奧巴林學說”的慢熱狀態不同,中國學者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就關注到并且翻譯了“奧巴林學說”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到了20世紀50年代早期,甚至在米勒實驗發表之前,“奧巴林學說”就在中國學術界取得了官方地位.[35]但與西方研究者如米勒對于奧巴林學說中官方原始大氣環境、細胞產生的化學路徑等科學性內容的關注不同,中國學者更加關注奧巴林學說中偏哲學性的部分.
1942年的《文化桂林雜志》和1946年《科學時代》雜志曾刊登兩篇“奧巴林學說”的譯文,從這兩篇譯文的節選來看,中國學者普遍對于“奧巴林學說”背后的哲學考量更為關注.在《生命的起源》一文中,奧巴林對于隱藏在各家生命起源觀點之后的哲學觀做了明確地區分:依照觀念論觀點的解釋,生命的本質是屬于某種非物質的、靈魂上的起源的……與這相反的唯物論卻教給我們,生命本質上也是物質的……(機械唯物論的立場)生物只是一具異常復雜構造著的機械而已,……根據辯證法唯物論,(生命)發生在物質發展的某一定的階段上.[36]甚至奧巴林認為,生命起源問題背后反映的是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圍繞著這個問題(生命起源),卻總是展開了尖銳的哲學斗爭;而這種哲學斗爭,其本身則是反映著社會集團之間的斗爭的.”[37]在奧巴林的話語體系中,生命起源的各家學說與西方哲學的各個流派構成了對應關系,即哲學上的“唯心論”對應著生命起源學說中的“自生說”和“生命永恒說”,哲學上的機械唯物主義對應于生命起源學說中的生命自動生成理論,①該理論與“自生說”的區別在于自生說認為生命可以從無機物中普遍自然發生,而生命自動生成理論則認為生命起源于生命物質結晶化,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特殊的結構.而奧巴林以達爾文進化論構建的學說則對應于哲學上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
這種區分結果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在這里不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界至少在生命起源這個問題上對于奧巴林的推崇恰恰是基于他的哲學上的觀點,而對于“奧巴林學說”中被米勒所借鑒的對于原始大氣成分的猜測,[2]以及奧巴林自我評價中最重要的團聚體假說,中國學界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缺乏足夠的認識.正如郭穎頤所指出的,這一時期中國學界對于生命起源、人類和宇宙關系、人類的本質等一系列問題都有一種預先設立的前提,即科學一元論.[38]哲學觀點先行成了這一時期中國科學傳播的重要特點.
不論是“羅廣庭事件”的爭論還是“奧巴林學說”的流行,都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對于生命起源問題的突出態度,或者說中國學界對于西方科學知識傳入的普遍心態.從微觀層面來看,這是一種重理論輕實驗、哲學觀點優先的心態;從宏觀層面來說,它反映出中國學者濃重的博而不專的治學傳統和對于西學價值判斷中的意識形態情結.這些都成為中國學界在20世紀上半葉知識傳播中的重要特點,影響著幾代中國知識分子.
4 結語
文章研究表明,20世紀上半葉關于生命起源的“胚種說”“自生說”“蛋白質說”等觀點的具體內容都被傳入中國,甚至被公認為20世紀上半葉最重要成果的“奧巴林學說”也在40年代之后被引入中國學術界.從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的中國科學知識傳播中心的上海到40年代新的傳播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在生命起源知識的傳播過程中,重哲學觀、重意識形態、輕科學性的傾向展現的尤為明顯.
從發展的階段性而言,生命起源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達到高峰.這樣的高峰有多方面的表現,其傳播區域之廣、參與人群之多、內容之豐富都較前一階段有了明顯的發展,甚至在這一時期還發生了中國本土化的生命起源爭論——羅廣庭事件,更可以看出此時期社會各界參與到生命起源討論中的難得景象.但從世界生命起源研究的發展史來看,20世紀上半葉是國際生命起源研究的低谷期,一直到50年代米勒實驗的發表以及第一屆國際生命起源大會召開之后這一現象才得以扭轉.而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由于特定歷史條件,學界對于生命起源的關注度下降,使得中國與西方在這一研究上產生了時代的交錯,錯過了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良機.
從傳播效果來看,中國學界對于思想性成果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要遠高于實驗成果.重要的實驗性成果即使被介紹進中國,也并沒有在中國學者之間產生大的影響,甚至連“新自生說”這樣的觀點被引入中國后也被“束之高閣”.而經過改造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唯物論的“奧巴林學說”這樣的思想性成果卻容易被中國學界所接受,捆綁在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結構中.這樣一種重理論輕實踐、哲學導向先行的傳播特點與日后中國科學界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上的特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構成了20世紀早期科學傳播中獨特的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