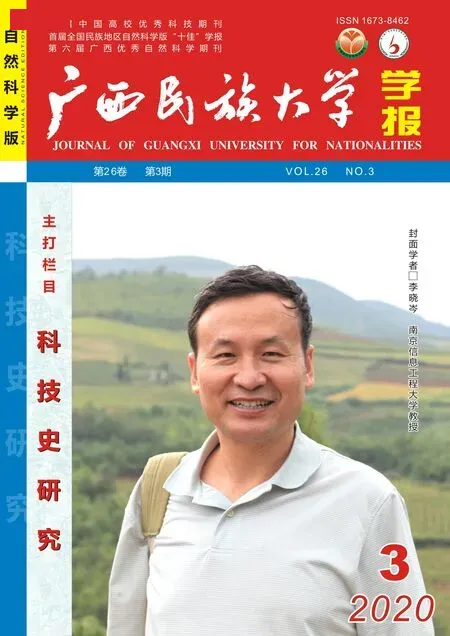《房龍地理》出版發行的歷史啟示*
楊丹丹
(1.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2.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1 房龍與《房龍地理》
1.1 房龍簡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荷蘭裔美國人,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出色的歷史通俗讀物作家、插圖畫家,偉大的文化普及者.1902年,房龍獨自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1905年獲得學士學位.1906年前往德國,在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房龍曾遭遇多次打擊,這些打擊不止來源于生活,更來源于工作.房龍博士畢業后曾嘗試過多種工作,但均以失敗告終,最終在康奈爾大學和俄亥俄州安條克學院獲得職位.房龍因其風趣幽默的授課風格廣受學生的喜愛,但同行認為他的教課模式對學生的學業并無益處,并且通過后期實驗被驗證.房龍因此備受打擊,便辭職做回自己的老本行——記者,但其工資并不足以維持房龍家庭的開銷,一直靠妻子娘家補貼家用.
在承受生活、工作雙重打擊的同時,房龍也在不斷地嘗試創作,希望借助創作的成功,擺脫生活的困境.但其寫作事業也并不是一帆風順.1913年,他正式出版了由他博士論文改編的《荷蘭共和國興衰史》,這是房龍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但銷量慘淡.隨后又陸續編寫其他書籍,也并未大賣.
由于現實的多重打擊,房龍的精神世界開始崩塌,以至于患上了嚴重的精神衰弱.房龍不再像以前一樣意氣風發,充滿自信.自此,他開始對自己的作品產生懷疑,即使他的代表作《人類的故事》在出版前得到了自己老師和業內人士的高度評價和稱贊,但他仍然害怕不能暢銷.為了能提高銷售量,他開始高頻率的出席宴會,在不同場合下進行推銷,這與初入大學意氣風發的房龍判若兩人.
幸而皇天不負苦心人,房龍的付出終于得到回報.1921年《人類的故事》剛一問世,便在出版界一炮走紅,并獲得最佳兒童讀物獎,而房龍也因此廣為人知,一躍成為暢銷書作家.[1]由此,房龍的作品開始受到廣泛關注,而房龍在1921年以后又接連出版了《圣經的故事》《寬容》《美洲的故事》《倫勃朗的生平與時代》《房龍地理》等一系列著作.
1.2 《房龍地理》簡介
在房龍眾多的著作中,在地理界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房龍地理》.促使房龍創作此書的原因是源于讀者的一封信,這位讀者在信中告訴了房龍他的困擾,他控訴自己明明努力學習地理知識,但在應用時,還是不得不查詢百科全書.而現階段圖書市場上的地理書籍都是屬于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的堆積,沒有聯系、枯燥且難以記憶.所以他希望房龍可以為了和他有同樣困擾的讀者寫一本書——一本不是知識堆積,而是充滿趣味性的書.他的要求是“把所有的高山、城市、大海統統放進地圖里,只告訴我們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的情況,告訴大家他們為什么會居住在那里,他們來自哪里,他們在干什么——把人類關心的故事寫進地理學”.房龍最終花費十年寫成此書,并在告讀者部分用了這位讀者的信作為其書的介紹,并做出了回應:“親愛的,這就是(你想要的書)”.[2]前言1-2《房龍地理》一書于1932年發行,本書最初只有十六章,后經修訂擴展到四十七章.
房龍將歷史融入地理,文筆生動詼諧,曾得到著名作家郁達夫的贊譽:“他的筆,實在巧妙不過,干燥無味的科學常識經他那么一寫,讀他書的人,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覺得娓娓忘倦了.”[3]60-61房龍打破了地理書籍的固有寫法,并沒有以地理風貌作為其重點的描寫對象,而是以人類為主線,通過描寫人在某種環境下怎么生活、環境對人的影響、環境對人的改變來為讀者介紹各個國家地理、政治、宗教等情況.《房龍地理》與其他地理書籍相比,它穿插了地理區域的歷史,讓讀者明白許多很難理解的知識從哪里來、是怎樣發展到現在難以理解的狀態,將地理的知識連成一片,成為系統有聯系的整體.這正是對房龍信奉的“歷史是地理學的第四維,它賦予地理學時間和意義”[2]前言1-2的踐行,而這也使得他寫出的地理知識更加豐滿,也更受讀者所喜愛.
1.3 《房龍地理》的發行概況
1932年,《房龍地理》在美國一經出版,便立即引起轟動.僅在出版的幾個月內,就在美國售出了近14萬冊.第二年,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以及中文等14國文字的譯文本便相繼出現.[4]隨著“二戰”的爆發,許多科學知識傳播活動逐漸停滯,《房龍地理》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出版數量銳減.到了戰爭中期,世界各國對科普的熱情逐漸高漲,但關注點已經逐漸轉向戰時科普,《房龍地理》并未重新得到關注,出版數量仍處于下降趨勢.
1945年“二戰”結束后,科普事業逐漸恢復并繁榮起來,美國圖書市場出現了大量的適合各年齡段的生動詼諧、圖文并茂且與房龍風格相似的非小說類書籍,《房龍地理》逐漸被取代.再加上房龍已經去世,無人去修訂《房龍地理》,其中很多知識已經與時代脫節,以至于《房龍地理》的出版數量持續下滑.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國外圖書市場更是無法找到《房龍地理》的蹤跡.
2 20世紀《房龍地理》在中國的發行歷程
2.1 《房龍地理》中譯本首次出現
“五四”時期,中國掀起了翻譯大潮,20世紀20年代-30年代,隨著各國的譯作開始大量涌入中國,美國文學也開始以此方式被大規模的介紹和引入.[5]《房龍地理》作為一本在世界范圍熱銷的書籍,自然也就進入了翻譯者的視線.《房龍地理》于1932年在美國出版,次年,中國便出現了中文版.《房龍地理》中譯本進入中國后隨即贏得許多讀者的喜愛.在這一時期,《房龍地理》中譯本處于暢銷狀態.[6]
2.2 《房龍地理》發行停滯
自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末,在長約50年的時間跨度里,《房龍地理》中譯本在中國市場未見其蹤跡.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先后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20世紀50年代的國家建設和學習蘇聯的熱潮,此階段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蘇聯著作上,對其他外文著作的關注則較少.據翻譯家卞之林統計,中國在1949年10月-1958年12月期間,翻譯的蘇聯文學作品“共3526種,占此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藝術作品總數的65.8%;總印數82005000冊,占整個外國文學譯本總數的74.4%”.[7]173
雖然中國對其他國家譯著的關注較少,但對美國優秀著作的關注度顯然更低.這與當時的國際大環境有關.20世紀50年代,冷戰已拉開序幕,以美蘇兩國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在不斷升溫.當時中國和蘇聯“老大哥”關系更為密切,美國對中國采取了敵對政策.[8]中美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以至于美國圖書在1949年至“文革”結束之前,進入中國讀者視線的數量極少.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房龍地理》未能重新發行.
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隨著尼克松總統訪華開始緩和.1979年,中美結束了近30年的不正常外交狀態,并且開始正式建交.這為美國譯作進入中國營造了良好的國際氛圍.自此,美國譯作開始大量涌入中國市場,房龍作品也得以有機會重新進入中國讀者的視線.
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逐漸意識到翻譯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人文思想的重要性.翻譯界由于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也掀起了浪潮,迎來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第二次翻譯熱潮.這次熱潮的主流以西方文學為主,與此同時,社會科學著作也開始被大量翻譯.[7]217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后,中美兩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也日趨密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讀者迫切地希望通過美國譯著了解美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因此,中國對美國譯著的介紹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發展.[5]677此時房龍的作品開始進入中國讀者的視線,如《寬容》一書,由于社會進入改革發展的狀態,也需要寬容的氛圍.于是房龍的《寬容》一書于1985年重新發行,[6]為引進房龍的其他作品做了鋪墊.
20世紀80年代,已經有很多美國著作進入中國,但《房龍地理》卻并未重新發行,主要是受人文地理命運的影響.由于房龍在書中更加關注地理學的人文意義,[9]《房龍地理》的發行狀況與人文地理在中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系起來.《房龍地理》一書在中國的發行經歷了盛行、沉寂、恢復發行和暢銷四個階段.而現代人文地理學也在中國經歷了衰落(1949-1979)、復興(1980-1990)和全面發展(1990年以來)幾個階段,[10]《房龍地理》在中國的發行情況實際上是現代人文地理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
《房龍地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并未發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此階段逐漸式微的人文地理尚未恢復.地理學在最初由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兩部分組成,人文地理一直是地理學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49-1979年,中國主張向蘇聯學習,地理學科為了響應這一號召,從蘇聯引入經濟地理,全盤學習蘇聯.當時蘇聯地理學界普遍認為,地理學是由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所組成,[11]140經濟地理從而取代了人文地理成為地理學的兩大分支之一,而人文地理則遭到全盤否定.當時人文地理被認為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偽科學,從而喪失了作為一門學科的價值.
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中國獲得了更多和其他國家地理界交流的機會,中國開始逐漸意識到人文地理的價值.1981年,中國地理學會舉行了人文地理學研討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關于人文地理的研討會.[11]研討會對人文地理的發展歷史、國外研究現狀及后期發展進行了討論,隨后又開了多次人文地理學研討會.1984年,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相關的各項工作開始有序進行,這一時期,中國開始大量的翻譯關于人文地理的外國圖書、論文,試圖將國外更多優秀的人文地理論著引入中國,來彌補中國在這一方面的不足.20世紀90年代以后是人文地理全面高速發展的階段,伴隨著這股春風,《房龍地理》也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
2.3 《房龍地理》重新發行
《房龍地理》得以重新發行不僅是人文地理的復興,還有翻譯熱潮的推動.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逐漸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但由于世界版權公約的束縛,翻譯運動于1993-1994年期間陷入低谷.1994年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中國出版行業對世界版權公約的逐漸了解,中國的翻譯運動又迅速興起.[12]這也推動了《房龍地理》的重新發行.《房龍地理》是作為一本地理書籍重新出現在中國讀者的視線中.在馬祖毅的《中國翻譯通史現當代部分》的地理部分就曾提到地理著作《房龍地理》.[5]
《房龍地理》再次發行的背后所蘊含的不僅是人文因素的影響,所起的更大作用是國際格局的巨大變化.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上的超級強國,而中國開始受到影響,選擇的翻譯作品開始大程度傾向于美國.
2.4 《房龍地理》迎來暢銷
21世紀初,由于美國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在全球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翻譯界引進的美國譯著開始增多.房龍的作品也隨著大規模的翻譯活動進入了中國.房龍的16本圖書作品,除了少數幾本書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國,大部分作品都是在21世紀初進入中國讀者的視線,其中《人類的故事》《房龍地理》《寬容》《圣經的故事》等書更是被大量翻譯,出現多個譯版.根據《房龍地理》版本的收集情況,可以看出,雖然《房龍地理》在20世紀90年代里恢復發行,但并未暢銷.在筆者搜集的中譯本中,僅有3個版本是在這一時間段出版發行的.僅在2000-2019年,筆者搜集的《房龍地理》不同的中譯本就有41本,而在搜集過程中有許多版本因為找不到出版時間或出版社無法收入,所以《房龍地理》從2000年到2019年翻譯發行的版本數量可能要遠大于41本.由此可以認為,《房龍地理》真正在中國暢銷的時間是在21世紀初.
在21世紀初,《房龍地理》不僅是作為地理書籍被翻譯,而更多的是被作為一個著名作家的作品而被翻譯.在這一時期,翻譯家開始將更多精力集中在思考《房龍地理》可以從哪些方向進行改進,其關注點也逐漸開始從地理知識上偏移,開始對《房龍地理》進行了所謂的“改良”.他們開始從思考這本書的插圖是否過于老舊;一些語言是否過于西方,不便理解;有些部分的描述錯誤過多,是否可以將其改進等一系列問題,也導致圖書市場上出現了多種多樣不同的《房龍地理》.
在改良版的《房龍地理》中有從寫作技巧,也就是文筆優美程度去賞析《房龍地理》,而這一方向的轉變,使得其更加滿足兒童的閱讀需求.《房龍地理》被教育部列入《語文新課標》指定閱讀書目,使得市場上改編版的兒童《房龍地理》,即《地球的故事》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
3 《房龍地理》的版本分析
21世紀初,《房龍地理》中譯本出現數量如此之多,除了作品本身優秀之外,還有就是自21世紀以后,中國開始將目光更多地投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建設,這促使在21世紀譯著呈現“井噴”現象.但與之而來的卻是翻譯質量下降,并且出現出版社為了經濟利益,假借外國作品之名的現象,以至于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偽書”.[12]《房龍地理》中譯本在21世紀初也有部分版本存在這樣的現象.市場上的中譯本良莠不齊,譯作雖以《房龍地理》為名,但譯者已經進行了改編,甚至改寫.所以21世紀初,在市場上暢銷的《房龍地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只是《房龍地理》招牌下的產物,但如果想要真正的去了解《房龍地理》,可能需要去進行多方對比,才能達到真正了解《房龍地理》的精華的目的.
筆者在中國圖書市場里,搜集到了《房龍地理》普遍發行的五個版本,試圖通過分析給予讀者一些閱讀建議.這五個版本分別是1997年趙紹棣、黃其祥翻譯,由國際文化出版社發行的《房龍地理》;2007年黃一少翻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發行的《房龍地理》;2013年文思翻譯,中國華僑出版社發行的《圖解房龍地理》;2016年白馬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地球的故事》;2016年鄧敏華翻譯,吉林大學出版的《地球的故事》.
筆者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以解讀原本的《房龍地理》為目的,所以筆者以章節的長標題、手插畫、譯者序言等幾個具有原著特色的點作為衡量標準.對比幾個版本,1997年趙紹棣、黃其祥翻譯的這一版本是中國恢復發行以后可以找到的較早版本,這一時期中國對《房龍地理》持全方位接受的態度.所以在這一版本里,《房龍地理》的所有細節幾乎無刪減和增添,從目錄便能看到房龍的特色——長標題.稍有不足的是其沒有對房龍手插畫上的地名進行翻譯,但并不能否定其貢獻,它仍是保留《房龍地理》完整度較高的版本.
2007年的版本與1997年的版本相比最直觀的變化是書中的手插畫變成了一幅幅經典的世界名畫,內容上增加了一些對油畫的敘述,對房龍的一些想法進行刪除,語言風格更加直白、平穩,更加貼近生活語言,使其風格與其他書籍無異.這種改變雖然讓《房龍地理》更加趨同于現在的圖書風格,但是卻失去了房龍的文筆風格.另外在目錄上也缺失了房龍著作的長標題特色,將其改為短標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讓《房龍地理》更好地融入中國的圖書市場,但缺失了原有的意味.
2013版與2007年的版本相比似乎又有回歸經典的勢頭.書中內容更多的選擇保留原文,只是在形式上選擇放棄了手插畫,將經典的彩圖插入其中.但與2007年的版本相比,此版更為用心,插圖不會過于突兀.雖然房龍特色的長標題被替換為短標題,但在整體上保留了房龍的文筆特色,筆者認為是回歸經典的一個開始.
2016年白馬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地球的故事》,可以說是徹底的回歸經典.這版在保留原著風格的基礎上對其細節及語言進行適當的選擇,其語言更加生動.此書譯者白馬曾多次翻譯房龍的作品,他在序中也指出了《地球的故事》①房龍地理的別稱.的不足及與現在時代不符的錯誤,并提及自己為什么翻譯此書的原因,以及閱讀此書時對哪些部分需要保持警醒,讓讀者去感受真正的《房龍地理》.在這一版本里我們隨處可以看到房龍的影子:獨特的長標題、簡單的手插畫、表達希望讀者怎么使用這本書的序.這些都使讀者可以更加真實地認識到房龍作品的魅力,還原了房龍作品的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讀者市場.
2016年由鄧敏華翻譯、吉林大學出版的《地球的故事》,則無疑是對《房龍地理》的改頭換面.因為它是作為小學教材要求的課外讀本而被出版,讀者對象是兒童.書中的內容被大量刪減,將適合兒童閱讀的部分文字進行保留并用夸張生動的語言去迎合兒童的閱讀興趣點,并配有適合兒童的彩圖插畫,還對一些內容進行一定的批注解讀.但此版更多的是用來欣賞房龍的文筆特色,側重點集中在哪一句用了什么修辭手法,使用這樣的修辭手法的好處,使《房龍地理》完全成了中國兒童版的《地球的故事》.
筆者認為如果寄希望于了解原版的《房龍地理》,可能更適合去閱讀白馬在2016年翻譯、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地球的故事》.另外,《房龍地理》的盛行與英語成為全球性語言也是分不開的.如果讀者想通過閱讀《房龍地理》的英文版來補充地理知識、學習英語,筆者推薦劉乃亞、紀飛的中文導讀《房龍地理》.此書也符合上文筆者提到的有譯者的序,而且作者會對每一章節進行介紹,幫助讀者去把控大的方向,留給讀者充分的學習空間,適合用于英語學習的書籍.

表1 《房龍地理》中譯本統計Tab.1 Statistics of various Chinese versions of Van Loon's Geograph
4 結語
縱觀《房龍地理》在中國的發行情況,不難看出《房龍地理》中譯本首次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但沉寂期長達大半個世紀.《房龍地理》中譯本的發行歷程中是受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其中不乏政治、經濟的因素.
首先,一本書的發行并不只是取決于其內容質量的高低,可能更多地取決于社會在不同時代的需求.這個需求不僅指的是對書本內容的需求,還有對書本背后所代表的國家的文化、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需求.就如筆者所提到的《房龍地理》最先發行就迎來熱潮,這與當時大環境渴望了解西方文化以及書籍迎合了對白話文推廣的需求都不無關系.《房龍地理》在中國發行的沉寂期長達五十多年之久,在這個過程中,更多的是受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
其次,《房龍地理》中譯本的出版情況可以映射在整個翻譯史中,美國文化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影響,也是不同時代中美兩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差異的透射.《房龍地理》在中國經歷了長達50年的沉寂期,它不單是因為中國人民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文革”等事件,還與國家在政治上的選擇有關.在美蘇冷戰時期,中國采取“一邊倒”政策,而美國對中國采取封鎖、遏制和拒不承認策略,這使美國文化無法進入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房龍地理》恢復發行,這也離不開政治大環境的影響.中美建交,美國成為世界上的超級強國使得《房龍地理》中譯本再次出現成為可能,而美國在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所呈現的強大的綜合實力以及英語成為全球性語言,更促使中國在引進外文譯著的選擇上偏向美國.
最后,就《房龍地理》的版本分析而言,一部優秀的譯作,不但需要深厚的語言功底,更需要的是對原作者的了解,明白作者在書籍內容設定上所要表達的東西,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補充說明.另外,一個包含譯者的自序也極為重要,讓讀者明白本書的閱讀價值,以及書中可能出現的錯誤,給讀者一個正確的引導.
致謝: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感謝張九辰教授給予悉心指導,同時也感謝中國科學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李子威給予的大力幫助,在此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