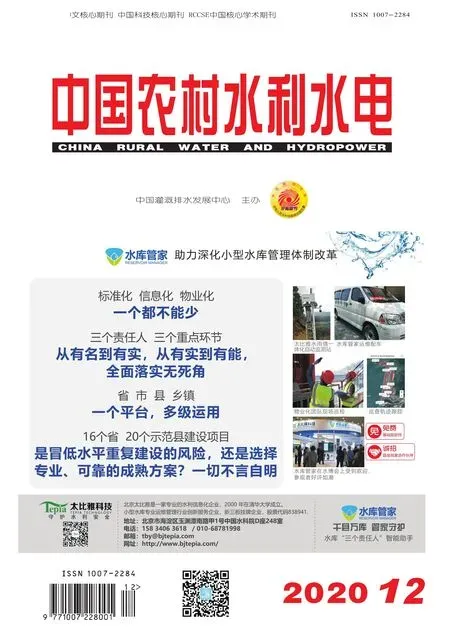不同水肥綜合調控模式下水稻生長特征、水肥利用率及氮磷流失規律
劉路廣,陳 揚,吳 瑕,余乾安,潘少斌,楊小偉,王 敬,王麗紅
(1.湖北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武漢 430070;2.湖北省節約用水研究中心,武漢 430070;3.中建三局綠色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武漢 430056;4.武漢大學 水資源與水電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武漢,430070;5.湖北水利水電職業技術學院,武漢 430070)
0 引 言
水稻是我國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其總產量占到了全國糧食作物總產量的40%左右[1,2],同時水稻也是農業中耗水量最大的作物,稻田灌溉用水量占農業總用水量的65%以上[3,4]。由于水稻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區,水稻生育期內降雨一般較為充沛但分布極不均勻,雨水往往沒有被充分利用,反而造成了田間養分的流失[5,6]。肥料的施用對水稻產量的形成有重要意義,也是水稻生產投入成本的主要部分[7]。氮肥在化肥中投入量占比最大,全國平均單季水稻氮肥施用水平為180 kg/hm2,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75倍[10-13],氮肥平均農學利用率(單位施氮肥量增加的產量)不到農業發達國家的50%[14],氮肥中的很大部分通過揮發、徑流、淋溶等途徑流失到地表水、地下水及大氣中[15],破壞了水生生態系統的平衡[16,17],造成了嚴重的水體、土壤污染[18]與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19,20]。基于以上問題及現狀,如何實現產量、水肥利用率及環境效應的協同提高是田間水肥調控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問題[21-24]。為解決該問題,需要進一步探明水稻生長與水分養分之間的作用機制,充分發揮水肥耦合效應在高產前提下達到節水、減排的目的,因此,開展田間水肥調控試驗研究對節約水肥資源與環境保護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與應用價值。
1 試驗設計
1.1 試驗處理
該試驗在湖北省中心站試驗小區內進行。試驗處理主要考慮灌溉模式、施肥水平和施肥方式3個因素,其中施肥水平和施肥方式僅針對氮肥開展處理設計,磷肥和鉀肥施肥水平及施肥方式與農民現有施肥習慣一致。
灌溉模式:常規淹灌模式(W0)、間歇灌溉模式(W1)、蓄雨型間歇灌溉模式(W2)。不同灌溉模式稻田水層控制標準見表1。

表1 不同灌溉模式全生育期水層控制標準
施氮水平:不施氮肥處理(N0)、當地實際施氮水平(N1):180 kg/hm2(折純量,下同)、當地施氮水平的75%(N2):135 kg/hm2。磷肥及鉀肥所有處理施肥量均相同,磷肥(P2O5)施肥量40 kg/hm2,鉀肥(K2O)施肥量70 kg/hm2。
施肥方式:基肥+一次追肥(基肥∶蘗肥=50%∶50%)F1、基肥+二次追肥(基肥∶蘗肥∶穗肥=50%∶30%∶20%)F2。氮肥施基肥時使用碳酸氫銨,施追肥時使用尿素;磷肥與鉀肥于施基肥時全部一次施入,磷肥使用過磷酸鈣,鉀肥使用氯化鉀。基肥在整田插秧時施入,孽肥在插秧后15 d左右施入,穗肥在插秧后60 d左右施入。
由于場地有限,對于蓄雨型間歇灌溉模式(W2),只進行不施氮肥N0與施氮肥N1F2處理。田間小區試驗共計12個處理,每個處理重復數為3,共計使用36個試驗小區。
1.2 采樣分析方法
灌水量、排水量均可通過灌(排)水前后田間水層深度的差值進行計算,田間耗水量通過觀測逐日(每日上午8時)水層變化量進行計算。水位觀測采樣人工觀測與HOBO自記水位計相互校核。深層滲漏量通過每隔5~7 d觀測測滲筒內水深變化獲得。作物需水量通過逐日田間耗水量減去逐日田間滲漏量得到。
水稻生育期劃分根據《灌溉試驗規范》(SL 13-2015)規定進行;物候觀測從返青期開始,約10 d左右觀測1次水稻分蘗數及株高,然后按小區平均分蘗數取典型植株3蔸,進行葉面積指數、干物質積累量調查。測產考種于收獲前1 d開展,每個小區調查有效穗數30蔸,取代表植株5蔸考種,考察每蔸有效穗數、總粒數、空粒數、實粒數、結實率、千粒重;收獲時,每個小區取中間3個1 m2區域進行測產。
田面水樣取樣:在施肥后的第1、3、5、7、9 d及田間排水后進行取樣,水稻每個生育期至少取樣一次,化驗分析在取樣后24 h內完成,水樣多時置于4 ℃環境下低溫保存。
滲漏水樣取樣:在每個試驗小區布置穿過耕作層的PVC管(埋藏深度20、40、60 cm),管下部打數個小孔收集滲漏水,每次取樣時提前用小型手提式水泵抽干管內水,4~5 h后使用水泵再進行取樣,取樣時間與田面水取樣時間相同。
水樣TN濃度測定采用堿性過硫酸鉀消解,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方法;TP濃度測定采用過硫酸鉀消解,鉬酸抗顯色,分光光度計測定方法;硝態氮測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方法;銨態氮測定采用納氏試劑顯色,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方法。
各試驗小區在泡田前和收割后使用土鉆分耕作層上層(0~20 cm)、下層(20~40 cm)采集土樣,在每個小區中間部位取樣,將土樣混合、風干后對其總氮、總磷含量進行測定。土樣TN含量測定采用H2SO4消化土樣,自動定氮儀蒸餾,酸式滴定管滴定方法(半微量凱氏法);土樣TP含量測定采用HClO-H2SO4消化土樣,鉬酸抗顯色,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方法。
水稻氮磷觀測指標包括水稻地上各部分總氮、總磷含量。收割后按平均分蘗數取植株樣3蔸,洗凈烘干后分為莖桿、葉、籽粒三部分進行總氮、總磷含量測定。植株TN測定采用濃硫酸、過氧化氫聯合氧化,自動定氮儀蒸餾,酸式滴定管滴定方法;植株TP測定采用濃硫酸、過氧化氫聯合氧化,鉬銻抗顯色,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方法。
2 不同水肥調控模式下水稻生長特性指標及產量
2.1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分蘗數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分蘗數動態變化見圖1(a)。由圖1(a)可知,不同水肥處理下水稻分蘗數變化趨勢并不相同,其變化趨勢差異主要由灌溉模式不同而引起。常規淹灌(W0)下水稻分蘗數從返青期開始不斷增長至分蘗后期達到最大,拔節孕穗期至抽穗開花期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之后保持相對穩定;間歇灌溉(W1)下分蘗數從返青期開始不斷增長至拔節孕穗期達到最大,抽穗開花期略有下降,之后保持相對穩定;蓄雨型間歇灌溉(W2)下分蘗數變化趨勢介于W0與W1之間,分蘗數從返青期增加至分蘗后期達到最大,拔節孕穗期至抽穗開花期略有下降,之后保持相對穩定。

圖1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生長特性及產量
同一施肥模式,生育前期(返青期~分蘗期)W1、W2下水稻分蘗數均小于W0;生育中后期(拔節孕穗期~黃熟期)W1、W2下N1F1、N2F1、N2F2處理分蘗數不斷接近并最后超過W0,而W1、W2下N1F2處理分蘗數仍小于W0。表明W1、W2下適當的干濕交替對生育前期水稻分蘗產生形成了一定抑制,有效控制了無效分蘗,有利于中后期分蘗數的維持與穩定,W0下稻田水分充足,使水稻產生了過多的分蘗數,生育中后期水稻水分或養分受限時分蘗數易快速下降。與W1相比,W2下施氮肥處理分蘗數略大于W1,不施氮肥處理W2分蘗數普遍小于W1。表明施氮肥下由于分蘗期降雨較集中,W2較W1田間水分更為充足,促進了水稻的分蘗;不施氮肥下水稻缺少養分根系發育不良,W2較大的蓄水深度給水稻生長發育帶來了明顯不利影響。
不同施氮水平下,施氮肥處理水稻分蘗數顯著大于不施氮肥處理,且低施氮組分蘗數均小于高施氮組。表明在一定范圍內增加施氮量可有效促進水稻分蘗的產生與維持。不同施肥次數下,除W0N2處理外,二次追肥下水稻生育前期分蘗數均低于一次追肥,但黃熟期二次追肥與一次追肥差異不大甚至略有超過,而二次追肥下W0N2處理全生育期分蘗數均較顯著低于一次追肥。因此一定施氮水平下增加追肥次數可有效控制無效分蘗的產生,但同時需考慮到水稻各生育階段的基本養分需求。
2.2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株高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各生育期株高動態變化見圖1(b)。由圖1(b)可知,不同水肥處理株高總體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株高從返青期至乳熟期不斷增長,黃熟期保持穩定。
同一施肥模式不同灌溉模式下,W1、W2下水稻株高生育前期均略低于W0,生育中后期逐漸接近W0甚至略有超過,表明W1、W2下水稻生育前期由于一定的干旱脅迫株高略小于淹灌,但生育中后期水稻的株高增長有明顯反彈。與W1相比,W2下施氮處理生育前期水稻株高略高于W1,生育中后期株高基本與W1保持一致;W2下不施氮肥處理生育前期與W1差異不大,生育中后期略低于W1處理。
不同施氮水平下,施氮肥處理水稻株高均明顯高于不施肥氮肥處理;低施氮量處理相較于高施氮量處理,一次追肥下低施氮量處理株高與高施氮量處理差異不大,但二次追肥下低施氮量處理株高明顯低于高施氮量處理。表明一定范圍內降低施氮量對株高的影響不明顯,但施氮量降低到使水稻生育某一階段缺少養分時,對水稻的株高增長會產生明顯的抑制。
不同施肥次數下,高施氮量下二次追肥處理與一次追肥處理水稻株高之間差異性很小,但低施氮量下二次追肥處理株高明顯低于一次追肥處理。表明在一定施氮水平下,增加追肥次數對水稻株高增長影響不大,但增加追肥次數使水稻生育某一階段缺少養分時,會對水稻的株高增長產生一定的抑制。
2.3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葉面積指數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葉面積指數變化見圖1(c)。由圖1(c)可知,不同水肥處理下LAI變化趨勢大致相同:LAI從返青期至拔節孕穗期水稻快速上升達到峰值,拔節孕穗期至黃熟期緩慢下降。表明水稻葉片部分的生長主要在返青期至拔節期孕穗期,之后葉片生長速率逐漸小于衰老速率,LAI不斷下降。
同一施肥模式不同灌溉模式下,W1、W2下水稻LAI全生育期LAI均普遍小于W0,拔節孕穗期相差達到最大,之后不斷減小。與W1相比,W2下施氮肥處理LAI全生育期均大于W1處理,且W2下黃熟期水稻LAI明顯高于W1處理;W2下不施氮肥處理水稻全生育期LAI基本小于W1。
不同施氮水平下,施氮肥處理水稻LAI均明顯高于不施肥氮肥處理,且LAI有隨著施氮量增加而增加的趨勢。這說明一定范圍內增施氮肥有利于水稻LAI的增長與保持。不同施肥次數下,分蘗前期至拔節孕穗期二次追肥處理水稻LAI基本高于一次追肥處理;第二次追肥后,抽穗開花期至黃熟期二次追肥處理LAI逐漸接近并超過一次追肥處理。因此在一定的施氮水平下,增加追肥次數有利水稻生育中后期LAI的保持。
2.4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變化見圖1(d)。由圖1(d)可知,不同水肥處理下水稻干物質積累量變化趨勢大致相同:從返青期至分蘗后期增長較快,從分蘗后期到拔節孕穗期增長速率有所放緩,從拔節孕穗期到乳熟期增長速率達到全生育期最大,乳熟期至黃熟期保持穩定或略有下降。
同一施肥模式不同灌溉模式下,W1下水稻干物質積累量生育前期普遍低于W0,而W2干物質積累量與W0差異很小;生育中后期W1、W2干物質積累量均逐漸超過W0。主要因為W1、W2處理干濕交替有利于生育的水稻根系發育,生育中后期水稻能吸收更多的水分及養分。與W1相比,W2下施氮肥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均高于W1,但黃熟期W1與W2干物質積累量差異很小;W2下不施氮肥處理下干物質積累量基本小于W1。表明施氮肥下W2水稻在生長發育過程中莖葉生長更為茂盛,主要因為W2下田間水分較充足,對水稻莖葉的生長有促進作用;不施氮肥下W2水稻受淹嚴重,影響了水稻的干物質量積累。
不同施氮水平下,施氮肥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顯著高于不施氮肥處理。一次追肥下低施氮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相對高施氮處理略有下降,但總體而言差距并不明顯;二次追肥下低施氮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明顯低于高施氮處理。因此在一定范圍內減少施氮量對水稻干物質積累的影響不明顯,但低于一定限度后,施氮量減少會明顯抑制水稻的干物質積累進程。
不同施肥次數下,高施氮量下二次追肥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生育前期低于一次追肥處理,第二次追肥后逐漸接近并超過一次追肥處理;低施氮量下二次追肥處理水稻干物質積累量全生育期均低于一次追肥處理。表明一定施氮水平下,增加施肥次數有利于生育后期水稻的干物質積累量的增加,但同時需要考慮到水稻各階段正常生長的基本需求。
2.5 不同水肥處理水稻產量
不同水肥處理下水稻產量見圖1(e)。由圖1(e)可知,同一施肥模式不同灌溉模式下,與W0相比,W1、W2水稻產量均有所增加,平均增產6.1%與2.7%。與W1相比,W2下施氮處理產量減少了5.1%,產量有所減少可能因為W2下生育前期水分過充足,水稻產生了較多無效分蘗,與中后期的生殖生長形成了競爭,影響了最終產量,因此對于W2,可適當降低前期的蓄水上限,避免稻田長時間淹水。
不同施氮水平下,施氮肥處理產量均顯著高于不施氮肥處理,說明施氮肥對水稻產量形成有明顯促進作用。一次追肥下低施氮量與高施氮量間產量差異不大,但二次追肥下低施氮量處理產量均較顯著小于高施氮量。因此,較高施氮水平下減少施氮量不會明顯影響稻田產量,但減少到一定限度后使水稻生長敏感階段缺少養分時,會帶來明顯的減產。
不同施肥次數下,高施氮量下二次追肥處理產量均高于一次追肥處理,但低施氮量下二次追肥處理產量明顯低于一次追肥處理。表明不同施氮水平下增加追肥次數對產量的影響有明顯區別,高施氮量下增加追肥次數可以有效增加產量,但低施氮量下增加施肥次數可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減產,主要是因為高施氮量下增加追肥次數有效地提高氮肥利用率,抑制了作物前期的無效分蘗,有利于產量的增加,但低施氮量下增加追肥次數使得水稻在分蘗期生長受到了過度的抑制,分蘗數、株高、葉面積指數均明顯降低,水稻中后期的生長得不到充足的養分供應,產量明顯降低。
3 不同水肥綜合調控模式下水肥利用率
3.1 不同水肥處理水平衡要素
不同水肥處理田間水量平衡要素匯總見表2。由表2可得,與常規淹灌(W0)相比,間歇灌溉(W1)、蓄雨型間歇灌溉(W2)下稻田灌水量分別平均減少15.3%與29.8%,灌水次數平均減少4次與5次,排水量平均減少15.4%與63.1%;與W1相比,W2下灌水量平均減少17.5%,灌水次數平均減少1次,排水量平均減少56.3%。表明W1適當的干濕交替可以有效地減少了田間灌水量、灌水次數及排水量;W2節水效果顯著,灌水量、灌水次數及排水量進一步下降,其中排水量下降幅度最大,主要因為W2在保持較低灌水下限的同時提高了蓄雨上限,充分發揮了水稻本身的耐旱耐淹特性及稻田的儲水能力。

表2 水稻全生育期不同水肥處理水量平衡表
2018年試驗降雨利用率總體較高,主要因為灌溉后基本未發生強降雨,雨水得到了高效利用。與W0相比,W1、W2下降雨利用率分別平均上升了5.1%與20.4%,與W1相對,W2降雨利用率平均上升了15.3%。表明W1通過降低灌水下限可以一定程度提高降雨利用率;W2降雨利用率得到顯著的提升,大部分降雨都被儲存在稻田,降雨利用率達88.1%。
與W0相比,W1、W2田間滲漏量分別下降了19.5%與上升了5.7%;與W1相比,W2田間滲漏量上升了26.4%。主要原因是W1無水層時期田間滲漏速率減少,滲漏量明顯減小;W2在蓄雨時期田間水位高,滲漏速率增大,滲漏量明顯增加。
與W0相比,W1、W2平均蒸發蒸騰量分別上升了4.0%與8.6%;與W1相比,W2平均蒸發蒸騰量上升了4.3%。本次試驗 W1、W2蒸發蒸騰量略有增加可能因為W1、W2作物根系較為發達,生育后期作物蒸騰量有一定程度提高。
3.2 不同水肥處理氮磷排放規律
不同水肥處理田間氮磷排放總負荷見表3。由表3可知,相同施氮肥處理下,相比于W0,W1、W2稻田TN排放負荷平均減少26.0%與53%;TP排放負荷平均減少11.0%與31%;相比于W1,W2下稻田TN排放負荷減小了39%,TP排放負荷減少29%。表明相比W0,W1可有效減少稻田氮磷排放負荷,而W2對于控制稻田氮磷排放效果更顯著。

表3 不同水肥處理下氮磷排放總負荷
不同施氮水平下,TN排放負荷明顯隨著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因為施氮使得田面水及滲漏水的TN平均濃度均顯著增加。
不同施肥次數下,F2處理相對于F1處理氮磷排放負荷顯著減小,W1N1、W1N2、W0N1、W0N2下F2處理比F1處理總氮分別減少了41.5%、43.9%、16.4%、25.7%,平均減少31.8%。說明適當的增加施肥次數可以有效地減少田間的氮磷排放負荷,主要因為田間排水主要集中在第一次追肥與第二次追肥之間,同時F2處理田間滲漏量TN平均濃度也要低于F1處理。
3.3 不同水肥處理氮肥利用率
由表4可知,不同灌溉模式下水稻氮肥利用率變化規律不一致。相比W0,除N2F2處理外,各施氮處理下W1、W2水稻氮肥利用率平均上升了5.2%與5.1%,但N2F2處理下W1處理相較于W0下降了14.7%;相比W1,W2的氮肥利用率上升了3.8%。表明灌溉模式對水稻氮肥利用率的影響與施氮肥制度有一定聯系,在一定施氮水平下,W1相對W0可以提高氮肥利用率,但水稻同時受到干旱脅迫及養分脅迫可能使W1氮肥利用率低于W0,主要因為N2F2下水稻生育前期缺少養分,W1下一定程度干旱脅迫對水稻產生了不可逆的生長抑制。W2與W1相比氮肥利用率略有提高,但主要因為W2下不施氮處理吸氮量明顯小于W1,而施氮處理下W2吸氮量與W1無明顯差異,表明W2與W1氮肥利用率較為接近。

表4 不同水肥處理氮素吸收利用指標
不同灌溉模式下,相比W0,W1、W2平均氮素收獲指數分別上升4.0%與下降4%;相比W1,W2氮素收獲指數下降了7.9%。表明W1有利于氮肥更多地向籽粒轉移;W2氮素收獲指數有所下降,主要因為W2處理收獲時葉面積指數仍比較大,過多占用了水稻總吸氮量,氮素收獲指數下降。
不同施氮水平下,一次追肥、二次追肥處理施氮量降低對水稻氮素利用率的影響有明顯差異,一次追肥處理減少施氮量氮素利用率有所上升,二次追肥處理減少施氮量氮素利用率反而有所下降,表明施氮水平改變對氮素利用率的影響與施肥次數有關。施氮水平對氮素收獲指數的影響不明顯。
不同施肥次數下,除W1N2處理外,各施氮處理二次追肥下氮素吸收利用率均高于一次追肥,因此一定施氮水平下增加追肥次數能提高氮肥利用率,但也需要考慮水稻生育各階段的基本要求。各施氮處理二次追肥下氮素收獲指數均略低于一次追肥,表明增加追肥次數會延緩莖葉的衰老,氮素更多地分配到水稻莖葉中。
4 結 論
(1)與淹灌相比,間歇灌溉可合理抑制水稻前期生長,有利于水稻后期生長及高產;與間歇灌溉相比,蓄雨型間歇灌溉會促進水稻全生育期生長,但后期莖葉過盛使產量略有減少;增加施氮量可促進水稻的生長發育與高產,但超過一定限度后效果有限甚至產生負效應;高施氮量下增加追肥次數可促進水稻后期生長與高產,但低施氮量下增加追肥次數可能使作物前期缺少養分,產生相反效果。
(2)灌溉模式是稻田水量平衡要素的主要影響因素。與淹灌相比,間歇灌溉下稻田節水15.3%;與間歇灌溉相比,蓄雨型間歇灌溉下稻田節水17.5%。
(3)不同水肥處理下,田面水及滲漏水氮磷濃度大小主要與施肥量及施肥時間相關,氮磷排放負荷大小主要與排水量、滲漏量及排水時間相關。與淹灌相比,間歇灌溉下總氮排放負荷減少26%、總磷排放負荷減少11%,有利于稻田土壤氮磷肥力的維持與氮肥利用率增加,且能促進氮素更多向籽粒轉移;與間歇灌溉相比,蓄雨型間歇灌溉下總氮排放負荷減少29%、總磷排放負荷減少39%,土壤總磷含量下降增加,氮肥利用率差異不大,但籽粒氮素占比下降;減少施氮量可明顯減少稻田總氮排放,對氮肥利用率的影響與施肥方式相關,對氮素分配的影響不明顯;增加施肥次數可減少稻田總氮排放,增加氮肥利用率,但同時也會增加莖葉氮素占比。
(4)從節水、減排及作物產量綜合效果來看,應優先推薦蓄雨型間歇灌溉模式,對于田埂高度較低、水源條件較好的地區,可以采用間歇灌溉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