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速度”再提速:改革書寫特區新傳奇
文/趙廣立 李晨 朱漢斌 溫才妃 刁雯蕙

圖/東方IC
科研不愁經費、人才不分國籍、辦學擁有自主權、創業不缺生態……這樣的創新創業“樂土”就在深圳。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下稱《實施方案》),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拿到“政策禮包”的深圳以開放、創新為翼,再次出發。
“這個文件作用非常大!”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給《實施方案》點贊,“40年的改革開放經驗告訴我們,發展不僅是資源問題,更是政策問題。”在他看來,《實施方案》中關于科技創新、人才、辦學、成果轉化等的開放政策,對社會發展意義重大。
科研經費雙軌制“一石三鳥”
任毅(化名)是中國農業科學院深圳農業基因組研究所(下稱“農科院基因所”)的副研究員,長期從事生物信息學研究。由其團隊開發的基因組學技術,由于性能較好,在應用中采納度較高。然而,一度讓任毅煩惱的是,生物信息學作為底層驅動技術,必須要跟其他領域應用結合才可以申請到競爭性課題,非常耗費精力。
2017年,深圳市開始實施科技創新“十大行動計劃”,其中包括在全市范圍內遴選出十幾家高水平的基礎研究機構或企業,每年提供1億元~2億元的穩定經費支持,高標準建設“十大基礎研究機構”。
“有了穩定的經費支持,這些基礎科研機構就可以根據自身的優勢,自主布局科研方向。”農科院基因所副所長錢萬強說,此舉一石三鳥。比如研究機構可以在生物信息技術領域自主布局,相關團隊也能沉下心來將精力放在算法開發上,之后還可以讓更多同行享受到生物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的支撐。
在《實施方案》中,黨中央和國務院肯定了深圳這一做法。《實施方案》明確:“支持實行非競爭性、競爭性‘雙軌制’科研經費投入機制”,體現了對深圳先行先試“探索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科研經費投入融合機制”的肯定和延續。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陳勁介紹,對高水平科研團隊來說,堅持競爭性、非競爭性“雙軌制”的科研經費投入機制,減少了重復性科研申報或科研評價,能夠使科技人員安心科研工作;但同時依然保留了競爭性,保留了讓能者“揭榜掛帥”的通道。
用才不問國籍,“來了就是深圳人”
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在建設之初,高級人才緊缺,經常要從北京搬救兵。如今,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了——不是不再缺人,而是他們從深圳也能招聘到合適的國際化人才。
自2016年以來,深圳通過高校等平臺頻頻牽手諾貝爾獎得主,在基礎科研與產業化方面開展合作,規劃建立十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諾獎實驗室的運轉也很靈活:不要求諾貝爾獎得主全職留在深圳,但每年至少一個月在深圳工作,而且要把實驗室的骨干和團隊帶到深圳。
“這方便了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等高校進一步與國際接軌。”陳勁表示,“硅谷經驗”證明,移民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創建創新園區非常關鍵。深圳率先強調國際人才引才用才力度,探索打造國際化移民城市,對在新型國際關系下吸引國外優秀人才到我國創新創業提供了更好的條件,也進一步實現了人才的多樣化。
“深圳的吸引力一定要做到比其他城市更大才行。全世界都在競爭,我們的吸引力在哪里?”徐揚生認為這要好好思考,包括制訂一些特殊的吸引政策。
《實施方案》提出,深圳要“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有研究者認為,此舉意在指向期待深圳盡快在科研人才、機構和高校的國際化聚合和提升方面實現重大突破。
科技創新發展中的人才問題,由吸引人才和培養人才兩方面組成。“來了就是深圳人。”徐揚生認為,吸引世界一流科學家和學者來深圳工作,對于深圳的創新氛圍有非常積極的影響。“過去,外籍人才在國內通常留不了太長時間,還有納稅和居住證方面的限制。”錢萬強表示,新政策應對外籍人才的身份、停留時間、納稅等方面出臺寬松的細則,吸引更多國際人才到深圳工作,幫助深圳市建成國際化都市。
擴大辦學自主權,深圳能否建成“斯坦福”
吸引人才是一方面,培養人才更為緊迫。
大概十一二年前,徐揚生在斯坦福大學前面的草坪上坐了一整天。“按照中國、按照深圳這樣的發展勢頭看,50年內我們國家會不會出現像斯坦福這樣的世界名牌大學?”
“我大概思考了一天,結論是:會。”徐揚生講道,“經過詳細的調研以后,我發現不僅能夠建成這樣一所大學,而且還可能建成一批這樣的大學,而且我認為這些大學應該出現在深圳這樣的地方。”
在支持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實施方案》明確深圳“探索擴大辦學自主權”——既包括“探索擴大在深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又囊括“在符合國家相關政策規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
“這個政策頒布得非常及時,因為真正要培養好的人才,大學要有特色,辦學要有自主權。”徐揚生認為,中央賦予深圳探索高等教育改革更多的自主權,有利于辦出有時代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人才培養模式。
依托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籌建的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暫定名),也在做這樣的探索。
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籌備辦主任樊建平稱,這所大學志在祖國南方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為深圳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注入源頭活力。
樊建平認為,創新本質上是一個試錯過程,中央支持深圳探索擴大辦學自主權,就是給出較大試錯空間,希望調動社會各方去參與、去試驗,好的體制機制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才能逐步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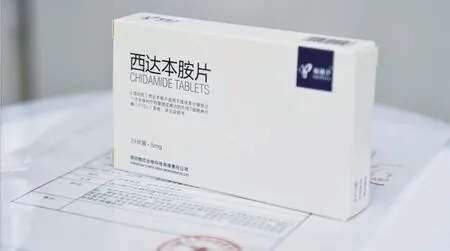
微芯生物原創藥“西達本胺”在2014年底獲批上市(圖/新華網)
創業者匯聚,這是“干實事的地方”
如果不是在深圳,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微芯生物”)可能早在2009年就“失敗”了。
微芯生物以開發原創新藥立身。2009年微芯生物因發展需要啟動產業化建設,但同時在開展的臨床研發同樣耗費巨大,雙重壓力之下,難以為繼。
一定要把微芯生物留在深圳。深圳市及時出手,幫助微芯生物代建產業化基地。在良好的產業環境下,“燒錢”的原創藥“西達本胺”終于在2014年底獲批上市。2019年,微芯生物成功登陸科創板。
“深圳這片充滿包容、公平、創新的沃土滋養了一批各行各業的領軍企業和優秀企業家,他們用自己的創新拼搏開創了令世界矚目的‘深圳速度 ’。”微芯生物創始人、董事長魯先平感嘆道。
作為創業者的圣地,深圳的創新創業環境持續向好。此次不僅《實施方案》強調深圳要堅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習近平總書記也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依法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
15年前,樊建平受中國科學院黨組委派,帶領團隊來深籌建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時候,也是一名“創業者”。如今,該研究院已初步構建出一套集科研、教育、產業、資本為一體的微型協同創新生態系統。
“我們在探索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模式,叫‘樓上樓下創新創業綜合體’,樓上是研究院,樓下是企業。企業跟研究院共用儀器設備,以低成本地開啟初創公司的運行,同時研究院為企業提供智力支撐,促進問題的有效解決。”
樊建平說,這種模式能有效縮短一些技術特別是生物醫藥領域技術落地的周期,助力科技初創企業跨越成果轉化“死亡谷”。
“走在前頭,干在實處。深圳是一個干實事的地方。”徐揚生說,深圳在創新方面有股敢闖敢干的精神,“如果沒有這個精神,深圳就不是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