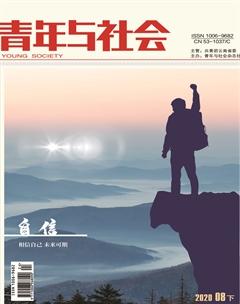算法傳播假新聞:危害、肇因及治理
王英明 張競文 柏首鋅
摘 要:算法傳播虛假新聞已經飽受詬病,造成社會公眾認知割裂、主流媒體話語權喪失、未知社會風險觸發等多種危害。從技術邏輯、算法偏見、公眾思維三個層面分析算法滋生假新聞的肇因,以領導者角度,著力培養輿論領袖、構建權威性媒體等方式加強對算法假新聞的治理。
關鍵詞:假新聞;算法傳播;輿論領袖
算法新聞是指在算法程序的引領下,人工智能依托自然語言生成技術自動生成大量新聞文本。其取代記者簡單勞動,具有快捷及時的作用,為新聞傳播帶來了諸多貢獻。然而,后真相時代情緒往往先于事實進行傳播。算法滋生的假新聞也帶來不容忽視的問題。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扎哈羅娃于5月28日表示,美國試圖利用假新聞使國際忽略俄羅斯在疫情處理方面的努力,使國際合作在應對全球威脅方面復雜化。
一、算法傳播假新聞的危害
算法假新聞不僅使得國際合作關系復雜化,更會造成公眾認知固化、主流媒體話語權沒落,甚至觸發未知的社會矛盾。民眾訴諸的事實反駁假象變得極為困難,事實逐漸失去主導社會共識的地位。
割裂社會公眾認知。其一,個體極化。人工智能算法基于公眾瀏覽記錄、數據信息精準推送相似新聞,使高度相似信息在封閉環境中傳播,使得公眾不斷強化自身偏好,并以自身喜好判斷事物,從而喪失對事物的判斷與分析。其二,群體極化。社會公眾逐漸形成對訊息的固有看法,算法推介使得轉發、評論、點贊相似的個體形成認同群體。群體形成強大的扭曲的認同并排斥觀點相左群體,甚至形成不同群體間的尖銳對立,加劇社會矛盾。其三,思維固化。算法形成的封閉傳播空間會割裂大眾對社會的認知,公眾新聞關注點和訊息需求點長期集中某一領域、某一話題,長此以往,使得公眾狂熱與情感形成一條價值鏈,喪失對社會問題和公眾問題的思考。
主流媒體話語權沒落。第一,官方權威受損。官方權威訊息經過取證、核實、編排等過程要經歷一段時間,依據算法產生的假新聞往往可以即時發布,對缺乏知識背景和謠言辨別能力的群體,容易釀成“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的悲劇,使得政府權威訊息雖真而無人信。第二,傳播系統情緒化。新媒體工作者為博得“眼球效應”,依托算法推送迎合公眾,增加訂閱和點擊量,訊息未經核實就極有可能先帶來流量,整個傳播系統中的信息傳播傾向于主觀化和情緒化。第三,正面引導缺失。隨著社會發展,公眾選擇網絡作為壓力的宣泄口,算法根據以往信息推送訊息往往過于同質化,娛樂化、“個性化”的需求隨之高升,甚至不免出現庸俗化、低俗化、扭曲化的需求,官方重大新聞、國家重大消息等往往被忽視,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無法得到有效的引領。
觸發未知社會矛盾。算法通過精準化的推送,成為部分人謀取利益的手段。通過發布社交媒體算法傳播的假新聞,中傷自己在事業有沖突的單位和個人,使得個體的人格、事業、生活受損,從而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營銷公司非法獲取公眾消費大數據,并通過精細化包裝,依托算法對受眾心理進行精準測量甚至惡意利用[1]。推送定制廣告與假新聞,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誆騙、引誘消費者,造成公眾財產損失。在西方,算法傳播的假新聞成為政黨交相攻訐的技術手段,西方國家在國內通過算法精準傳播假新聞,使公眾誤解、敵視對手國,造成國際局勢緊張。
二、算法傳播假新聞的肇因
算法傳播假新聞的機制有深厚的社會環境土壤,技術邏輯形成閉塞“回聲室”,人為操縱帶有偏見的算法程序,不斷割裂具有缺陷的社會公眾認知,形成“技術-算法-思維”所難以破解的假新聞。
技術邏輯。在算法推薦技術的影響下,公眾會普遍處于一種“回聲室”效應中。一些消息被不斷地重復和強調,人們就會逐漸相信并堅定地認為所見即事實。相較于傳統媒體,民眾更加傾向于從社交圈獲取新聞資訊、分享觀念見解,實際上,社交圈已經對信息進行了一次“價值過濾”,導致圈子內的價值觀念以及消息渠道嚴重趨同,就像處在一個封閉的房間環境中一樣,人們不斷聽到相似的聲音,不斷接受到相同的價值觀念熏陶,便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圈子足以帶來全部的事實,從而出現公共輿論的偏差。此外,公眾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過分推崇加劇這一現象,人工智能能在潛移默化中改變社會公眾的訊息接收、信息傳播與價值認同,使社會公眾天然地認為人工智能是有益無害的,事件的發展、評判、解釋被算法機制所操縱,由此建構起對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盲目信任。
算法偏見。社交機器人是最常見的假新聞創建者,算法是支撐其運作的底層技術。人工智能機器人獲取公眾瀏覽數據和信息,模擬人的行為,創作出精準推送的假新聞。基于此,公眾數據來源于社會,社會的個體和群體難免摻雜著虛偽、不公、邪惡、偏見、歧視等因素。智能機器人在合法信息傳播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算法的底層程序受到人為操縱和控制,算法編程自身也極易受到開發者的人為因素影響,甚至許多人仍然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偏見設計用于散播謠言、垃圾郵件、惡意軟件、錯誤信息、誹謗等虛假內容。原本技術進步通過非法數據、算法偏見、人為干預形成技術阻礙,使得虛假信息泛濫造成社會出現不良影響和危害性后果。
公眾思維。認知缺陷是假新聞產生的思維因素[2]。公眾中存在大量憑借直覺判定事實的認知風格,甚至存在容易產生妄想的個體。公眾相信自己的觀點勝過他人的觀點,即使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想法。假新聞的算法邏輯只要符合公眾想象、認知的基本邏輯,便可以催生令公眾信服的觀點和內容,公眾通過自我說服、自我辯解的方式增強自我認同,通過虛假新聞傳播的反復驗證,從而產生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我信念,特別容易通過錯誤信息傳達不切實際的想法,盲目傳播、轉發、評論,造成話題熱度上升,從而加劇假新聞的泛濫。此外,一旦形成固化認知,公眾便會通過各種途徑驗證、證明所持觀點,甚至枉顧事實根據和價值理念。
三、算法傳播傳播假新聞的治理
通過算法新聞的生成邏輯,以輿論領袖打破“回聲室”,不斷優化算法對抗帶有偏見的算法,同時增強公眾算法素養,增強辨別假新聞的能力,從而發揮正向引領作用,消解假新聞的危害。
培養“輿論領袖”。政府在法律和行政權威的基礎之上,采取柔性的方法來進行輿論發展方向的引導,規避最初的隱瞞式、滯后式策略。主動進行信息的公開和傳播輸出,由輿論領袖首先將信息進行權威性解答和詮釋并傳達給公眾,再由公眾通過自己的輿論圈傳達給更多的人,產生更大范圍的影響和普及。一方面將權威信息進行及時傳播使之在盡量短的時間內進行擴散,覆蓋面的擴大伴隨的是影響力的增強;另一方面則是從側面阻斷其他信息傳播渠道,代表權威的“輿論領袖”釋放輿論基本立場信號,在輿論傳播初期便設立一個局限和范圍,所有的輿論傳播者需要在規定范圍內進行操作,而違反輿論領袖立場的輿論和信息則失去發揮的空間和信任基礎,其影響力和可信度大打折扣。
優化算法以規制偏見算法。其一,建立規范化的算法機制和準則。以政府行政人員、輿論引導專家等為主,協助算法專家編制一套合理、合法的底層算法系統,通過實踐操作、訓練、檢驗等測試,形成一套穩定的算法偏見糾錯系統,在實效檢測中不斷優化算法,提升算法實用性和時效性,從而抵制假新聞的產生、傳播與泛濫。其二,厘清算法偏見數據的社會環境因素。了解算法系統中嵌入的社會因素,通過算法自身檢測清除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并設計干預措施和算法來破壞來自非可信來源的信息流,通過檢測不可信來源、違規算法程序帳戶,封鎖假新聞并防止其擴散,創建阻止此類信息流的可行性算法,從源頭阻塞大多數虛假信息。其三,建立假新聞檢測模型。通過過濾冗余術語或字符對數據集進行預處理,根據假新聞特征提取已應用于偽造的新聞數據集,對疑似假新聞的訊息進行集中審查與處理,最終形成假新聞檢測的模型,確定的假新聞送交傳媒專家郵箱或發送即時消息甄別,對抗假新聞泛濫。
增強公眾算法素養。一方面,減少算法傳播假新聞的渠道。政府在輿論引導平臺上進行詳細的調研和評估,用更加多元化和民眾易于接受的方式進行輿論引導和傳播,著力識別假新聞的來源并控制這些來源的信息,擔當起保護和檢測錯誤信息的“守門人”,著力打擊欺騙性策略模仿真實新聞媒體的網站所產生的新聞。另一方面,提升公眾判斷假新聞的能力。通過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紹算法運行機制和原理,使公眾了解算法傳播假新聞的潛在的危害和產生邏輯,同時進行打擊假新聞的教育或實施算法掃盲干預措施,甚至于建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相關教學體系,形成社會公眾的算法素養提升機制,從而基于算法素養角度提升公眾辨別事實的認知能力。
參考文獻:
[1] 史安斌,王沛楠.作為社會抗爭的假新聞——美國大選假新聞現象的闡釋路徑與生成機制》[J].新聞記者,2017年第6期.
[2] 汝緒華.算法政治:風險、發生邏輯與治理》[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作者簡介:王英明(1999- ),男,山東濰坊人,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經濟管理學院學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