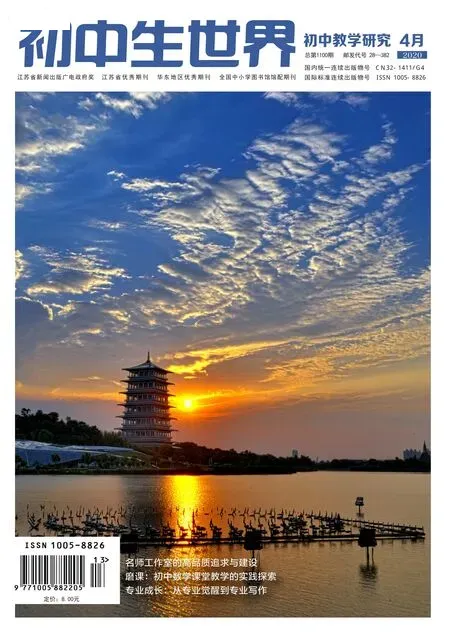文言文教學的四重視角
——以《小石潭記》教學為例
■韋存和
呂龍老師應邀在鎮江市天王中學執教的《小石潭記》取得了很好的現場效果,得到了幾個名師工作室教師們的一致好評。原因是多方面的:呂老師曾獲全國教學基本功競賽一等獎,他音色純正的普通話,不疾不徐的從容教態,啟發學生回答時的機智與耐心,都是重要因素。可依我看,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這節課所采取的基于文言、文章、文體、文化的文言文教學的四重視角。
一、文言視角:披文入情,在語言文字中體悟作者情感變化
呂老師沒有采取傳統的串講方式,而是借助朗讀,抓住關鍵詞語(“冽”“清”“斗折蛇行”“犬牙差互”等)和難點句子(“凄神寒骨,悄愴幽邃”等),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披文入情。課上,教師通過詞語教讀、學生齊讀、學生自由讀、學生讀文章中的四字短語、學生再次齊讀等方式,有序地進行朗讀訓練,拉近學生與文本的距離。教學過程中,教師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把握關鍵詞語和難點句子,讓學生輕松地走進文言文文本。在理清基本內容的同時,教師還引導學生大致把握了作者的情感變化。
仔細觀察本節課,我們會發現,教師始終貼著文言文文本在教學,所有的環節都與詞語的解釋、句子的翻譯有著密切的關聯。然而,教師并沒有作瑣屑的逐字逐句的解釋與翻譯,所以課堂既實在,又保持了很多的靈動,引人入勝。其實,文言文真的不必篇篇、處處串講。《小石潭記》是“永州八記”中文字較為曉暢的一篇,而統編教材又有著注釋詳盡的特點,《小石潭記》的注釋達27 個之多。教師只要幫助學生理解了重難點詞句的意思,別的詞句自當迎刃而解,何苦字字句句一路講來,講得無味,聽得無趣呢?
二、文章視角:起承轉合,在行文曲折中品悟作品結構之美
本節課注意到了篇章的結構之美。教師用演繹法完成了這個環節的教學。起承轉合是古人常用的文章結構技巧,但要用得自然貼切,不著痕跡,還是需要很深的寫作功力的。而且,現在的學生對于這樣的結構方式還不能算是耳熟能詳。因此,教師用演繹的方法先把一般性的結論(原理)提供給學生,然后讓學生從文章中求證。這無疑大大地消解了學生認知的難度,相當于提供了在學習上“更上一層樓”的階梯。第一節起筆由遠及近,由聲到形,曲折婉轉;第二節承筆細細描摹,虛實正側,手法多樣;第三節轉筆宕向遠處,寫溪水、源流,由樂轉憂;第四節合筆環視四周,回到眼前,攜悲涼歸去。學生也許不能盡解其中之味;但在教師的引導下,景物的變化,情感的起伏,在行文曲折的結構之美中盡顯風華。
三、文體視角:追蹤尋變,在作者行止中參悟游記寫景順序
在柳宗元之前,人們對山水的描寫尚在有意無意之間,即使酈道元的《水經注》具備了地理上的科學性和卓越的文學性,但仍然以客觀記述為主。柳宗元第一個塑造了鮮明、生動的系列自然山水形象,更為豐富地表現了人的情感,從而使得山水游記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門類。教學《小石潭記》,自然需要格外關注開山水游記創作先河的柳宗元作品的文體特征,尤其是體現游記特征的作者行蹤,這就勢必會牽出作者觀察景物視角的變化。
呂老師不僅在課堂第二個教學環節中精心設計了一個有關“在題目中加字”的問題,喚起學生對本文文體的有效注意,還在第三個教學環節中啟發學生探尋柳宗元行蹤,把握“永州八記”由地標參照著手,以作者行蹤為序的總體形式特點,這也是體現游記文體特征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他還引導學生逐節進行具體探究,這樣一來,第一小節的移步換景和后面幾小節的定點觀察便水落石出了。
不僅如此,呂老師還啟發學生具體地分析了本文定點觀察的三種方式:近觀(凝視)——遠眺——環視,讓游記散文豐富的觀察視角給人以具體深刻的印象。作品的開創價值自然也在課堂上得以凸顯。
四、文化視角:相機引述,在點染比較中感悟文章的哲學意味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哲學家,但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柳宗元的哲學思想體現于他的論說文,如《天說》《天對》《封建論》《非國語》等篇章之中,而且將其哲學的主導思想定義為“統合儒釋”,卻多少忽視了作為柳宗元代表作中熠熠閃光的“永州八記”,其實更多的是受莊子哲學的影響。這些作品賦予山水精神人格化,在自然山水中安頓作者悲哀苦悶的靈魂,追求精神的自由與開闊。呂老師注重對《小石潭記》哲學意味的挖掘,且沒有把柳宗元的哲學思想生硬地灌輸給學生。他抓住作品第二節對魚兒“樂”的描寫,引入本冊教材中莊子的話:“鰷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師生由此領悟了莊子追求無拘無束的絕對的精神自由,結合柳宗元被貶永州的寫作背景,探究出柳宗元期待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是“和莊子的哲學思想一脈相承”的結論。課堂有了哲學意味,就會多些厚重,給學生的未來人生以更深遠的啟示。呂老師的可貴之處在于做到了有機的融合、自然的生發,這也非常切合八年級學生語文學習的實際情況。
當然,情景交融是山水游記的本質特征,許多時候,在柳宗元筆下,所游之景和所寄之情都無法截然分開。從這個意義上說,本節課的課堂結構似乎可以進一步完善。我是贊成由體味景物入手去體悟作者感情的,《小石潭記》中景物的動靜、虛實、冷暖,甚至作者形諸筆下的景物自身,無一不傾注著作者的內在情感。如能把體會感情和分析景物特征放在同一環節里進行,教學上可能會顯得更自然,領悟上也會更深邃些。一孔之見,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