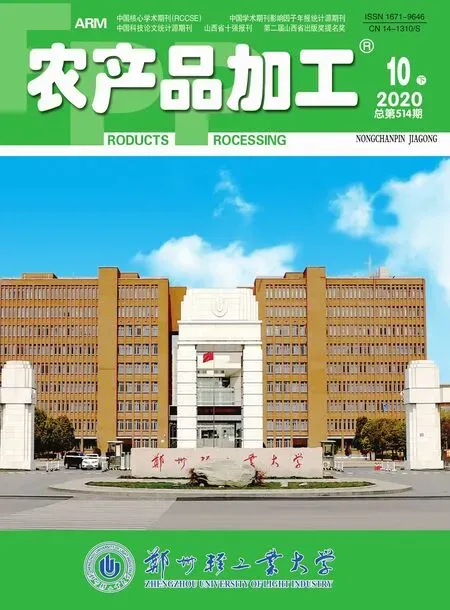食品安全指數研究進展
徐曉燕,孫中葉,屈凌波
(1.河南工業大學 經濟貿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鄭州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1)
0 引言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是一個遍及全球的公共衛生問題,同時也是個世界性難題。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已經嚴重影響到居民對政府、企業等生產監管部門的信任度,威脅社會穩定;同時,對我國的食品進出口貿易及經濟發展也產生嚴重影響。為解決好食品安全問題,各級政府部門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其效果并不理想。長久以來,食品抽檢合格率是評價食品安全狀況的主要指標,我國地域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居民食品消費習慣復雜多樣,導致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復雜,監管種類繁多,所以當前單一結果類指標的評價方法已不適合于食品安全保障的要求。食品安全指數通過構建一系列食品安全指標,對影響食品安全的相關因素進行賦值,并給出綜合評價值,以此來反映食品安全的情況。構建食品安全指數評價體系,以食品安全指數來衡量、評價食品安全的狀況,依據食品安全指數制定食品安全監管的政策,促進食品質量信息的有效披露,科學引導消費者的食品購買行為,增加消費者對食品企業和政府監管部門的信任度,對維護我國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1 食品安全指數的內涵與應用現狀
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的定義,食品安全包括食品數量安全、食品質量安全和食品可持續安全。國內農經界多數學者將食品安全界定為食品質量安全,在此框架下,學者對食品安全指數的研究也界定為對食品質量安全指數的研究。食品安全指數通過指數的形式來反映食品安全基本情況,根據一定的計算方法對反映食品安全基本情況的檢測數據進行統計計算,從而對食品安全基本情況進行綜合評價的信息[1]。
目前,關于食品安全指數的理論研究成果頗豐,但尚處于探索階段,系統的理論成果并不多。從2012年起,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 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專家評分法,每年在全球范圍內編制發布“Global Food Security Index”[2]。國內較多學者將其稱為《全球食品安全指數》,但其實并不完全準確,該指數僅通過3 個國際通用指標:食品價格承受能力、食品供應能力、質量安全保障能力來評價食品安全,這3 個指標是從食品供需角度來評價,無法反映食品質量安全與否。另外,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和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食品風險評估專家利用危害物實際攝入量與安全攝入量之間的數量關系,構建了食品安全指數(IFS),作為食品安全危害物暴露風險的評價方法。國內并沒有形成全國統一標準的食品安全指數體系,只有少部分省市制定與發布了地方食品安全指數,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地方食品安全指數主要分為2 種,一是以北京市為代表的食品安全信任指數,主要反映食品安全正面信息情況;二是以上海市為代表的食品安全風險指數,主要反映食品安全負面信息。
2 國外關于食品安全指數的理論研究
國外食品安全評價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影響因素分析和食品安全風險分析2 個方面。Jill E Hobbas[3]通過分析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3 個國家在食品安全立法和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方面采取的不同措施,評價政府行政管理對食品安全的影響,通過比較發現這3 個國家雖然在監控過程中的側重點不同,產生的監管效果也不同,但是提出制定公共政策仍然是政府確保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Banati D[4]通過闡述中歐和東歐地區的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丑聞導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問題,提出保障食品安全的立法和監管保障工作應貫穿整個食品產業鏈,并確保其在食品產業鏈各環節的統一性、執行性和協調性。Swarte C 等人[5]設置了食品安全目標(Food Safety Objective,FSO),作為防范食品安全風險的指標,用來控制微生物帶來的風險,并為政府部門制定食品產業鏈的健康目標提供依據。Unnevehr Laurian J 等人[6]探討了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HACCP)在食品安全風險監控中的作用,認為在食品安全條例的制定過程中適當的應用HACCP,比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干預措施更加經濟有效。Konig A[7]針對歐盟的食品風險防范流程提出了完善食品安全風險識別機制,擴大食品安全風險防范的范圍以及增加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流程等建議,以改善歐盟食品安全風險防范的透明度、開放性和責任性。國際食品微生物標準委員會(ICMSF) 利用流行病學數據,通過建立過程指標、物理指標、微生物指標和公共健康指標等,對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目標進行評估。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每年發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數報告》,其數據來源于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的官方數據,通過動態基準模型綜合評估全球113 個國家的食品安全現狀,并給出總排名和分類排名,雖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其包含的指標內容無法準確反映食品質量安全,同時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些關鍵控制點的評價上存在誤差。具體到國家,國外學者對食品安全指數的研究也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缺乏基于各國國情的量化研究。各國缺乏針對本國居民的食品消費觀念、食品安全保障技術、食品安全監管能力等方面的實際情況構建動態評價模型的研究,只能籠統地對各個國家食品安全所在的層級進行評價,無法使各國居民準確詳盡地了解本國的食品安全情況。
3 國內關于食品安全指數的理論研究
國內學者對食品安全指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食品安全狀況的評價,利用IFS 法評價食品安全危害物暴露風險,以及對食品安全指數體系構建的探討方面。
孫春偉等人[8]界定了食品安全指數的概念,指出食品安全指數的確定可以綜合食品安全信任指數反映出的積極信息與食品安全風險指數反映的負面信息綜合評價,具有代表性和時效性,能夠及時反映居民經常消費的主要食品的安全信息。吳廣楓等人[9]指出了我國現有食品安全狀況評價方法存在數據質量無保障、食品安全信息公開程度低等問題,食品安全監督抽檢中百分比抽樣方案存在局限性,提出從食品消費安全狀況、食品生產經營安全狀況、食品安全監管狀況3 個維度構建我國食品安全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劉文[10]構建了食品安全R 指數,并以食品合格率與合格度為指標,評估了7 類食品的質量安全情況。李太平[11]運用木桶原理和黃金分割法則,采用五級標度法構建了我國食品安全指數的測度方法,并運用構建的食品安全指數對2015 年度我國食品安全進行了測度。
國內學者利用IFS 指數法對我國某些食品安全危害物暴露風險進行評價。劉劍等人[12]利用IFS 對四川成都市的草莓的農藥殘留進行了安全分險評價。蘭珊珊等人[13]用IFS 對西南地區的食用菌的農藥殘留進行評價。金彬等人[14]利用IFS 對浙江寧波的蔬菜的農藥殘留進行了食品安全評價。張文等人[15]運用IFS對甘肅省春季蔬菜與水果的農藥殘留進行了安全風險評價。曾小峰等人[16]利用該指數對廣西北海市海產品的重金屬污染水平進行了安全風險評價。程加遷等人[17]利用該指數對廣西北海市海產品的重金屬污染水平進行安全風險評價。張文等人[18]則利用該指數對江蘇地區克氏原螯蝦鎘的膳食暴露量進行了安全風險評價。從這些文獻中可以看出,IFS 是一種微觀風險評價指數,只是針對某一種危害物對食品安全造成的影響進行評價,因此其不適用于國家宏觀食品安全狀況的測度。
國內也有許多學者運用主成分分析法[19-20]、灰色關聯分析法[21]、層次分析法[22-23]、網絡層次分析法[24-25]、熵值法[19]及德爾菲法[26]等方法來確定指標的權重,從而構建食品安全指標體系來對食品安全狀況進行綜合評價。但是,由于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觀性和指標權重分配的不確定性,使得評價結果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用主觀賦值法構建的食品安全指數沒有實際應用價值。
4 結語
總體來看,國內外對于食品安全指數的研究仍處在探索階段,存在的主要不足之處為如下幾點。首先,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種評價方法在食品安全評價領域的應用,沒有針對政府監管者的實際需求提出適合用于政府監管的安全評價工作的具體方案,而且缺乏對政府食品安全監管績效的評估,從而無法確定適合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推行的高效經濟的食品安全評價方法;其次,我國食品安全評估主要是基于相關的質量安全標準,根據食品檢驗結果是否符合標準來確定產品是否合格,即用所謂的“合格率”來判斷,這種判斷方法過于籠統,并且有很多的局限性,公布的信息容易給消費者造成一定的誤解;最后,相關研究中食品安全指數的原始數據采集缺乏準確性和時效性,特別是針對居民經常消費的生鮮食品的數據采集有一定的滯后性,容易使食品安全指數的評價產生誤差。
針對食品安全指數的研究,必須要確保基礎數據的有效性,指標體系構建的權威性、客觀性、簡便性、辨識性,構建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統,促使食品安全信息的有效披露,消除食品安全信息不對稱對食品市場的影響,為消費者的食品購買行為、政府監管工作和企業經營活動進行科學的引導。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可以利用大數據、物聯網、GIS 等先進的信息技術對食品安全生產流通進行監控,以便獲取更加準確的原始數據,也可以將人工神經網絡、決策樹、遺傳算法等人工智能方法運用到了食品安全評價中,建立動態的食品安全評價體系,這些方法經濟、快捷、更為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