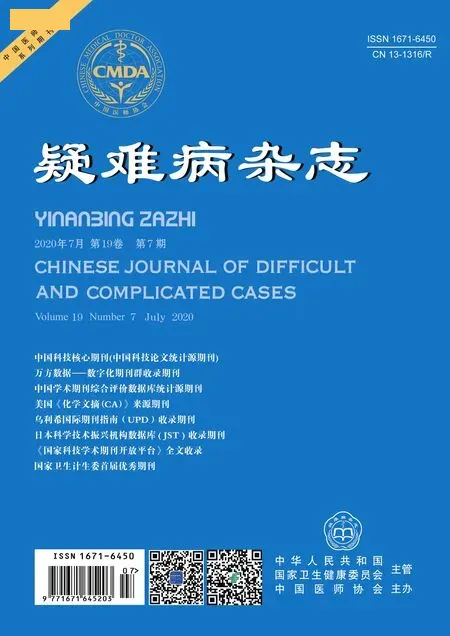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炎性因子風暴與房顫的關系
賈茹,尹德春綜述 曲秀芬審校
最近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在世界蔓延。大多數患者病情穩定,預后良好,但部分感染患者快速進展為重癥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或多器官功能衰竭(MOF)并最終死亡。炎性因子風暴是導致病情惡化的主要機制之一,大量炎性因子引起體內嚴重的炎性反應狀態,而炎性反應與心房顫動密切相關。
1 炎性因子風暴概述
炎性因子風暴(又稱細胞因子風暴)是一種以全身性炎性反應、高鐵蛋白血癥、血流動力學不穩定和MOF為特征的臨床癥狀。目前為止,有Toll樣受體(TLRs)、核苷酸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NLRs)、視黃酸誘導基因-I樣受體(RLRs)、C型凝集素受體(CLRs)等4種模式識別受體參與炎性因子風暴的發生[1]。當病原微生物進入人體時,激活TLRs,而后激活各種信號介質級聯反應,最終使核轉錄因子κB(NF-κB)誘導多種炎性細胞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1β(IL-1β)、干擾素調節因子3(IRF3)和激活子蛋白-1(AP-1)等的大量生成[2],引起機體損傷。多種疾病的進展機制中都有炎性因子風暴的參與,涉及多個系統。因此,不能把炎性因子風暴認定為是一種疾病,它是不同初始損傷的共同終點,其本質是機體免疫系統功能失調,炎性因子會對其自身的產生起正反饋調節,級聯產生大量的炎性因子最終導致機體損傷[3]。
2 新型冠狀病毒中的炎性因子風暴
近期對入院時新冠肺炎感染患者血液的實驗室檢查發現,大部分患者C-反應蛋白(CRP)、白細胞介素-6(IL-6)及血清鐵蛋白增高,淋巴細胞絕對值降低,該結果表明,SARS-CoV-2可能主要作用于淋巴細胞,尤其是T淋巴細胞,病毒顆粒通過呼吸道黏膜傳播并感染其他細胞,在體內誘發炎性因子風暴,產生一系列免疫反應,并引起外周白細胞和免疫細胞(如淋巴細胞)的變化[4]。流式細胞術分析發現,外周血CD4+和CD8+細胞的數量大大減少,而其狀態卻被過度激活,CD4+T細胞中具有高度促炎效應的CCR4+、CCR6+、Th17細胞增加,此外,發現CD8+T細胞有高濃度的細胞毒性顆粒[5]。T細胞的過度活化,促炎因子的大量釋放,這些都說明了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體內,出現了炎性因子風暴。并且,與未進入ICU的患者相比,ICU內的危重患者血漿中IL-2、IL-7、IL-10、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SCF)、單核細胞趨化因子(MCP-1)、TNF-α等細胞因子的水平更高[6],也證實了這一點。
3 新型冠狀病毒增加房顫易感性
Yao等[7]研究發現,心肌細胞中NLRP3炎性小體在房顫中的作用,通過免疫印跡法評估了陣發性房顫(pAF)和持續性房顫(cAF)患者心房全組織裂解液和心肌細胞中NLRP3炎性小體的活性,并建立了表達組成性激活NLRP3的心肌細胞特異性敲入(CM-KI)小鼠模型,結果顯示,pAF和cAF患者的心房肌細胞中NLRP3炎性小體的活性增加,且NLRP3的特異性抑制劑MCC950可以減弱CM-KI小鼠的自發性房性期前收縮和房顫的發生,這項實驗證實了炎性反應與房顫息息相關。最近的一項研究,利用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計算機斷層掃描(CT)檢測惡性腫瘤患者心房18F-氟脫氧葡萄糖(FDG)的攝取,與對照組相比,惡性腫瘤伴房顫的患者,心房FDG攝取率增高,且惡性腫瘤伴房顫組中4例尸檢心臟的病理證實,在FDG攝取區域有血管外巨噬細胞和淋巴細胞浸潤[8]。說明心肌局部炎性反應與房顫的發生關系密切,可能通過局部炎性介質的增多,影響心臟電活動,誘發房顫。
SARS-CoV-2與SARS-CoV的基因組具有較好的序列同源性[9],通過對121例SARS患者的研究發現,心動過速是SARS-CoV最常見的心血管并發癥,并且有1例患者出現陣發性房顫[10]。與SARS-CoV相比,人群對SARS-CoV-2普遍易感,患有潛在慢性心血管病者更容易感染SARS-CoV-2,也更容易出現并發癥和危急情況,甚至死亡[11]。在感染SARS-CoV-2患者的臨床特征描述中,感染者除了有呼吸系統癥狀外,16.7%的患者出現了心律失常[12],雖然沒有提供心律失常的明確分類,但SARS-CoV-2有可能通過以下機制,影響心房的電重構或結構重構,增加房顫易感性。
3.1 炎性因子風暴引起心房電重構 在臨床研究中曾發現,炎性介質與心房電學性質有關,可以引起心房電重構。有文獻報道,物理刺激后P波平均持續時間增加,CRP、IL-6、TNF水平瞬時升高,但心房容積無差異,提示炎性因子的急性改變與心房電傳導及AF易感性有關[13]。COVID-19患者體內T細胞過度活化,重癥患者短時間內發生炎性因子風暴,IL-2、IL-6、IL-7、IL-10、TNF-α等炎性因子大量釋放,其中多種炎性因子已被證明與房顫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如經IL-6預處理的大鼠心房組織,即使輕微的張力也可以導致房顫的發生[14]。與竇性心律組相比,房顫患者心房組織中TNF- α表達水平升高,T型鈣通道亞基mRNA表達水平降低, TNF-α可能憑借通道功能損傷和下調通道蛋白表達的方式,降低心房肌細胞T型Ca2+電流,參與房顫的發生[15]。
3.2 心肌損傷 SARS-CoV主要通過刺突蛋白(S蛋白)與細胞膜上表達的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蛋白結合侵犯人體[16],與SARS-CoV相比,SARS-CoV-2的S蛋白與人類ACE2有更強的結合親和力[11]。研究發現,ACE2在心肌細胞及周細胞等心臟細胞中均有表達,且ACE2在心臟的表達高于作為該病毒主要靶器官的肺,表明心臟可能存在感染易感性[17],是SARS-CoV-2導致心肌損傷的關鍵。在疫情初期的COVID-19患者臨床特征描述中發現,有12%的患者出現了急性心肌損傷也證實了這一點[4]。心房心肌病可由炎性反應引起,重癥COVID-19患者體內發生炎性因子風暴,強烈的炎性反應狀態很可能導致心房心肌病的發生發展[18]。研究發現,有基礎心臟疾病(如高血壓、冠心病、心肌病)的患者,在感染SARS-CoV-2后,更易發生心肌損傷,使TnT水平升高,患者可有更嚴重的呼吸功能障礙和更低的氧分壓[19],這些基礎心臟病本身已經對心臟結構產生影響,而COVID-19患者體內嚴重的炎性反應狀態甚至是炎性因子風暴和低氧血癥等,都會加重心房心肌病。近期,在對感染者進行的病理解剖中,發現了心肌間質中有少量單個核細胞的炎性浸潤[5],表明COVID-19患者存在心肌局部炎性反應,它可以通過多種機制,影響心房重構,誘發房顫。COVID-19患者發病時最常見的癥狀是發熱[4],發熱可以使患者心率加快。快速房性心動過速可導致鈣超載,介導氧化應激、細胞凋亡、膜功能障礙、能量消耗和低度炎性反應的發生[20],這些均是導致心房重構、誘導房顫發生的危險因素。而房顫可能是在劑量—反應關系中被觸發的,全身受累及感染越嚴重,房顫的發生率越高[21]。COVID-19患者免疫系統過度激活,血清中促炎因子水平升高,并級聯釋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引起全身性炎性反應,或炎性因子聚集于心房,引起心房心肌病,增加房顫易感性。
3.3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改變 ACE2是血管緊張素轉換酶(ACE)的同工酶,裂解血管緊張素Ⅱ(AngⅡ)產生Ang (1~7),發揮抗炎和抗重構的作用[22]。SARS-CoV-2通過病毒表面的S蛋白與ACE2結合而入侵人體,使ACE2的表達減少,進而導致AngⅡ局部升高。AngⅡ可以通過刺激促炎細胞因子(如IL-6、IL-8和TNF-α)的產生和直接激活免疫細胞來增加炎性反應,而TNF-α、IL-2、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PDGF)等細胞因子可以調節鈣穩態,引起肺靜脈異常觸發,縮短心房動作電位持續時間[13]。經AngⅡ處理的小鼠,依賴CD11b和CD18整合素,使心房中性粒細胞浸潤增加[23],心房的局部炎性反應,也會導致心房重構,最終引起房顫。AngⅡ也是引起纖維化的復雜信號系統之一,尤其是AngⅡ 1型受體,屬于主要的促纖維化細胞膜受體,也可以產生活性氧[24],當AngⅡ局部升高時,促進心房纖維化的發生發展,增加了活性氧的產生,而心房纖維化是導致房顫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活性氧也被認為在心房纖維化和電重構中起著潛在的重要作用,是導致房顫的重要介質[13,24]。
4 房顫的治療
4.1 抗炎藥物干預治療 類固醇類藥物是臨床上常用的抗炎藥物,臨床試驗表明,圍手術期內短期應用類固醇后,在房顫消融術后前3個月內,類固醇組的早期復發率明顯低于對照組[25]。他汀類藥物具有包括抗炎在內的多種作用,一項Meta分析結果顯示,使用他汀類藥物預處理,可以顯著降低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房顫的發生率[26]。秋水仙堿可以縮短炎性反應期,是預防心臟手術術后房顫發生的有效藥物[27]。除此之外,噻唑烷二酮、羅格列酮及醛固酮受體拮抗劑等藥物,通過其直接或間接的抗炎作用,可以調節炎性反應與氧化應激,減輕心房重構及纖維化,對房顫產生有利影響,減少房顫的發生[20]。
4.2 精準治療 當前,射頻消融手術是治療房顫的重要策略,然而這一過程會引起一定的組織損傷。在傳統手術與抗炎藥物預防及治療房顫的基礎上,也可以利用炎性細胞因子的特異性拮抗劑,嘗試開展對房顫的精準預防或治療。例如,在對全身性幼年特發性關節炎(JIA)疾病的研究中,發現了細胞因子IL-1β的失調,并成功將IL-1受體拮抗劑阿那白滯素應用于治療,并在隨后的的臨床對照試驗中,證實了其有效性[3]。通過精準抑制導致房顫的主要炎性因子來預防或治療房顫,是一種治療房顫的新思路。
5 總 結
大量的基礎及臨床研究表明,房顫與體內的炎性反應狀態密切相關。病原體入侵人體,激活機體的免疫系統,釋放促炎因子,當機體免疫系統失去負反饋調節時,導致炎性細胞因子大量釋放,最終引起炎性因子風暴。體內大量的炎性因子引起全身或心房局部炎性反應,使心房電重構或者結構重構,最終導致房顫。COVID-19患者體內炎性因子水平高,重癥患者體內發生炎性因子風暴,且病理解剖結果證實了患者心肌間質中有少量炎細胞的浸潤,SARS-CoV-2病毒與ACE2結合,使AngⅡ水平升高,這些均促進了心房電重構或結構重構,因此應該對COVID-19患者進行密切的隨訪,警惕遠期房顫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