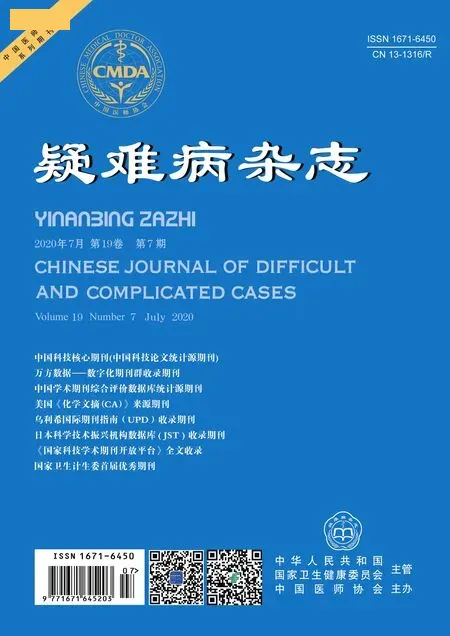肺動脈高壓基因遺傳突變研究進展
崔宇菲,張磊綜述 葉嵐審校
肺動脈高壓(PAH)是一種罕見的血管疾病,可表現為運動無力或暈厥、呼吸困難和右心室肥大。普通人群中肺動脈高壓患病率約1%。在我國排除左心疾病和肺部疾病后,肺動脈高壓以先天性心臟病相關肺動脈高壓、特發性肺動脈高壓(IPAH)和結締組織病相關肺動脈高壓(CTD-PAH)較常見;既往臨床上將PAH定義為靜息時肺動脈平均壓力≥25 mmHg,左心房壓正常。在2019年,該定義已修改為平均肺動脈壓力>20 mmHg,左心房壓力正常,肺血管阻力≥3 Wood單位[1]。PAH的病理生理機制復雜,環境和遺傳因素影響其發生發展;肺動脈高壓是遺傳基因突變、表觀遺傳因素及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多種血管活性分子、多種離子通道、多條信號通路在肺血管重構中發揮重要調節作用[2]。PAH包括IPAH、遺傳性肺動脈高壓(HPAH)和相關性肺動脈高壓(APAH)。本文將著重綜述基因(BMPR2、BMP9、ACVRL1、SMAD1、SMAD3、SMAD4、SMAD9、CAV1、KCNK3、ATP13A3、SOX17、AQP1、EIF2AK4、ABCC8、TBX4、GDF2等)突變在遺傳性肺動脈高壓中的作用機制研究進展,旨在探討PAH的遺傳病因及對今后基因篩查和基因相關治療策略的影響。
1 BMPR2突變
骨形成蛋白Ⅱ型受體(BMPR2)是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受體超家族成員骨成型蛋白(BMP)的受體蛋白,基因位于2q33.1-33.2(2號染色體長臂3區3帶),含13個外顯子。BMPR2突變占所有PAH患者的25%[3],成為肺動脈高壓最重要的基因突變之一。BMP信號轉導是通過質膜上配體結合BMPR2和激酶1樣激活素受體(ACVRL1,也稱為ALK1),激活下游蛋白實現的[4]。研究確定BMPR2突變占有PAH家族病史患者的53%~86%。PAH的BMPR2特異性變異是導致氨基酸置換的錯義突變,錯義突變廣泛分布在BMPR2外顯子上,但大多數位于關鍵的功能域內,特別是外顯子2~3編碼的配體結合域和功能上由外顯子6~9和11編碼的高度保守催化激酶區域[5]。BMPR2單倍計量不足是遺傳性PAH的主要分子機制。在BMPR2下游,他克莫司(FK506)通過結合BMP信號抑制劑FK結合蛋白,逆轉了PAH肺動脈內皮細胞功能失調的BMPR2信號轉導[6];有臨床試驗證實,低劑量FK506對PAH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較好[7]。
2 BMP9突變
對一項獨立的病例對照研究進行外顯子組基因負荷分析,總納入331例IPAH患者和10 508例對照者。研究人員進行功能評估以分析基因突變對蛋白質生物合成和功能的影響。編碼人骨形態蛋白9(BMP9)基因被確定為一個新的遺傳基因位點。BMP9中罕見編碼突變發生在6.7%的病例中,功能研究表明,BMP9突變導致肺動脈內皮細胞中BMP9分泌減少和抗凋亡能力受損[8]。我國也有研究顯示,BMP9的罕見有害變異與IPAH的發病呈強相關性,BMP9突變攜帶者體內活性BMP9減少,BMP9突變可以影響BMP9的合成、分泌、轉錄后加工及對ACVRL1通道的活化能力。BMP9可能是IPAH新的致病基因[9]。
3 ACVRL1突變
遺傳性出血性毛細血管擴張(HHT)是一種遺傳性血管疾病,激酶1樣激活素受體(ACVRL1)是TGF-β1型受體的一種。HHT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對伴有PAH的HHT患者基因進行研究, ACVRL1基因和內皮素(ENG)基因變異可能與PAH的發生存在關聯。ENG基因突變可導致HHT1型,ACVRL1基因突變可導致HHT2型。對HHT合并IPAH家系進行研究發現,ACVRL1突變可導致HHT患者合并IPAH。目前已經發現54種可導致2型HHT的ACVRL1突變,其中13種突變(占24%)可導致PAH的發生[10]。HHT的ACVRL1突變可以發生在基因全區域內,但是致PAH發病的基因突變基本局限于激酶活性區域。絕大多數ACVRL1突變是錯義突變,其中大約89%包含在重要的催化域內,提示致病性高[5]。
4 SMAD家族基因突變
SMAD家族是TGF-β受體激酶的重要效應分子,有實驗證實SMAD9基因突變明顯影響了SMAD轉錄活性;相比之下,SMAD1和SMAD4基因缺陷引起的轉錄激活抑制作用較輕[11]。最近研究顯示,SMAD3缺失在PAH中表現出一種新的病理機制,可促進血管細胞增殖,并通過心肌蛋白相關轉錄因子(myocardin-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MRTF)解除抑制人類肺血管平滑肌細胞(huPASMCs)的肥大[12]。
5 CAV1突變
小窩蛋白(caveolin 1,CAV1)首次被發現是通過對三代家族中4例PAH患者的外顯子組測序,因此認為CAV1的變異與PAH發病有關。目前發現的突變都隱藏在CAV1的末端外顯子中。已有研究表明,由于突變蛋白在內質網中,導致腔內合成作用明顯受損[13]。CAV1基因在肺動脈高壓中的作用機制逐漸被發現,有試驗提示內皮細胞中富含CAV-1的細胞外泡脫落進入循環中引起CAV1減少,導致TGF-β信號異常,引起血管重構及肺動脈高壓。此外,CAV1突變(c.474delA)導致SMAD1、SMAD5和SMAD8過度磷酸化,因此導致CAV1的抗增殖功能降低[14]。有試驗證實了骨髓間充質干細胞(rBMSCs)突變的CAV-1(Cav1F92A)基因對PAH平滑肌細胞表型轉換的影響。Cav1F92A增加NO濃度,提高細胞黏附、細胞生存能力,增加了抗炎細胞因子白介素-4(IL-4)、IL-10,但降低炎性細胞因子IL-1α、干擾素-γ(IFN-γ)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表達。Cav1F92A基因修飾的rBMSCs(Cav1F92Agene modified rBMSCs,rBMSCs/Cav1F92A)激活NO/cGMP通路,恢復細胞形態,抑制細胞遷移。試驗認為rBMSCs/Cav1F92A可抑制細胞的遷移,促進細胞的形態恢復。rBMSCs/Cav1F92A可用于肺動脈高壓的治療[15]。rBMSC/Cav1F92A細胞可以激活eNOS/NO/sGC/cGMP/PKG-1 信號通路,上調Mst1表達,改善肺組織內的氧化應激狀態并抑制自噬激活,從而緩解PAH大鼠肺部血管重構[16]。
6 KCNK3突變
PH敏感性鉀離子通道蛋白基因(KCNK3基因)突變與PAH相關。相關研究顯示,KCNK3突變導致鉀離子通道蛋白功能喪失,引起細胞膜去極化導致肺血管收縮,通過抑制凋亡導致肺血管重構和肺血管增殖,與肺動脈高壓發病相關。Ma等[17]在2013年發現6種KCNK3突變,并證實了均為有害突變且與PAH發病相關。試驗表明突變導致通道功能喪失,可能導致靜息膜電位去極化。磷脂酶抑制劑處理后逆轉了細胞內外鉀通道的電流減少。研究表明,細胞中cAMP濃度升高可以提高KCNK3的活性,從而達到治療肺動脈高壓的作用。在臨床研究中,曲前列環素可以提高細胞cAMP濃度從而激活KCNK3活性。內皮素1抑制KCNK3的活性,使用Rho激酶(Rho associated kinase,ROCK)抑制劑可以減弱這一抑制作用。
7 ATP13A3突變
與陽離子運輸通道相關的ATP酶13A3(ATP13A3)是參與離子通道運輸的ATPases亞家族P5B的成員,在血管細胞中高度表達,并且參與PAH的發生[18]。在PAH中鑒定出的多個ATP13A3突變都聚集在催化磷酸化結構域內,這表明可能對蛋白質功能產生重要影響。在一項干擾素β(IFN-β)治療PAH的研究中顯示,ATP13A3的變異可能引起肺動脈高壓易感性[19]。
8 SOX17突變
SOX17在血管生成過程(包括動靜脈分化和肺微脈管系統的發育)中是至關重要的,PAH存在SOX17靶基因中罕見有害變異的過度表達,表明該途徑在PAH病因學中的關鍵作用[20]。SOX17依賴于β聯蛋白的結合來激活靶基因的轉錄。一項全外顯子測序研究表明,SOX17突變是PAH相關性先天性心臟病的主要危險因素[21]。在0.7%的IPAH患者和3.2%的PAH相關性先天性心臟病患者中檢測到可能的致病變異。一項對日本HPAH或IPAH患者進行的類似研究確定了另外3個SOX17變異體[22]。
9 AQP1突變
肺動脈平滑肌細胞(PASMCs)的遷移和增殖是肺動脈重塑進而造成肺動脈高壓的主要病理基礎。水通道蛋白1(AQP1)具有促進上皮細胞、內皮細胞遷移的作用。有試驗表明,缺氧可促進AQP1在肺動脈內的表達[23],AQP1可通過β聯蛋白對PASMCs的增殖和遷移進行調節。AQP1水平的升高通過上調β聯蛋白,導致MYC原癌基因蛋白和cyclinD1的表達而促進PASMC的增殖和遷移[24]。全基因組基因負荷測試通過比較PAH患者和對照個體之間的變異頻率來鑒定新的基因變異,檢測出ATP13A3、AQP1和SOX17中罕見有害變異的統計學顯著富集, AQP1和SOX17突變攜帶者在診斷時年齡較小,推測PAH發病較早,為定向治療發展提供了新的靶點[25]。
10 常染色體隱性PAH的突變
目前肺動脈高壓臨床分類中,肺靜脈閉塞性疾病(PVOD)和肺毛細血管瘤病(PCH)屬于PAH亞組,PVOD和PCH均為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在對POVD進行的外顯子序列測定中,致病基因EIF2AK4在所有分析的家系(n=5)和25%散發性疾病(n=20)中均被檢出[26]。同時,Best等[27]在遺傳性和散發性PCH中獨立檢測到雙等位基因EIF2AK4突變。EIF2AK4的發現有助于PAH、PVOD和PCH的鑒別診斷。一項研究進一步證實了EIF2AK4突變在臨床PAH患者中的致病作用,該研究發現了9例具有雙等位基因的EIF2AK4變異。而且,攜帶有EIF2AK4突變的PAH患者年齡較小且其生存率降低。我國也報道了2例EIF2AK4基因檢測陽性并且診斷為肺靜脈閉塞病的案例[28]。
11 ABCC8/TBX4/GDF2突變
對BMPR2或ACVRL1基因突變陰性的PAH患者中發現了一個新的ABCC8基因變異[29]。在成纖維細胞樣細胞系中鑒定出ABCC8變體的表達降低了ATP敏感性鉀通道的功能,進一步表明ABCC可能是PAH的有害突變。用選擇性ABCC8激活劑二氮嗪對這些細胞的處理可使通道功能恢復到正常水平。在155例兒童期PAH和257例成人期PAH患者中進行了全外顯子組測序分析表明,與成年發作的IPAH隊列相比,兒童期發作的IPAH樣本組中發現TBX4(編碼T-box轉錄因子)的可能致病等位基因[30]。血漿生長分化因子2(GDF2)編碼BMP9,它是BMPR2的主要配體ACVRL1受體復合物和內皮細胞遷移及生長的有效抑制劑。研究表明,GDF2突變會導致BMP9功能喪失, 這些突變導致BMP9和BMP10水平降低。 這些發現支持增強PAH中BMP9或BMP10信號傳導的治療策略[31]。
綜上所述,自從引入大規模并行測序技術以來,PAH的遺傳學已得到迅速發展,該技術支持同時評估多個基因的基因組變異。BMP信號的失調仍然是PAH發展的主要危險因素,而BMPR2單倍體劑量功能不足作為疾病的主要分子機制,正在發展為靶向治療方案。持續的基因發現及對新發現基因的突變篩選在未來將有可能實現分子檢測PAH。目前研究強調了在將基礎遺傳學研究轉化為潛在治療模式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雖然目前直接糾正潛在突變仍然具有挑戰性,但基因編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肺血管內的靶向突變糾正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