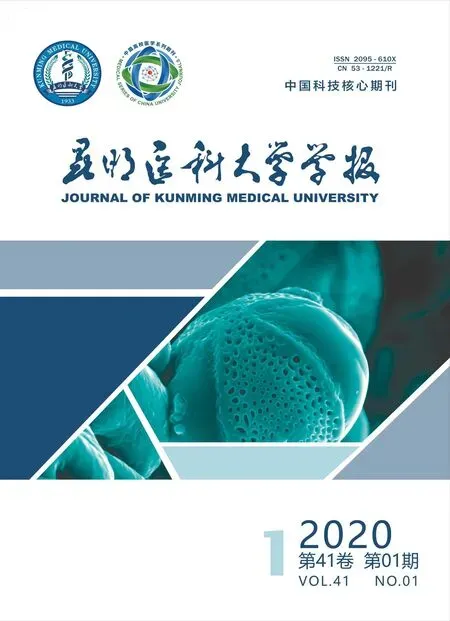可卡因誘導神經細胞自噬的研究進展
沈寶玉,楊根夢,李媛媛,劉 柳,黃 儉,曾曉鋒,李利華
(昆明醫科大學法醫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可卡因又稱古柯堿,是古柯樹的天然植物產物,由奧地利化學家紐曼于1859 年提純并命名。可卡因作為古老的濫用毒品之一,具有強效的神經興奮作用,長期濫用常引起神經毒性和藥物依賴。此外,可卡因的長期濫用常伴隨HIV 感染[1-2],給社會公共衛生帶來了嚴重的負擔。自噬是一種高度保守的生理機制,可作為細胞短期存活的手段,主要對細胞分解代謝途徑進行調控,在維持細胞能量平衡和生長調節上起著重要作用。自噬作為細胞死亡或存活的決定因素和在不良生理條件下的關鍵防御機制,在最近幾年引起了廣泛關注[3]。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神經細胞自噬,其誘導自噬的過程由多種機制調控,并在可卡因神經毒性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綜述現有證據,探討可卡因誘導神經細胞自噬的分子機制和可卡因聯合HIV 引發的神經毒性。
1 自噬過程
在正常生理條件下,自噬處于較低水平,當細胞處于營養缺乏、缺氧、代謝應激[4-5]等狀態時,自噬活性顯著上調。自噬過程由一組進化上保守存在的自噬相關(autophagy-related,Atg)基因所介導,其特征為自噬體(Autophagosome)的形成,自噬體由雙層膜結構包裹待降解的蛋白質、受損的細胞器或病原微生物等自噬底物而組成,并與溶酶體融合以降解和再循環自噬底物,進而作為細胞存活的能源[6]。根據自噬底物向溶酶體轉移的不同機制,可將自噬過程分為3 種不同類型:巨自噬、微自噬和伴侶介導的自噬[7-8],通常所稱的自噬指巨自噬,下文將巨自噬簡稱為自噬。
自噬體膜的磷脂主要來源于內質網(endoplasmic reticulum,ER)、胞質內顆粒(Endosomes)或線粒體(Mitochondria),并招募含3類磷脂酰肌醇3激酶(Class Ⅲ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的多蛋白復合體[9-11],其中包含:beclin 1(BECN1)、PIK3C3(PI3K 催化亞基3 型,也稱VPS34)、PI3KR4(PI3K 調控亞基4,也稱VPS15)、膜曲率感受器Atg14(也稱BARKOR)和核受體結合因子2(nuclear receptor binding factor 2,NRBF2)。此外,自噬體的形成是由包含Atg13、Atg101 和unc-51樣自噬激活激酶 1(unc-51-like autophagy activating kinase 1,ULK1)的多蛋白復合體所啟動的,該復合體在含Atg9 的自噬體膜上裝配和活化,并激活Atg9 的磷酸化[12]。隨后,VPS34 產生磷脂酰肌醇3-磷酸(phosphatidylinositol 3-phosphate,PI3P),PI3P 與Atg 蛋白家族結合,并與WD 重復磷酸肌醇相互作用蛋白(WD-repeat protein interacting with phosphoinositides,WIPI)家族進一步促進自噬體膜的擴張直至閉合[13]。自噬體在包裹自噬底物后與溶酶體融合形成自噬溶酶體(Autolysosomes),而調控該融合過程的分子機制涉及數十種蛋白質,其中大多數涉及內吞相關通路[14]。自噬溶酶體形成后,Atg 偶聯系統(Atg conjugation systems)誘導自噬體膜在自噬溶酶體的內部降解[15],而ATP 依賴性質子泵活性的改變導致了自噬溶酶體內部酸化,最終引起自噬底物的降解[16]。此外,自噬體的形成、自噬體與溶酶體融合及自噬底物降解的過程與兩個泛素樣結合系統的活性有關[17-18]。酵母Atg8 在哺乳動物中的同源物被稱為微管相關蛋白1 輕鏈3(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3,LC3),而Atg3、Atg7 及Atg12-Atg5-Atg16L1 復合物促進了LC3B(LC3β)與磷脂酰乙醇胺(phosphatidyl ethanolamine,PE)結合[19],LC3 與PE 結合并在自噬體膜發生脂化。脂化的LC3 稱為LC3-Ⅱ,在自噬體識別和攝取自噬底物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調控作用[20]。
綜上所述,自噬過程包括自噬體的形成、自噬體與溶酶體融合及自噬底物降解等環節,各環節緊密聯系并受多種分子機制調控。此外,Atg 蛋白、BECN1、LC3、LC3-Ⅱ等蛋白常作為自噬的標志物,可通過檢測上述蛋白表達水平來判斷自噬活性。
2 可卡因誘導神經細胞自噬
體外實驗表明,可卡因增加星形膠質細胞中自噬體的形成和自噬標志物蛋白如BECN1、Atg5 和LC3-Ⅱ的表達[21],并隨可卡因劑量和接觸時間的增加而上調[22]。此外,可卡因誘導了小膠質細胞自噬體的形成和自噬標記物如BECN1、Atg5、LC3-Ⅱ的表達,并與可卡因劑量和接觸時間呈正相關[23]。Guha 等[24]的研究發現,用可卡因處理的皮質神經元,自噬體數量和LC3-Ⅱ的表達顯著增加。Lu 等[25]用可卡因處理體外小鼠伏隔核原代細胞,發現自噬體的形成和LC3-Ⅱ的表達增加。此外,可卡因也誘導了人腦血管周細胞(human brain vascular pericytes,HBVPs)中自噬標記物BECN1 和LC3B-Ⅱ的表達上調[26]。
體內實驗表明,可卡因可上調小鼠伏隔核中LC3-Ⅱ的表達水平,并誘導自噬體的形成[25]。此外,可卡因增加了小鼠紋狀體中自噬標志物BECN1 和LC3B-Ⅱ的表達[21-23]。Guha 等[24]的研究發現,在孕鼠攝入可卡因后生產的小鼠中,其背側紋狀體、皮質、外側韁核和伏隔核中,LC3-Ⅱ的表達水平顯著上調。Sil 等[26]的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小鼠腦血管周細胞中LC3 的表達。綜上研究結果表明,可卡因可誘導多種神經細胞自噬。
3 可卡因誘導神經細胞自噬的分子機制
體內和體外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神經細胞自噬,而自噬受多種分子機制調控。以往的研究表明,可卡因可通過內質網(ER)應激、一氧化氮/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Siah1(NO/GAPDH/Siah1)、多巴胺D1 受體/鈣-鈣調素依賴性蛋白激酶2 型/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FoxO3a(DRD1-CaMKII-AMPK-FoxO3a)、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和sigma 1 受體(σ-1R)等信號通路誘導神經細胞自噬。
3.1 ER 應激對可卡因誘導神經細胞自噬的調控作用
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星形膠質細胞自噬,自噬抑制劑3-MA 或Wortmannin 可抑制可卡因誘導的自噬。此外,可卡因可上調ER 應激通路標志蛋 白(EIF2AK3、P-EIF2AK3、EIF2S1、P-EIF2S1、ATF6、ERN1、HSPA5 和DDIT3)的表達,而自噬抑制劑不能抑制ER 應激通路標志蛋白的表達上調。另一方面,ER 應激通路抑制劑Salubrinal 或4-苯丁酸鈉可抑制可卡因對ER 應激通路和自噬的誘導作用,此外,用siRNA 沉默EIF2AK3 后,顯示了同樣的結果。綜上表明,ER應激通路是可卡因誘導星形膠質細胞自噬的上游部分[21]。Sil 等[26]的研究表明,ER 應激通路作為可卡因誘導人腦血管周細胞(human brain primary pericytes,HBVP)自噬的上游部分而發揮作用。此外,σ-1R 抑制劑BD 1047 可抑制可卡因誘導的ER 應激通路標志物和自噬標志物表達,這表明σ-1R 在ER 應激通路的上游介導了周細胞自噬。Guo 等[23]的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小膠質細胞中ER 應激通路蛋白磷酸化,而ER 應激通路抑制劑Salubrinal、PPP1R3A 及對應的siRNA 均可抑制該誘導作用,并降低自噬標志物LC3-II 的表達。綜上,ER 應激通路作為可卡因誘導多種細胞自噬的上游而發揮重要的調控作用。
3.2 NO/GAPDH/Siah1 對可卡因誘導自噬的調控作用
Guha 等[24]的研究表明,可卡因通過NO/GAPDH 級聯誘導細胞自噬。可卡因在大腦皮層神經元中引起GAPDH 亞硝化及其核轉運。NO/GAPDH/Siah1 信號軸被抑制劑CGP2466B 所抑制后,GAPDH 亞硝化受阻,可卡因誘導的LC3-II表達受抑制;相反地,GAPDH 過表達后,大腦皮層神經元LC3-II 表達水平升高。而在神經型一氧化氮合酶(nNOS)敲出的小鼠皮質神經元中,可卡因不能增加其LC3-II 水平。綜上,可卡因可通過NO/GAPDH/Siah1 信號通路誘導自噬。
3.3 DRD1/CaMKⅡ/AMPK/FoxO3a 對可卡因誘導自噬的調控作用
研究表明,可卡因可在體內體外誘導AMPK的磷酸化,而在AMPK 敲除小鼠的伏隔核中,LC3-Ⅱ的表達被顯著抑制,這表明AMPK 可在小鼠伏隔核中介導可卡因誘導的自噬[25]。此外,AMPK 被報道可直接調控FoxO3a,FoxO3a 與Atg的啟動子區結合,調節自噬活性;而AMPK 在Thr172 位點磷酸化和鈣通量相關,CaMKⅡ可能是AMPK 的上游激酶[27]。本研究發現可卡因在體內體外誘導伏隔核神經元中FoxO3a 表達和CaMKⅡ磷酸化,而CaMKⅡ抑制劑KN-93 可阻斷可卡因誘導的CaMKⅡ磷酸化、AMPK 磷酸化和LC3-Ⅱ表達。此外,DRD1 抑制劑SCH23390 可阻斷可卡因誘導的CaMKⅡ磷酸化、AMPK 磷酸化和LC3-Ⅱ表達。綜上表明,可卡因可通過DRD1/CaMKⅡ/AMPK/FoxO3a 信號通路誘導自噬。
3.4 其他信號通路對可卡因誘導自噬的調控作用
研究表明,可卡因可降低小膠質細胞中mTOR通路標志蛋白AKT 和p-RPS6 的表達,這表明mTOR 通路參與了可卡因誘導的小膠質細胞自噬[23]。Walker 等[22]的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星形膠質細胞自噬,并下調mTOR 磷酸化,而mTOR 抑制劑可進一步誘導LC3-Ⅱ的表達,這表明mTOR通路在可卡因誘導自噬中起著負調控的作用。此外,可卡因可誘導σ-1R 的表達,而σ-1R 抑制劑和對應siRNA 均可抑制可卡因誘導的自噬。研究表明,σ-1R 在ER 應激通路的上游介導了可卡因誘導的自噬[23,26]。故σ-1R 相關通路在可卡因誘導自噬中起著一定的調控作用。此外,Bcl-2 作為抗凋亡蛋白,它的磷酸化可使Bcl-2/BECN1 復合物解離,并釋放BECN1 參與自噬過程[28],而可卡因可誘導Bcl-2 磷酸化從而引發自噬[22]。最后,除了BECN1 和Bcl-2,Atg5 和Atg7 也被報道調節自噬。Walker 等[22]的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BECN1、Atg5 和Atg7 的表達,而BECN1、Atg5 和Atg7 對應siRNA 可有效地抑制可卡因誘導的自噬,這表明BECN1、Atg5 和Atg7 對可卡因誘導的自噬起著一定的調控作用。
4 自噬在可卡因神經毒性中的作用
根據以往的研究,可卡因可通過多種信號通路誘導神經細胞自噬,而自噬在可卡因神經毒性中的作用是有爭議的。自噬通常被認為是細胞存活的機制,而廣泛的自噬可導致程序性細胞死亡,稱為自噬性細胞死亡。研究表明,可卡因可誘導自噬性細胞死亡[22,24],而自噬抑制劑可部分逆轉自噬性細胞死亡[22]。此外,自噬介質Atg5 或BECN1 的耗竭可顯著降低可卡因的神經毒性[24]。另一方面,自噬在可卡因神經毒性中起著一定的保護作用。當可卡因和自噬抑制劑聯合作用于小膠質細胞時,其存活率遠低于單一藥物作用的小膠質細胞[23],而可卡因誘導的自噬又引起促炎性細胞因子如TNF-α、IL-1β、IL-6 等的表達[21,23],從而加重可卡因神經毒性。故自噬在可卡因神經毒性中的作用可能是一個雙面且動態平衡的過程,損傷和保護并存。
5 可卡因聯合HIV 引發神經毒性
HIV 被分別命名為HIV-1 和HIV-2,HIV 感染主要指HIV-1 感染。CNS 是HIV-1 的一個重要靶點,HIV-1 在感染后的最初幾天內進入CNS,并通過HIV 基因編碼蛋白如Tat 蛋白和gp120 蛋白引發神經毒性。大量的研究表明,可卡因聯合HIV通過破壞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完整性、影響神經元代謝、干擾多巴胺系統和改變神經突觸可塑性等機制引發神經毒性。
5.1 可卡因聯合HIV 破壞BBB 完整性
Gandhi 等[29]使用人腦微血管內皮細胞(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HBMECs)和星形膠質細胞構建BBB 細胞模型,并測定跨內皮電阻(transendo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TEER)、FITC 標記的葡聚糖轉移率、單核細胞遷移率和緊密連接蛋白ZO-1 和JAM-2 的轉錄和表達變化,綜合評價了可卡因與HIV 聯合對BBB 完整性的破壞作用。研究表明,可卡因聯合HIV-1 Tat 蛋白可顯著下調BBB 模型跨內皮電阻和緊密連接蛋白ZO-1 的轉錄和表達,并上調FITC 標記的葡聚糖轉移率、單核細胞遷移率和緊密連接蛋白JAM-2的轉錄,從而破壞血腦屏障完整性,最終加速HIV-1 相關神經認知障礙(HIV-1-associate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HAND)的 進 程,其 中HIV-1Tat 蛋白C 支起著關鍵作用[29]。
5.2 可卡因聯合HIV 影響神經元代謝
正常的腦功能需要星形膠質細胞與神經元串聯的代謝物交換,交換過程受到嚴密調控,一旦受阻或損害將會引發中樞神經系統損害。Cotto 等[30]的研究表明,可卡因和HIV-1 Tat 蛋白通過干擾肝Ⅹ受體(liver X receptors,LXRs)信號,下調了載脂蛋白E(apolipoprotein E,ApoE)的表達,并激活甾醇調節結合蛋白(sterol regulatory binding protein,SREBP)通路,導致星形膠質細胞膽固醇失調,從而影響星形膠質細胞向神經元提供所需的膽固醇支持,進而影響神經突觸完整性和神經傳遞,最終引發神經認知障礙。
5.3 可卡因聯合HIV 干擾多巴胺系統
研究表明,可卡因和HIV-1 Tat 蛋白可顯著上調多巴胺水平,阻礙多巴胺降解,并改變HIV-1Tat 與多巴胺神經末梢的相互作用,從而引發神經病理癥狀[31]。此外,可卡因和HIV-1 聯合作用可干擾多巴胺的再攝取和清除,并改變樹突棘形態,從而導致多巴胺系統功能障礙[32]。
6 小結
以往的研究表明,可卡因能夠誘導神經細胞自噬,而可卡因誘導的自噬過程由多種機制所調控。同時,可卡因濫用具有強烈的神經毒性,而自噬在其中起著雙重作用,目前調控機制不清楚。特別在可卡因濫用合并HIV 中樞感染時,其協同神經毒性機制尚不清楚。因此,研究可卡因誘導的神經細胞自噬機制和可卡因聯合HIV 引發的神經毒性機制,有助于解決毒品濫用和HIV 中樞感染的世界公共衛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