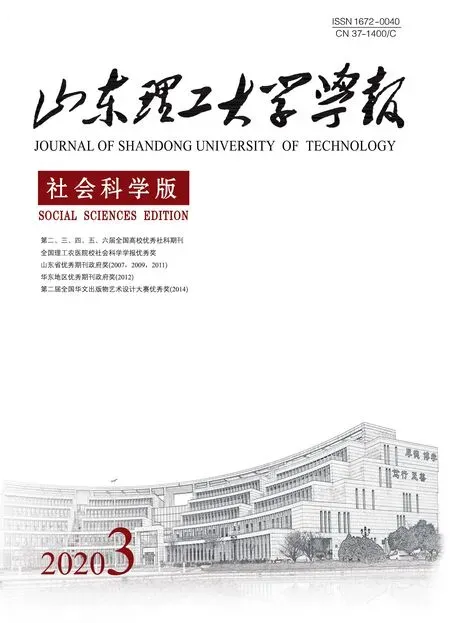《詩大序》論解
祝 秀 權
一
《詩序》是《詩經》之剛要,《詩大序》既準確地闡釋了詩的產生及其在周代創作與使用的真實情況,也準確闡釋了中國早期“詩”的性質。《毛詩序》是學《詩》的門徑,解《詩》的引路明燈。《序》中隱含著大義,隱含著經義,隱含著詩人的創作本義。305首詩,《詩序》幾乎百分之百地正確闡釋了詩義,且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詩”原本就產生于上層社會,產生于統治階級、貴族集團,產生于政治性質的事件,如祭祀、教育等等。其時詩的創作本身也主要是一種政治性質的行為,而不只是文學性質的行為。
《詩大序》末段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箋》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詩大序》末段鄭玄闡釋有誤。“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是詩人樂之、憂之、哀之、思之,非指后妃樂之、憂之、哀之、思之。序者明言“《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意以“關雎”代指詩人,其義甚明,非指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意為“使之(君子)不淫其色”,“其”指“女”。“無傷善之心”,意為“使之(女)無傷善之心”。如此解,方與“憂在進賢”義相合,亦與“后妃之德”義相合。關于“后妃之德”,筆者另文有論。
末段作結,序者之意分兩層說:“樂”正照應“哀”,“憂”正照應“思”,“不”正照應“無”。意思雖分兩層說,而兩層意思實則相同或相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即“哀窈窕”之意;“憂在進賢”,即“思賢才”之意;“不淫其色”,即“無傷善之心”之意。“哀”既然與“樂”相照應,則“哀”必非“衷”之意。
《論語》孔子所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是對《詩大序》末段之意的概括: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由此可知,《序》語甚古,非秦漢之后人所作。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與“淫”、“哀”與“傷”具有對應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程度的不同,故“哀”解為本字本義為佳,即“哀”應作如字解。
二
《詩大序》首尾二段皆言《關雎》,中間主體部分概論《詩》。
先曰“風”。因為“風”為《詩》之首,同時也是為了上接“風之始也”,使整個論述渾然一體,上下銜接嚴密無間。曰“風”之后,接曰“詩”。這是因為:第一,沒有“詩”,哪有“風”?故“風”之后,對“風”之所由來之情況加以上述而接曰“詩”;第二,“風”是“風教”的意思,為什么是“風教”的意思呢?因為“詩”是“言志”的,不是普通的抒懷。
《詩大序》認為,“詩”是“志之所之”;并認為“在心為志”,可知《詩大序》所言之“志”是“情志”之“志”。沒有“情”,哪有“詩”?故下文對“詩”之所由來之情況加以上述而接曰“情”。“情”是“詩”的必要條件。然而“情”本身并不是“詩”,也并不是有了“情”就有了“詩”。故于“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后,接曰由“情”而導致的嗟嘆、詠歌、舞蹈。然而“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以及由“情”而導致的嗟嘆、詠歌、舞蹈也不是“詩”,故《詩大序》此數語未出現“詩”字。這是耐人尋味的。為什么呢?因為由“情”而導致的嗟嘆,是“言”,不是“詩”;由“情”而導致的詠歌,是“歌”,不是“詩”;由“情”而導致的舞,是“舞”,不是“詩”。
“言”和“舞”固然不是“詩”,“歌”為何也不是“詩”?因為“歌”與“詩”是兩個雖然極有聯系,卻又有很大不同的概念。“言”可以“歌”,即使句式不整齊、不押韻的“言”也可以“歌”,但這顯然不是“詩”的概念。“歌”屬于俗文化,“詩”屬于雅文化;“歌”從一開始就不分身份、地位,人人皆可歌,“詩”在一開始就產生于上層社會,它只是上層社會特定人群的文化產物和文化用品;“歌”源遠流長,夏商周之前就有,“詩”則是中國的語言、文化、禮樂制度、人的思想認識水平和境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語》《左傳》記載的“歌”,皆是隨時隨地隨意而歌,不分身份、地位;而“賦詩”卻不是這樣,得有一定身份、地位之人,在特定之場合,方可賦詩。之所以“賦詩”,而不是作詩,這是由其時對詩的尊重決定的,說明其時之人對詩和歌的性質具有明確的認識和界定。
言、歌、舞不是詩,“情”也不是詩。《詩大序》并未言“情志”,而是各自單言“志”和“情”,可見《詩大序》所言的“志”和“情”是有別的。其區別在于:“情”是泛言,“志”則是高級情態、復雜情態的“情”。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此“志”不可用“情”代替。故有“情”動于中,而只能“形于言”,卻不是“詩”。
故《詩大序》下文引入了“治世”“亂世”的概念,意在說明,“詩”是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下的文化產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毫無疑問,“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以及“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不是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語言文字都擁有的功能,故曰“莫近于詩”。今人一看“動天地,感鬼神”,大多以為虛幻不實而不信,殊不知中國最早的“詩”與祭祀禮樂文化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詩”就是在古人“動天地,感鬼神”的祭祀禮儀中孕育產生的,筆者對此另文有論。
“莫近于詩”是作者特意強調的一句話,它是特意為了把“詩”與歌、言等概念相區別而言的。《詩大序》這一表述意在告訴人們:“詩”是人類創造的高級文化藝術形態,“詩”的產生遠在言、歌、舞之后。從社會層面說,“詩”是特殊社會文化背景的產物;從詩人層面說,“詩”是特殊社會文化背景而激發的詩人的高級的、復雜的情感狀態的產物。故發生學意義上的“歌”不可以為經,而詩,即使是萌芽狀態的詩,亦可以為經,《周頌》即是。只有“詩”才可以“正得失……移風俗”云云,閑情雅興絕不是《詩》。
《詩大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云云,稱曰“先王”,這是很耐人尋味的,說明《詩大序》的作者是周代人,是文王、武王、成王的后裔。否則,《詩大序》的作者若是秦漢以后人,可稱之曰“先王”乎?
明確了“詩”之后,故接曰“詩有六義”。下文的主要內容都是針對“六義”而言。
先曰“風”之所由來。“上以風化下”,說的是《周南》《召南》,“下以風刺上”,說的是《國風》中其余十三國風。“主文譎諫”是“風”的要義,正因為“主文譎諫”,故才能“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毛詩正義》曰:“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譎者,權詐之名。托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1]關于《詩》的“主文譎諫”,請參見筆者專著《詩經正義》[2]。
然后接曰“變風變雅”: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上文并未出現“正風正雅”字樣,而下即接曰“變風變雅”,故知“上以風化下……故曰風”數語,既曰正風,又曰變風,既曰風,又曰雅。構思、用語之精巧令人驚嘆,非圣人不能為此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大序》明確認為“變風變雅”的作者是“國史”,這就肯定了《國風》詩篇與民歌無關。
上段言風、雅之所由來,故下段即對風、雅、頌作明確的定義。筆者在此特別關注兩點:其一,“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一國之如何,全系于一人之如何;一人之如何,決定了一國如何。不只某一國如此,各國皆如此;即使現在亦是如此,何況古代君主制社會之國?《詩大序》此語絕不可輕易看過,因為它透露了《詩》的性質,暗示了“詩”的大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風”才有“教”的含義,故曰“謂之風”。不然的話,何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就謂之“風”呢?其二,上段言風、雅之所由來,并未言“頌”,而此段卻同時對風、雅、頌作明確定義。在《詩大序》的表述中,“頌”的出現令人覺得很突兀。尋繹其行文脈絡,不禁令人疑問:“頌”是“詩”嗎?筆者認為,這正反映了《周頌》的特殊性(《詩大序》對“頌”的定義專指《周頌》),也反映了《詩大序》作者立言的兩難和行文處理藝術之高妙。因為《周頌》的本質特性是“歌”,不是“詩”。中國最早被稱為“詩”的是正《大雅》,《周頌》在當時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高級的“歌”和萌芽狀態的“詩”。限于篇幅,在此不展開論述,讀者可參見筆者專著《中國詩歌發生學研究》。
三
人們評價《詩大序》,總愛批評它具有政治功利性,把文學當成政治的附屬物。《詩經》是詩,是文學。可是在《詩經》創作的周代,情形卻非常復雜。“詩”原本就產生于上層社會,產生于統治階級、貴族集團,產生于政治性質的事件,如祭祀、教育等活動。其時詩的創作本身也主要是一種政治性質的行為,而不只是文學性質的行為。就今人來說,其時詩的創作當然是文學創作,但其時之人的這種創作行為卻是一種無意識的文學創作。這種“無意識”決定了其創作的作品不是以文學審美為宗旨,而的確是一種政治功利行為。《詩大序》把周代詩創作的宗旨概括為三個方面:“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把詩之所用概括為五個方面:“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是極其準確、極其真實的。即使后世直至今日的任何體裁的文學,也不會完全沒有政治教化因素。
周代是中國“詩”的產生期,很難想象“詩”一產生就是抒情、審美的,因為在其時,“詩”是如此高雅、神圣的一種新事物,它不可能一開始就是純粹個人性的東西。一開始就是一種純粹個人性的行為,一產生就是以抒情為宗旨的,那是“歌”,不是“詩”。周代正是因為禮樂的興盛,才有了“詩”產生的契機。
詩既然是周代禮樂的產物,那么它就與禮樂密不可分,與歌舞密不可分。換句話說,詩在周代,它本身就是禮樂,就是歌舞。而周代的禮樂歌舞無疑是具有政治功利性的文化,禮樂歌舞的宗旨就是要“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禮樂歌舞的用途就是要“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的創作在周代的宗旨和用途與禮樂歌舞毫無二致。西周時期如此,春秋時期雖然禮樂有所廢弛,但圣人之世的禮樂并未完全廢弛,更未崩壞,所以春秋時期雖然出現了大量個人創作,但《國風》的創作也是極具政治功利性的文化。孔子把詩的功能概括為“興、觀、群、怨”,四個方面無一不指向政治功利性,非以審美、抒情為要義。張潛《詩法醒言》:“詩三百篇辭旨微渺,要非詩中之子所能自作,大抵皆當時學士大夫有所托而言之也。”
然而周代的詩就與審美、抒情無緣嗎?非也。《詩大序》并不否認詩的審美、抒情特性,相反,它一開始就十分肯定詩的抒情特性。沒有了抒情,也就不用寫詩了。但《詩大序》所言的詩的情、志,是指詩的創作的情志動因,非指詩的創作宗旨而言,故《詩大序》得出了“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結論。《詩大序》認為“變風”“變雅”雖“發乎情”,然需“止乎禮義”,其中暗含了一個言外之意:“正風”“正雅”本就是禮義的產物,它們作為“詩”,雖有抒情因素,但它們本身卻是以禮義為宗旨而創作的。《詩大序》顯然不排斥詩的情感、抒情因素。
四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魚麗序》簡直就是一部《詩經》編詩義的縮影。編《詩》者以《二南》為首,意以之象征周王朝之“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這其實正是周王朝的“始于憂”。其后之正《小雅》和正《大雅》象征周王朝的文治武功、治內治外,這即是周王朝的“勤”。經過了“始于憂勤”的周王朝,最終能在《周頌》所象征的“成功”中“終于逸樂”,而“告于神明”了。這儼然是一部后世國君的教本和明鏡。
《周頌》《大雅》《小雅》《國風》,在詩的風格、語言特征等方面,分別有樸拙、疏朗、流暢、精致四種特征,它們大體反映了從西周初期到西周中后期再到春秋時期周代詩歌發生、發展到成熟的幾個不同階段,且四部分詩歌所反映的周人的思想認識水平也各自具有不同特征。因《詩序》一刀切地把“正詩”的創作都歸之于周初成王、周公時,故以《常棣》為“閔管、蔡之失道”,而實則《常棣》的內容與“閔管、蔡之失道”毫無關系,且其詩絕非作于周初。《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戒成王不游樂、閔管、蔡之失道,這是周代歷史的大節,與編《詩》義若合符節。
這種隱去詩篇實際創作情況的編排,是編《詩》者的失誤嗎?非也。編《詩》者本即不欲編排一本普通的詩集,他的本意是欲編排一部經典以流傳后世。詩篇創作的實際情形,也就如同日常生活一樣,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隨機性。一切皆按照實際情況如實加以編排,幾近于一部雜亂無章的大雜燴似的詩集,即使不是圣人,任何一個普通人編輯《詩經》,也不會這樣做。故《詩經》的編排是編《詩》者的杰作,是圣人的大手筆,是圣賢對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是圣賢對中國最早的一批詩歌的升華、提煉和再創造。沒有這種獨具匠心、獨具慧眼的編輯,就不會有經典。
葉適《習學記言》:“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系。無所系,無以詩為也。其余隨文發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多矣。”[3]程顥、程頤《二程遺書》曰:“《大序》文似系辭,分明是圣人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