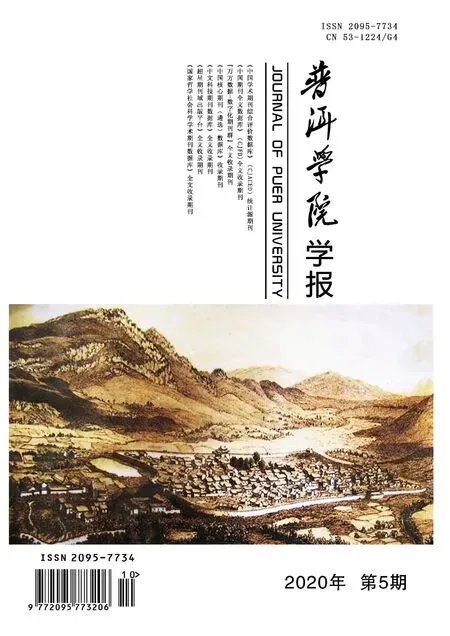《聊齋志異》的詩性敘事研究
伋 靜,錢 敏
1.中共和縣縣委黨校,安徽 和縣238200;2.安慶師范大學,安徽 安慶246000
魯迅先生在《小說史略》中指出,《聊齋志異》雖然寫鬼寫狐,講魑魅魍魎之事,表人世離別悵惘之情,抒書生壯懷之意,然而敘次井然、描寫委婉,用傳奇法,言古今情,能將封建社會的人文、習俗及風尚,有機地融入到故事創作中,使故事在“志怪”的同時擁有抒情與批判的功能。胡適曾在相關文獻中指出《聊齋志異》看似虛幻縹緲,卻包含著蒲松齡對社會黑暗的憤怒、怨恨及對“風清氣正”、“大同盛世”的期盼和向往。在很多短小精悍的故事及篇章中,我們能夠發現蒲松齡筆下的“狐仙”和“鬼魅”并非封建迷信的產物,而是經過藝術加工的、本土化的、平民化的、理想化的“精神”,譬如聶小倩的反叛精神、胡四娘的不屈精神及“鴉頭”的孝廉精神等。這種物化的精神和思想能夠在委婉動人和鏗鏘有力的敘事節奏中形成鮮明的主題意蘊,使《聊齋志異》所要表達的思想和情感,有效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蒲松齡常以“喜人談鬼”、“雅愛搜鬼”自居,但他卻反復感嘆“知己者,常在黑塞青林之間”。所以《聊齋志異》的創作初衷是對作者人生理性和“孤憤”之情的寄托,雖然寫鬼寫妖,以鬼狐暗諷社會,然而在“剔骨挖諷”之間,又流露出書生特有的執著感和憤世情。
一、《聊齋志異》的情節化結構
小說敘事的本質是情節架構和人物編制,是通過構建特殊的“情境”,使讀者感受到作者蘊含在情節中的思想及理念。亞里士多德曾在戲劇創作中指出,故事和情節并非相同的概念,兩者間存在著鮮明的從屬關系,即故事是記錄事件發生順序和演進歷程的載體,而在事件記錄的過程中卻添加了一定的因果關系,形成了情節[1]。《聊齋志異》在開篇卷中通常以簡短的敘事來記錄“古怪”而“神秘”的事件,譬如《尸變》《考城隍》《耳中人》《山魈》《捉狐》等篇章,都是稀奇而古怪、神秘而莫測的志怪故事。胡適也曾說過《聊齋志異》的開篇作品的確為“志怪”之作,然而在情節建構與人物刻畫中,卻相對細膩、委婉。尤其在人物描寫中,逐漸突破了傳統志怪小說的窠臼,將人與物、事與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如在《耳中人》一篇中,蒲松齡雖然沒有交代事件的緣由,然而卻將角色的情態、感知、思想生動地表達出來。如“小人聞之,意張皇,繞屋而轉,如鼠失窟”這處,語句雖簡短,幾個動作卻將角色的慌張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現代文學創作層面,情節化結構注重情感的抒發與表達,注重角色情感和作者思想的融合與流露。這種創作理念和思想,我們能夠在《聊齋志異》中窺見一二。譬如在《小二》中,角色的情感和思想是通過角色的肢體動作和所見所感表現出來的,如“女始著褲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該段文字詳細地闡述了事件的發生過程,雖然簡短,三個動詞卻給人以清晰的畫面感,在情感表達上,“始著褲”生動地刻畫出角色危急關頭不忘自身形象的情感和性格。而在“孤憤”情感上,《聊齋志異》在情節架構上,可以表現出鮮明的片段化特征,能夠凸顯敘事情節的“應然”特質,表現出對“抒情傳統”的發揚和“體認”。譬如以樂事、賞心、美景、良辰的行樂圖卷,充分表達出作者的“烏托邦理想”[2]。部分學者曾從題材和內容的角度出發,將《聊齋志異》的故事與作者的生活經歷作了結合,將其界定為作者思想流露與發泄的載體,有對仕途的抱怨與迷惘,也有對自由、理想的暢想。在這個過程中,蒲松齡將自己的情感有機地融入到故事中,使其成為文章的主體,并借角色之口,將兩種外化的情感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鮮明的主體意蘊。通常來講,詩化的敘事在于情感的抒發,是《聊齋志異》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關鍵。然而在志怪小說創作層面上,情感的表達與呈現,則需要情節作為載體和媒介,使情感的抒發與表達更有遞進性和層次性。詩化敘事過程擁有明顯的“片段化”特征,飽滿而完整的情感,能夠為《聊齋志異》的詩化敘事奠定了基礎。
二、《聊齋志異》個人化敘事視角
《聊齋志異》的主觀敘事和個人化視角主要表現在對鄉間寒士的刻畫上,將個人的偏好和好惡融入到情節編織和敘事的層面上,借此抒發個人的憎恨、憤懣及欲望。不同于傳統的“歷史敘事”和“倫理觀點”,蒲松齡在處理個人情感及敘事思想的過程中,主要以兩個角度出發。首先是對社會現實的傳聞化、軼事化處理。蒲松齡在撰寫《聊齋志異》的過程中,所涉及的題材較為寬廣,不僅涉及貞婦、孝子、烈士、忠臣,更涉及兵政權謀、志怪傳說,還涉及民間趣事和鄉俗傳說。《羅剎海事》便是包含了濃厚的異國風情的小品,而《山鬼》則從民間故事出發,將小人物、小事跡進行傳聞化處理。在整體層面上,《聊齋志異》能夠將明末清初的民變、災害、饑荒、戰爭等社會政變和歷史史實融入到小說創作中,也能夠將個人志趣和理想抱負,有機地整合到文章的創作中。其中,《白蓮教》便以個人志趣為出發點,或概述、或展示白蓮教的興起與沉浮,神秘與怪誕,使《白蓮教》擁有了濃濃的神秘學色彩。其次在題材改寫上,作者能夠將主觀情緒充分地宣泄出來,實現借文抒情的目的。根據相關研究調查顯示,《聊齋志異》中約有25%的篇章是作者根據詩人筆記或前人雜著撰寫成的,所以《聊齋志異》的詩化敘事又有“借鑒”的特征[3]。與原始故事相比較《聊齋志異》的敘述語言存在著明顯的主觀化特質,譬如《續黃粱》便是以《枕中記》作為故事原型撰寫而成,根據《唐國史補》能夠發現《枕中記》中的黃粱夢擁有較強的“寓言特征”,能夠表達作者的悲憫情懷和人生感悟。而《續黃粱》則將《枕中記》的主題變換為對貪官污吏的報應和懲處,用濃重筆墨描繪冥報場景,以此彰顯作者的激憤情感及深思靜觀的理性精神。
個人化視角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層面:首先情節敘事的主觀性,在小說創作中,主要有第一人稱、第三人稱等常規視角,還有介入式第一人稱視角。其中介入式視角主要指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描寫角色的心理、動作及情感,使小說敘事更加多樣化、多元化、層次化、立體化。我國古代的志怪小說和言情小說,主要以第三人稱為主要敘事視角,通過角色塑造和情節敘事,充分地將小說角色的情感展現在讀者面前。而在《聊齋志異》中,人們卻能夠發現明顯的介入式第三人稱視角痕跡。作者雖然以客觀的角度來概括并描寫角色和事件,然而在細節描寫中卻能夠將角色思想情感有機地表現出來,使個人的主張和思想融入到角色刻畫的過程中。譬如寫貪官污吏的昏庸無道、寫普通百姓的封建麻木等,這些都是在細節刻畫的過程中將作者的主觀情感呈現出來的。其次在題材的處理上,根據上文敘述,《聊齋志異》涉獵題材寬泛,能夠將詩人的思想進行轉換,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觀點,這種思想不僅表現在故事題材的處理上,更體現在作者凝練思想和觀點等層面上。如在《花姑子》一篇中,蒲松齡將造成安幼輿和花姑子的悲劇,歸因為封建禮教,歸因為社會迂腐的思想及理念,然而在結局處理上,作者卻以“偽圓滿”結局點睛,提出文章的本質,并借此諷刺人性中的貪婪和迂腐。這種處理手法幾乎在每篇文章中都能看到,然而這種借他人之口達自己之意,卻充分契合了蒲松齡的處世觀和價值觀,是作者思想內化的現實表征。
三、《聊齋志異》的詩意化和虛幻
通常來講,文學空間是虛構的物理空間,擁有較強的審美性、象征性和隱喻性特征,能夠有效地表達和流露出創作者的所思所感,能夠將客觀現實以主觀化的形式融入到小說敘事的過程中。在《聊齋志異》的敘事空間中,文化隱喻的敘事功能較為明顯,能夠將虛幻空間和擬實空間排除在外,注重“過濾現實要素”后的單純性的、純粹性的敘事載體。在這種敘事空間中,蒲松齡能夠將角色進行“激情的演出”,使小說敘事成為詩性演繹的載體和映射。其中擬實空間主要指對社會現實的描繪和滲透,虛幻空間則指對事件的編織和羅列,過濾掉現實的純粹性敘事空間,則指角色主觀化的思想和現實。這種虛幻空間,能夠使現實景物表露出較強的詩性特征,表現出作者的詩化思想。“山雨欲來風滿樓”便是將山雨到來前的情景進行了擬人化處理,能夠給人以別樣的感覺。然而這種感覺卻是構建在主觀化敘事的基礎上的,是通過視角的感官化,將詩情畫意完整地展現出來的。從詩歌創作的角度出發,這種虛幻空間主要指創作者的“借物喻人”和“借景抒情”手法,使創作者的情感充分地映射在詩歌的創作與撰寫過程中的[4]。
在《聊齋志異》中,虛幻空間主要體現在對周遭環境的描寫上,這種描寫突破了擬實空間和虛幻空間的限制,使人物情感和客觀事物得到了充分的融合。簡而言之,讀者通過蒲松齡筆下的環境描寫、景觀描寫,可以深入地了解角色所特有的思想和情感。部分學者和專家曾將這種包裹在景觀描寫下的“思想”或“情緒”稱為隱喻,然而筆者卻認為《聊齋志異》中的隱喻主要表現在虛擬空間中,表現在“洞府”“仙鄉”“夢境”“地府”等層面上。這種境界的設置與構筑,鑄就了《聊齋志異》的詩情隱喻。其中洞府、仙鄉、夢境是角色渴望征服、逃脫時間流逝的詩情世界,因此在情節架構上,蒲松齡著重表現了現實世界和“仙鄉洞府”的反差,通過仙界時光的流轉映襯出“此生易逝”的情感,進而構建出氛圍濃郁的“意境”。在這里“洞府”和“仙境”是“世外桃源”的象征,是逃脫世俗枷鎖的表征,同時也是承載作者思想和情感的載體,能夠有效地將作者的理想“物化”地表現出來。而這也是《聊齋志異》詩意化的重要體現,能夠將小說敘事的情景轉化為情感抒發的“意境”,而這種意境的表達與融合,又將成為讀者獲得“詩情畫意”的載體,進而在隱喻和象征的過程中,使《聊齋志異》的人文性更加明顯,更加鮮明[5]。仙鄉偶遇題材是蒲松齡結合男女的柔情、自然的風光及人際的溫馨,所流露出的文化氣息,描繪的是喜聞樂見的普世愿望,濃縮了作者對人世間的感慨與蒼茫。雖然在虛幻仙鄉的過程中,蒲松齡能夠通過想象和虛構的故事,體現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逃避,然而在詩意景觀的描寫上,卻將人生如夢的情感和思想,表達得酣暢淋漓,使仙鄉場景更具有詩情、詩景和詩意。最后在語言層面上,《聊齋志異》的詩意化主要體現在句式和修辭上。縱覽全文可發現,很多篇章多以三字、四字、七字為主,無論在情節敘事還是在語言描寫上,都有較強的節奏感,部分篇章則以對仗、對偶、押韻等方式,使句式層次清晰,節奏強烈。尤其在場景敘事和語言描寫等方面,這種簡短的語言,能夠極大地增強小說的意境感,使志怪小說擁有較強的詩歌性。藝術的精髓在于情感,無論是文學、繪畫、建筑,還是音樂,都注重情感和思想的表達,而詩意性則指作者將情感進行放大,以語言和意境的形式將情感呈現在讀者面前,使其對隱含其中的思想進行更直觀的體驗。譬如觀賞者只有在深入地觀賞和體驗作品的過程中,才能實現情感的共鳴,獲得豐厚的審美體驗。而《聊齋志異》的詩意敘事,則具體體現在意境構建、情感表達、畫面呈現、思想抒發等層面,以此使讀者在感受和體驗虛擬世界、擬實世界和虛幻世界的過程中,更好地感受到小說的審美性、思想性和藝術性。
四、結語
《聊齋志異》擁有較強的思想性、藝術性、人文性及文學性,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朽,充分表達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負。在敘事結構和空間層面上,架構出藝術化的詩意空間,使小說的表層與深層有機地融合起來,演化成時空、視角、結構相結合的詩性特質,使蒲松齡的大同思想、人文關懷及道德理念更好地呈現在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