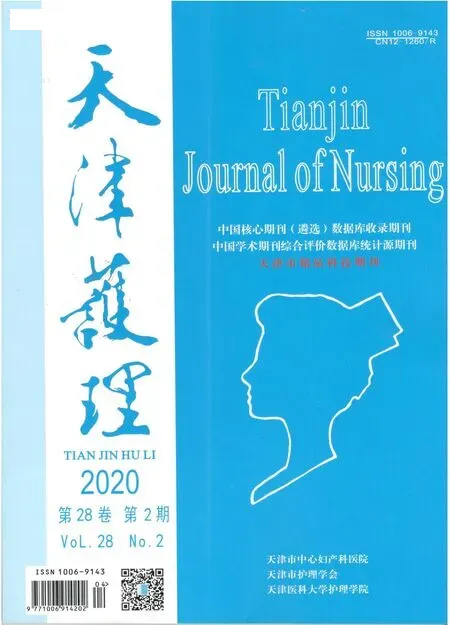兒科慢性疾病患兒主要照顧者照顧負擔的研究現狀
齊素紅 董梅
(天津市天津醫院,天津 300211)
兒科慢性疾病是指長期遷延不愈、 病情反復的疾病,如神經系統的腦癱、癲癇,呼吸系統的哮喘,循環系統的先心病,泌尿系統的慢性腎炎,骨科系統的股骨頭壞死等疾患。 兒科慢性疾病可出現機體的各個系統[1]。 慢性疾病患兒經常因病情的變化或出現并發癥、合并癥反復住院治療,而且患兒由于自理能力差, 給主要照顧者帶來了沉重照顧負擔,降低了照顧者的生活質量,也不利于患兒疾病的治療和康復。 本文旨在通過文獻回顧兒科慢性疾病患兒主要照顧者照顧負擔的研究現狀,分析對照顧者照顧負擔的影響, 以期對兒科慢性疾病患兒的照護問題的制定政策、 采取護理措施提供依據和參考。
1 照顧者和照顧負擔的概念
1.1 照顧者 照顧者是指給患兒提供照顧的人,由收費與否界定為正式照顧者和非正式照顧者。 前者是指收取報酬的醫護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等, 后者通常指的是提供無償照護的家庭成員、親朋好友等[2]。 在有些研究中將照顧者分為專業照顧者和非專業照顧者,專業照顧者也就是通過專業培訓的,如:醫生、護士、受過培訓的護工、陪護等。 非專業照顧者指的是:父母、孩子、親朋好友等[3]。 根據照顧時間可將照顧者分為主要照顧者和一般照顧者, 主要照顧者是指主要承擔照顧任務的照顧者, 有文獻指出主要照顧者是指一周照顧時間超過5 天, 并且一天的照顧時間不得低于8 小時, 同時還承擔大部分照顧任務的親屬[4]。 國內外的研究均以主要家庭照顧者為主,主要家庭照顧者絕大部分是患兒父母[5]。 蔣忠燕[6]在對自閉癥患兒的研究中將康復機構的照顧者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其照顧負擔。
1.2 照顧負擔 照顧負擔是指照顧者為照顧患者所付出的犧牲或對照顧者產生的不良后果。Zarit 等[7]將其定義為照顧者因照顧患者而感受到失落、失望、孤獨等情感變化,并付出身體、精神、情感、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代價, 強調的是照顧過程中產生的負面結果。 George 等[8]認為照顧負擔是指照顧病患的家庭成員在承擔這項任務時所遇到的心理、軀體、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Goodman[9]的觀點是照顧者負擔是因照顧患者時所遇到的問題而導致照顧者感受到的不利影響。 雖然不同學者在文字表達上有所不同,但總的觀點認同的照顧者負擔是指照顧者在承擔照顧任務時遇到的心理、軀體、經濟、社會的問題而產生的壓力感和令其不愉快的感受。
2 兒科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照顧負擔的情況
目前國內外對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照顧負擔的研究,多集中在腦癱、自閉癥、癲癇等疾病患兒的照顧者。 研究的方法主要分為橫斷面的問卷調查性研究和訪談式的質性研究。 在國內外的相關調查研究中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大多在輕、中度的負擔水平,長期對慢性疾病患兒的照顧不可避免的對照顧者生理、心理、社會、經濟等造成不同程度的負擔。 總結發現客觀負擔相對于主觀有更高的負擔水平, 也就是說客觀負擔大于主觀負擔[10]。分析認為慢性疾病患兒的照顧者主要為家庭照顧者特別是患兒父母, 由于其父母一般處于青中年的年齡段, 大多有自己的工作、社交,但是由于對慢性疾病患兒的長期照顧勢必會對其工作、社交等產生影響。 有的甚至是父母一方辭職全職在家照顧患兒,這必然會對其社會、經濟等方面帶來負擔[11]。 吉彬彬等[12]對孤獨癥兒童照顧者照顧負擔的研究顯示照顧者處于中等負擔水平, 并且照顧者覺得發展受限負擔和時間依賴負擔高于情感性負擔。 慢性疾病的病程較長有時甚至伴隨患兒終身, 病情時有反復但在長期復雜的照顧過程中照顧者的心理情緒負擔不可避免。鄧葉青等[13]學齡前期腎病綜合征患兒照顧者真實體驗進行研究, 心理負荷過重是患兒照顧者的主要感受。
3 兒科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
3.1 患兒因素
3.1.1 疾病的嚴重程度以及預后 疾病越嚴重預后越差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越重, 因為疾病越重往往提示患兒的自理能力越差,對照顧者的依賴程度越高。 照顧者除了對患兒進行疾病的治療外, 還要負擔患兒的飲食起居等生活護理。 照顧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體力來照顧患兒,郭妙蘭[14]在對哮喘患兒父母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得出: 患兒疾病的控制程度與父母的照顧負擔有相關性。
3.1.2 患兒的年齡 低年齡段的患兒由于疾病、 治療等原因配合程度差、 哭鬧等原因也是被認為加重照顧負擔的危險因素。高國貞等[15]在哮喘患兒家屬照顧負擔的質性研究中提到, 低年齡段的父母感到照顧負擔更重。
3.1.3 患兒治療的付費方式 在患兒慢性疾病的治療中主要的付費方式有:自費、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農村合作醫療、商業保險等,自費者會加重照顧者的經濟負擔。
3.2 照顧者因素
3.2.1 照顧者的年齡與自身健康狀況 照顧者的年齡越大或是自身的健康狀況越差, 由于本身的體力不足所以更容易感到更重的照顧負擔。 Anum 等[16]在研究中指出父母的心理健康狀況與照顧負擔呈負相關。 照顧負擔會影響照顧者的健康狀況,同時照顧者的健康狀況又會加重照顧負擔。
3.2.2 照顧時間 主要家庭照顧者照顧負擔大于其他照顧者的照顧負擔, 照顧者的人數越少平均的照顧時間越長照顧負擔越重。 照顧時間影響照顧者的生活質量,生活質量與照顧負擔呈負相關。 照顧者照顧患兒的時間越長其自身的生活質量受到的影響越多,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越重[17]。
3.2.3 照顧者的性別 對慢性疾病患兒的照顧大多由父母來承擔,患兒母親承擔了照顧的主要任務。 但是由于女性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比男性照顧者承受更多照顧負擔。
3.2.4 文化程度 照顧者的文化水平不同, 照顧能力也有差異。 研究顯示,照顧者的文化水平與照顧能力呈正相關。 照顧者的文化程度越高掌握疾病相關知識和照顧技巧的能力越強,應對能力越好,自我效能感高,因此對照顧負擔的感受越輕[18]。
3.2.5 應對方式 一般認為應對方式是一種包含多種策略的、復雜的、多維的態度和行為過程。 積極的應對方式可以改善人體的應對過程,減輕壓力源。 劉民輝等[19]通過對癲癇患兒父母照顧負擔與應對方式的相關性研究發現,患兒父母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有利于家庭團結, 促進家庭成員的合作和保持樂觀的態度,積極地應對方式與其照顧負擔呈負相關,積極的應對方式能夠降低患兒父母的照顧負擔。Gage[20]認為照顧者的應對方式與自身的心理健康有相關性,積極的應對方式對照顧者自身來說是積極因素, 消極的應對方式則是照顧者產生抑郁焦慮等負性情緒的高危因素。 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的應對方式隨著患兒疾病病程的發展而發生變化,葉增杰等[21]在對229名腫瘤患兒父母進行調查發現在患兒疾病的急性期(確診后的3 個月內) 應對方式一般為防御性的,例如:憤怒、否認等,但是在半年或是1 年以后應對方式一般為相對積極的。 這種變化與自身調節和醫務人員的指導有關。
3.2.6 社會支持度 是個體主觀感受或(和)客觀接收的源于正式或非正式支持性團體所提供的社會資源,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率[22]。社會支持具有緩沖應激的作用,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社會支持是目前研究比較成熟的因素。 研究顯示在患兒住院期間照顧者獲得的社會支持水平高于出院后, 可見我國針對慢性疾病患兒的延續護理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和進一步的提高。 照顧者獲得的社會支持中客觀支持大于主觀支持, 對社會支持的利用率與照顧者的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文化程度越高對社會支持的利用率越高,城鎮照顧者所獲得社會支持大于農村照顧者, 并且對社會支持的利用率也較高[23,24]。
3.2.7 自我效能 是個體對自己成功完成某項活動的自信程度。 這種自信心有助于個體有效實施并完成任務或者克服困難,減輕了照顧者感知的負擔程度。可能的原因是自我效能感好的人主動參與完成照顧任務,學習照顧技巧,選擇較為積極的應對方式。 國內學者李福球[25]對精神發育遲滯兒童家長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中得出:自我效能與照顧負擔呈負相關,自我效能感越低的照顧者照顧負擔越重。
3.2.8 其他 包括家庭收入、居住地、宗教信仰、照顧者與患兒關系等。 照顧者家庭日均收入的19%~35%用于支付患兒的健康相關費用經濟壓力沉重[26]。 在農村,由于醫療保障體系和照顧資源的欠缺,照顧者經濟壓力更顯著[27]。 照顧者與患兒關系越親近,責任感越強,照顧時間、精力投入越多,身心負擔越重[28]。
4 兒科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照顧負擔對生活質量的影響
慢性疾病患兒需要照顧者付出大量的時間、體力和耐心。 這種長期照顧是以照顧者自身的生理、心理的消耗為代價, 對照顧者心理健康的影響較身體健康的影響更為顯著。 照顧者的心理負擔重,也會導致生活質量的下降。 但是在對不同區域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宗教照顧者的研究中發現, 照顧者在照顧患兒的過程中承受負性情緒負擔, 也會獲得一些積極的心理體驗,比如:滿意、自尊和自我效能提高等,國外的研究者將之稱為創傷后成長[29]。多數照顧者為需要照顧患病的孩子和贍養年邁老人的社會 “夾心族”,他們由于照顧行為勢必造成他們本該在社會上承擔的角色丟失,比如:工作的減少甚至丟失,這對他們的生活來說是消極的影響, 會導致生活質量的降低。 生活質量降低又會反過來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 生活質量與照顧負擔呈負相關[30]。
5 小結
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以往單純的調查研究較多。 近年來關于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照顧負擔的質性研究越來越多, 這比量性測量工具更能深入的挖掘照顧者的真實感受。 亦有量性研究和質性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反應了照顧者的照顧負擔現狀。 相對于國外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照顧者長期的追蹤調查比較少, 缺乏長期的縱向隨訪得出的照顧者照顧負擔的動態變化情況。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側重于這一方面的研究, 可以更好地了解兒科慢性疾病患兒照顧者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 以及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為相關部門制定政策和護理人員開展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