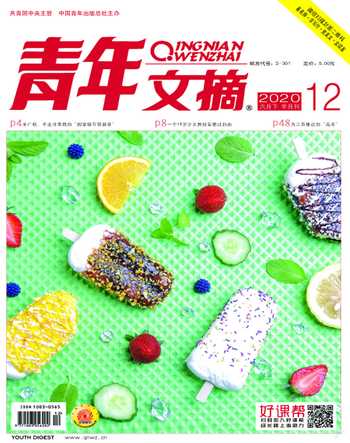陶勇:是重生,而不是活過來
尤蕾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陽醫院眼科發生暴力傷醫事件,三名醫護人員被砍傷,另有一位患者受傷,出診醫生陶勇受傷最重,后腦勺、胳膊多處被砍傷。
幾個月后,陶勇漸漸度過暗黑時刻,現在,他已經回到診室,恢復出診。而經歷過這件事,他覺得自己不是“活過來”而是“重生”了。
傷后,陶勇給盲童寫了首詩,希望有一天可以帶他們去巡演。“盲童也需要一條自食其力的路。他們眼中無光,心中應有光。”他受邀在網上講課,如果不能再拿手術刀,他想以后就做科研,帶學生。他還想過,今后或許會寫個小說。陶勇一直喜歡寫東西,之前,但凡有空,他都會寫寫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和事。
陶勇就這樣“出圈”了——“陶勇超話”閱讀量過億,還有專屬的“桃花源”粉絲群,粉絲們喜歡喊他“陶三歲”……
“桃花源”的slogan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處不是水云間”,暗合了陶勇的成長心路。陶勇說自己就是個普通的青年醫生,有點成績,成長不易。“我現在的流量大概是曇花一現,但也算帶給過大家正能量。”
名利之間,看個人想要什么
陶勇病情稍稍穩定,就用沒受傷的右手打完了《眼內液檢測》的后記。這是他8年經驗的總結,“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都是舶來品,到了我們這代人,有責任做一些原創性貢獻。”
從學生時代開始,陶勇就不喜歡灌輸式的機械教育,認為這容易埋沒獨立思考的能力。醫生王惠從進入醫院就跟著陶勇學習,“他最與眾不同的就是愛思考,帶學生是引導式、啟發式,而非灌輸”。
1997年,陶勇考入北京醫科大學(現更名為北京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專業。他的同學、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兒科醫生左英熹說:“他是個很單純的人,我和他從本科到研究生都是同學,覺得他至今都沒怎么變。”沒有變的,一指心性,二指相貌。
左英熹記憶里,陶勇一開始并不顯山露水,成績也在中等。“他不是那種大學里特別出挑的男生,不談戀愛,也很少參加社團。”陶勇屬于厚積薄發型,5年里,他堅持不懈地學專業、搞科研。保送研究生時,97級5年制臨床醫學中只有陶勇一人進入北大人民醫院眼科,“金眼科,銀外科。保研競爭非常激烈,成績特別優秀的才有機會報考眼科”。
醫生不是一個可以用性價比衡量的職業,尤其身處公立醫院,王惠覺得“總是需要一點理想支撐的”。陶勇不是沒有想過高薪酬的私立醫院也是一條路,但那里沒有公立醫院豐富的病例,“這猶如名與利之間的選擇,看個人想要什么”。
因為科研做得好,陶勇受到醫院重視,31歲時已經做了幾千臺手術,這對于博士畢業僅3年的醫生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對于一件一輩子都要干的事,應該學會享受每天多積累一點的樂趣。”陶勇說。
他把醫學當成修行之道。一次手術中,陶勇剛把患者眼睛打開,顯微鏡的燈就滅了,怎么辦?陶勇說,必須沉著冷靜,繼續完成手術,而整個過程中患者完全不知情。“上學時,老師就說過,如果遇到手術中停電,肚子已經打開,血還在流,慌亂的話就不知道刺哪了。”這就是心理素質的培養,能讓人保持堅毅的心性。
一糾結就干了這么多年
陶勇的同學經常開玩笑,他們這個班如果能出大師,就指望陶勇了。專業上陶勇確實在同年齡段醫生中一騎絕塵:35歲晉升主任醫師,37歲擔任知名三甲醫院科室主任,成為博士生導師。陶勇覺得是自己“幸運”,但事實并非這樣輕松。
陶勇選擇了眼科的一個冷門專業——葡萄膜炎。全國從事葡萄膜炎治療的醫生鳳毛麟角,朝陽醫院漸漸成為該病患者的首選。很多患者專門為了掛陶勇的號從外地趕來,“陶主任周一的門診不限量,經常晚上9點或10點才送走最后一位患者”。通常,陶勇一天要接診六七十位病患。周二手術日,從早晨7點半開始,他要連續做十幾臺手術。
認知心理學家安德斯·埃里克森說,想成為一等一的高手,最重要的內在因素就是心甘情愿地長時間接受千錘百煉。要出類拔萃,必須有努力不懈的意志。
“真正成為醫生后,才覺得學醫的過程不算苦,從醫才真的苦。”陶勇覺得那些千錘百煉固然有專業上的探索與精進,也有心性、意志在動搖與堅定間的不斷循環。
每次出完門診,陶勇都有“不干了”的沖動。“我火車票都買了,能不能讓我先看?”“我一大早就來了,我能先看嗎?”……一撥撥患者圍著他,時不時吵起來。葡萄膜炎本就復雜,需要醫生靜下心仔細詢問、診斷,“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集中精力”。而一旦碰上不講理的病患,陶勇想抽身都難。
晚上,陶勇常帶著一大堆負面情緒入睡,總愛做噩夢。第二天,他有時還會氣呼呼的。但下一次出門診,陶勇依然雷打不動地準時出現。他每一次都糾結:本來做葡萄膜炎的醫生就少,這些患者就是奔著自己來的,如果他都放棄了這些人,就等于眼睜睜看著患者瞎了,他于心不忍。
王惠和左英熹能感覺到,陶勇打心眼里喜歡做醫生、熱愛醫學。很多醫生尤其是外科醫生喜歡做手術甚于做科研,經常會以各種理由推脫科研項目,而陶勇至今一共發表了98篇SCI論文。
時間哪來的?兩臺手術之間,換臺子或消毒的十幾二十分鐘,他不是查文獻就是寫文章。陶勇總愛跟年輕醫生說,要把時間利用起來,年輕的時間就這么短,過去了就沒有了。
承擔起社會責任
每一次傷醫事件發生,輿論中總會混雜著多種聲音——身處醫療圈內的人抱團取暖,圈外有人出離憤怒但也有人幸災樂禍。
生氣嗎?“要是這樣就生氣,我不得氣死?”即便刀已經砍向自己,陶勇依然覺得,出現異樣的聲音很正常。醫患之間,不僅僅是信任那么簡單,它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
同時,起源于巫術的醫學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門經驗主義科學,離不開“信則靈”的法條。陶勇經常遇到患者家屬拿著一張寫滿問題的A4紙,要求他逐條給出明確結論。然而,坐了長途火車或飛機“投奔”醫生的患者和家屬通常會失望,因為“醫學很大程度上是經驗科學,與物理學不一樣,無法通過公式推導出結論”。
最怕的是遇到患者和家屬不信醫生。一位患白塞氏病的小伙子被父親帶到陶勇的門診。當時,患者雙目接近失明,陶勇為其制定了治療方案。兩個月后,陶勇又一次接診了這個小伙子,發現他的治療效果不明顯。陶勇覺得奇怪,追問之下才知道,患者的家人自作主張改了治療方案,“患者的父親和哥哥比著拿主意”,就是不信醫生。
當然,醫患之間的不信任不是一時半會可以解決的,要一步一步來。受傷后,陶勇呼吁安檢措施在醫院落地,“上天給我留了條命,是要我承擔起這個社會責任,讓善良的醫護不再受傷害,這比我繼續眼科事業還重要”。
“一再發生的傷醫事件,希望到我這里,可以畫上句號。”陶勇還希望,疫情期間,大家不要“捧殺”醫護人員。因為抬高公眾對于他們的心理期待,很可能在回歸正常秩序后成為醫患矛盾的導火索。
(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