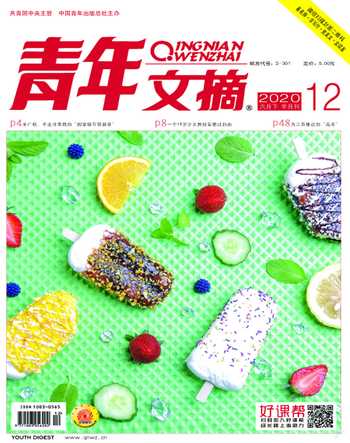全世界最喜歡打你臉的,肯定是法國人
鐘無艷

法國人一向愛跟別人唱反調。你要是問他們為什么如此沉迷說“不”,他們多數會搖頭皺眉打你臉:“不,這不是真的,我不信。”
不愛拒絕,不是法國范兒
在法國,你得時刻做好聽抱怨和慘遭拒絕的準備,因為法國人可以有1萬種方式說“不”。
別輕易給老人讓座,也別輕易做“準紳士”隨時對年輕女士伸出援手,大多數都會被禮貌地拒絕。別以為法國人只是對陌生人愛說“不”,越親近的人,越容易脫口而出說“不”。
當你興致勃勃想到個點子跟朋友分享時,別想著得到什么鼓勵——“你這個絕對行不通,已經有人做過這個了。”
要是親密的伴侶,不愛嘮叨說不,都進不了一家門。在法式親密關系中,說“不”似乎成了一種變相的情趣。丈夫向妻子提議計劃夏天去哪里度假,例行準備大概三個點子。前兩個都是拿來當炮灰的,最后一個才是心中所選。
這也怪不了法國人,他們用法語說“non”的慣性,相當于美國人說“yes”那樣自然而然。
拒絕是他們交流的常態,這并不代表他們不懂得傾聽,他們只不過習慣用“不”來接茬,這樣才有你來我往的對話交流而已。
法國人不僅日常交流愛拒絕,他們最舉世聞名的一種拒絕,叫拒絕說英語。法國人總給人一種“拒絕全球化”的氣息。外國人來到法國,總得花時間適應,因為法國并不想花心思來適應你。
雖然名為世界時尚之地,但從精神上說,法國仍然是“鄉村的”,對本土的事物自有一套堅守的原則。他們自言廚藝、葡萄酒、時裝和香水是無與倫比的法國范兒,至于什么“新技術消除了距離”的流行論斷,他們并不關心,也不信任。
法國人的拒絕,怪天性反骨
國內曾有個詞很火,叫“討好型人格”。這種毛病壓根不會出現在法國人身上。
因為在法國人眼里,自我認知永遠高于別人的看法,同樣,他們也不愛夸別人,因為贊美不會來源于別人的目光,說“不”正是他們想要追求的一種真誠、坦率、獨立的關系。
法國喜劇演員奧利維·吉勞德在他的個人秀《一小時變成巴黎人》里就解釋過他們為什么愛說“不”——用“不”做回答,是為了讓你有機會隨后說“是”。相反,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說“是”,就沒法再說“不”了。
拒絕是為保障自己有私人空間和距離,有余力做出理性和獨立的選擇。也就是說,法國人說“不”,只是下意識的語氣詞,并不是真的意味著“不”。
你可能會覺得,法國人為什么非要耍這樣的花招?不同的國家,都有不一樣的語境文化,在法國人的教育里,他們打小就把“不”掛嘴邊。
法國孩子所受的教育里,學會說“不”是思辨教育的一大基本入門,言外之意就是激發對方辯論。就算獲得良好成績,都必須要解釋為什么沒有拿到更高的分數。
這就是為什么,法國商人總會給人一種“粗魯”的印象。在會議上直面沖突,把所有矛盾攤在臺面上辯論,這可以說是他們的一種天性。法國人腦海里自能形成一套辯論式的思維。
都說世界上最薄的書,應該包括法國人的勝戰史。法國人被嘲是“二戰”中最慫的一個軍隊。他們一向不擅長武戰而擅長舌戰,他們最熱衷的戰斗,就是對國內權威的抗議。
國外版知乎Quora上,關于法國有幾個很火的問題:“我為什么不喜歡法國?”“為什么你要離開法國?”
底下有很多對法國人的不知足、悲觀消極,以及傲慢無禮的吐槽。就連法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我們法國人一年365天都在抱怨,什么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永無止休地發牢騷,說法國是抗抑郁藥物消費大國也不為過。”
法國人的“non”,就是擁抱生活的“yes”
法國人最難搞的“不”,在于不愿改變現狀的“懶”。
當然,法國人這種“懶”,也可以是一種享受活在當下的生活藝術。誰說生活一定非得為了未來而改變,享受現在,拒絕改變也不見得不好。
在巴黎街上,看到那些懶洋洋倚靠在橋上,享受著奶酪、法棍和葡萄酒野餐,一張嘴就像開了水的壺口永無休止的家伙,就知道他們是法國人。當然十有八九他們可能是在抱怨:辦公室好吵、咖啡不好喝、假放得太少了、天氣不好……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有項調查顯示,法國人每天平均花9小時睡覺,每天花在飯桌上的時間是美國和加拿大人的兩倍之多。
也有人做過統計,美國人花1個小時能完成的事,法國人要用6個小時乃至更長的時間完成。要是你有個法國丈夫,他突然心血來潮說要給你做頓法國菜,急性子的人一定會給氣壞了。他會在做飯的過程中,看著電視聽著音樂嘴里還哼著歌,將一頓飯打造成2個鐘頭以上的藝術品。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其實不是想給你做飯,而是享受自己做飯的感覺。
法國人的“不”,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對于平庸無趣生活的拒絕。“不”,其實也是對擁抱高品質精神生活的“是”。
如果說美國人就像一只積極友好、總愛搖著尾巴的樂天狗,那法國人絕對就是一只慵懶癱在地上誰都不想理的高冷貓。
生活對他們最大的樂趣就在于,一邊懶洋洋享受著太陽,一邊喋喋不休抱怨無趣的現狀。但好在最后,都會伸伸懶腰來句:噢,不,這就是人生。
這又何嘗不是法國人可愛的一面呢?
(摘自“九行”微信公眾號ID:jiuxing_neweekly,小黑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