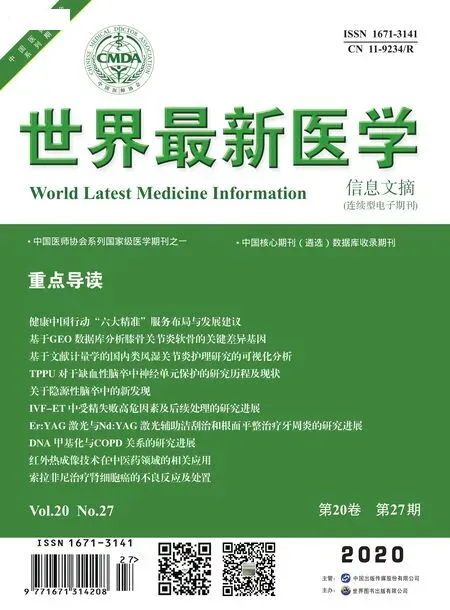TPPU 對于缺血性腦卒中神經單元保護的研究歷程及現狀
黃攀,張琳蕾,易興陽★,韓釗★
(1.德陽市人民醫院,四川 德陽;2.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浙江 溫州)
0 引言
缺血性卒中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發病率高,占所有腦卒中的80%左右,溶栓治療和神經保護治療是其兩大主要治療策略。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是唯一獲得批準的缺血性卒中的溶栓藥物,其溶栓療效已經在臨床實踐得到證實[1]。由于受到時間窗狹窄(發病后4.5小時內)和顱內出血風險的限制,限制了溶栓治療在臨床上的廣泛應用,因此,神經保護治療一直是缺血性卒中治療領域的夢想和希望。近三十年來,針對腦缺血病理生理環節開發了多種神經保護劑,如抗氧化劑、鈣通道拮抗劑、興奮性氨基酸受體抑制劑和神經營養因子等,全球進行了1000多個腦保護實驗研究和100多個臨床研究,大多在動物實驗有效而臨床試驗無效,導致臨床轉化失敗[2]。迄今尚無有效的神經保護劑獲得臨床指南推薦[1,3],但是人類研發有效神經保護劑的探索一直沒有終止。2011年美國卒中學術產業圓桌會議(Stroke Academic Industry Roundtable,STAIR)提出了腦卒中神經保護研究推薦意見[4],這促使我們轉換思路,為研發有效腦保護藥物奠定基礎。
1 腦缺血后神經單元(NCU)損傷和可能的損傷機制
NCU在缺血性腦損傷過程的作用及機制目前還沒有闡明,目前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以下幾個方面:(1)TJ結構破壞。缺血缺氧引起內皮細胞TJ相關蛋白的表達以及定位改變,導致腦微血管內皮屏障功能下降。(2)蛋白質磷酸化信號轉導途徑對BBB通透性改變的調控。其中研究較多的是酪氨酸蛋白激酶(Protein Kinase C,PKC)和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途徑。雖然相關的大量研究證實了這些信號通路參與到對TJ的調控,最終影響BBB的功能,然而具體的信號調控機制還沒有闡明。(3)炎癥和氧化應激對BBB功能的破壞。腦缺血再灌注時,血管內皮細胞粘附分子表達,促發炎癥級聯反應,導致炎性細胞粘附聚集和遷移,這是BBB損傷的基礎。炎性細胞聚集,產生大量的蛋白水解酶,特別是MMPs,導致血腦屏障的破壞。(4)星型膠質細胞參與對BBB完整性的維持障礙。AQP4主要分布于星型膠質細胞足突,是介導水進入腦組織的最主要蛋白。腦缺血損傷后,AQP4表達升高,水通道開放,大量水分子進入細胞內形成細胞內水腫,引起血腦屏障破壞。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和p38 MAPK信號通路參與對水通道蛋白4的調控。(5)近年研究表明,細胞凋亡在腦缺血中可能起主導作用,腦缺血損傷后缺血半暗帶產生的主要病理生理機制之一是細胞凋亡,線粒體結構和功能改變在細胞凋亡中起關鍵作用[18]。腦缺血后NCU和BBB損傷的線粒體細胞凋亡信號通路是目前關注的熱點。
2 線粒體細胞凋亡信號通路在NCU 損傷中的作用
線粒體作為細胞生物氧化和能量轉換的主要場所,線粒體的結構、功能異常與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發生、發展密切相關。腦缺血后注線粒體功能障礙的機制涉及氧自由基損傷、鈣超載、線粒體通透性轉換孔( mitochondrial p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MPTP) 的異常開放、線粒體結構損傷等。(1)線粒體超微結構改變。表現為線粒體內膜結構及線粒體嵴結構的改變:線粒體腫脹、分解、消失、胞質密度增加。(2)線粒體產生自由基功能的改變。自由基被認為主要產于線粒體, 正常情況線粒體氧自由基水平較低, 缺血時其水平就會升高,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增高。(3)線粒體呼吸鏈酶和ATP酶活性的變化。線粒體內膜有按一定順序排列的酶和輔酶,其中酶復合體Ⅰ、Ⅱ、Ⅲ、Ⅳ組成呼吸鏈。呼吸鏈中的酶復合體易受到缺氧影響,直接影響了ATP 的生成。(4)線粒體膜電位的變化。缺血/再灌注時的各種有害刺激,如缺氧、線粒體內Ca2+增加,都可造成MPTP 開放,從而引起線粒體膜電位下降,甚至消失,呼吸鏈斷裂造成細胞死亡[19]。(5)線粒體內細胞色素C的改變。線粒體內細胞色素C(cytochrome C,CytC)是核DNA編碼的蛋白質,是線粒體電子傳遞中復合體Ⅲ和Ⅳ之間傳遞電子的載體,腦缺血時CytC的釋放可啟動細胞凋亡。(6)線粒體DNA及其表達的改變。線粒體DNA(mtDNA)是氧化磷酸化系統重要酶系的前體物質。mtDNA 的損傷則可引起氧化磷酸化酶功能的改變,還可加速細胞凋亡的發生。(7)腦缺血后細胞能量代謝的恢復是細胞其他功能恢復的基礎,若細胞能量代謝障礙持續存在,則必然導致細胞凋亡或壞死,而線粒體在細胞凋亡過程中起重要作用[20]。腦缺血線粒體損傷可能從以下幾方面誘導細胞凋亡:A.線粒體CytC不僅在能量代謝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且其由線粒體內釋放入胞質,是啟動依賴CytC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ysteinylaspartatespecificproteinase,caspase)途徑細胞凋亡的重要步驟;B.線粒體損傷,ATP生成減少,細胞功能障礙;C.線粒體損傷,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反應,自由基產生增多,導致mtDNA的損傷、細胞膜損傷;D.線粒體內膜的MPTP的開放形成了線粒體通透性轉變(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MPT) ,MPT是細胞損傷引起凋亡或壞死的共同通路[21]。腦缺血線粒體損傷結果引起前-凋亡蛋白Bax的活化,該蛋白誘導線粒體釋放CytC,形成凋亡小體,啟動caspase-9的活化,之后死亡執行因子caspase-3和caspase-7被活化,通過蛋白水解酶使細胞崩潰,導致BBB和NCU的損傷。在這通路中B淋巴細胞瘤-2(B-cell lymphoma-2,Bcl-2)等抗凋亡蛋白、凋亡抑制因子以及JNK/p38MAPK信號通路參與了線粒體介導細胞凋亡的調控[18]。
2.1 花生四烯酸代謝通路
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是人體內心腦血管活性物質的前體,其代謝產物與腦血管病的發病密切相關[5]。AA的細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CYP)代謝通路是近年研究的熱點[6]。AA在CYP羥化酶作用下生成羥基二十碳四烯酸(hydroxyeicosatetraenoic acid,HETEs),在CYP表氧化酶作用下生成環氧二十碳三烯酸(epoxyeicosatrienoic acid,EETs),EETs再經過可溶性環氧化物水解酶(soluble epoxide hydrolase,sEH)作用下生成生物活性較弱的二羥基二十碳三烯酸(dihydroxyeicosatrienoic acid,DHETs)。HETEs具有強力的腦血管收縮作用和促動脈粥樣硬化作用。而EETs具有擴血管、調節離子通道、抗動脈粥樣硬化等多種生物學功能,對心腦血管具有保護作用。近期臨床研究發現,AA的CYP代謝通路代謝產物(EETs和HETEs)水平與急性缺血性卒中后神經功能惡化密切相關[7,8],提示它們在腦缺血性損傷中可能發揮重要作用。可溶性環氧化物水解酶(sEH)是調控EETs的關鍵限速酶。外周血EETs降低不僅與缺血性卒中后神經功能惡化密切相關,還與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狹窄程度和斑塊不穩定密切相關,并受編碼sEH基因(epoxide hydrolase 2,EPHX2)的調控[8,9,10,11]。實驗研究也表明[12],EPHX2基因敲除可增加動脈中動脈阻塞模型大鼠腦血流量,減少梗死體積,對腦缺血具有保護作用,sEH被認為是缺血性卒中防治的新靶點。1-三氟甲氧基苯基-3(1-丙酰哌啶-4-基)脲[1-trifluoromethoxyphenyl-3-(1-propionyl-piperidin-4-yl)urea,TPPU]是2012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獸醫學院分子生物科學中心Bruce教授等合成的一種新型sEH抑制劑[13]。TPPU分子量為359.3,容易透過血腦屏障與中樞神經系統的sEH結合,抑制sEH活性。猴體內藥代動力學表明[14],與傳統sEH抑制劑相比TPPU表觀分布容積和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大,生物利用度高,半衰期長,每日1次即能夠維持有效血藥濃度,可逆、非競爭性抑制sEH電流,解離速度快,不會明顯蓄積而影響正常的神經突觸傳導,動物耐受性好。TPPU在多種動物模型中顯示其在抗炎和心、腎保護方面均優于傳統sEH抑制劑[13]。心臟動物模型研究也表明[15],TPPU可預防心肌梗死后心肌纖維化,具有抗凋亡、抗氧化、保護線粒體等多種功能。
2.2 sEH 抑制劑對腦缺血保護的研究歷程
針對sEH的神經保護是近年關注的熱點,雖然EPHX2基因敲除對實驗性腦缺血有保護作用,但EPHX2基因敲除要用于臨床預防和治療缺血性卒中還相當遙遠,因此sEH抑制劑研發倍受關注。2005年將sEH抑制劑12-(3-金剛烷-1-基脲基)-十二烷酸 [12-(3-adamantan-1-yl-ureido) dodecanoic acid,AUDA]應用在腦缺血神經保護實驗研究中,證實其對實驗性腦缺血有保護作用[17]。2007年又證實了另一種sEH抑制劑轉-4[4-(3-金剛烷-1-基脲基)-環己氧基]-苯甲酸[trans-4-[4-(3-adamantan-1-ylureido)-cyclohexyloxy]-bensoic acid, t-AUCB]能夠改善腦血流,對實驗性腦缺血有保護作用。AUDA和t-AUCB通過抗凋亡、抗氧化、抗炎、抑制[Ca2+]內流、線粒體保護、拮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介導的興奮毒性等多種機制發揮腦保護作用[18]。但這兩種傳統sEH抑制劑從胃腸道吸收差,生物利用度低,要達到有效血藥濃度所用的藥物劑量必須夠大,藥物易在體內蓄積,副作用較大,動物耐受性差,同時發現這些傳統的sEH抑制劑半衰期短,體內血藥濃度不穩定,這些原因導致傳統sEH抑制劑臨床轉化的失敗。
3 TPPU 對腦缺血保護的研究現狀
TPPU是2012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獸醫學院分子生物科學中心Bruce教授等合成的一種新型sEH抑制劑,分子量小,容易透過血腦屏障,與中樞神經系統的sEH結合,抑制sEH活性[16]。TPPU口服生物利用度高,半衰期長,動物耐受性好[19]。是一種非常有希望轉化到臨床上使用的新型神經保護劑。TPPU在多種炎癥動物模型中顯示其在抗炎和心、腎保護方面均優于傳統sEH抑制劑[13]。心臟動脈模型研究表明[15],TPPU可預防心肌梗死后心肌纖維化,通過抗凋亡、抗氧化、保護線粒體等多種功能發揮心肌保護作用。
4 總結
目前,TPPU對于腦缺血保護的具體機制尚未研究清楚,需更多的基礎研究進行證實。相關通路一旦研究透徹,相信會給腦卒中治療帶來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