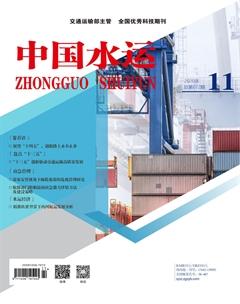郵輪旅游體驗研究
陳夏夏
摘 要:近年來,隨著郵輪產業在中國的持續發展,許多學者將目光投向郵輪旅游研究,以不同的思路、視角對郵輪展開了持續的思考與探究,留下大量學術成果。然而,相比西方,郵輪旅游作為國內一種新興的旅游體驗方式,人們對它的了解和研究還不夠深入與透徹。因此,本文通過文獻綜述的方式,類比一般大眾旅游,從認同視角進行研究,分析了郵輪體驗過程中的四種認同,即混合文化認同、場所認同、情感認同以及自我認同,并將郵輪旅游與傳統旅游的特點相對比,分析了郵輪旅游中認同的獨特之處。
關鍵詞:郵輪旅游;認同;體驗研究
中圖分類號:F592?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6—7973(2020)11-0023-03
郵輪旅游是用郵輪將一個或多個旅游目的地聯系起來的旅游行程。這種旅行方式始于18世紀末,興盛于20世紀60年代。從20世紀80年代起,郵輪旅游一直是全球旅游市場中增長最快、最具潛力的板塊,因此引起學界廣泛關注[1]。近年來,隨著郵輪產業在中國的興起,國內很多學者也開始展開對郵輪的研究,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新穎的研究視角、多樣的研究理論為基礎,展示了郵輪旅游的別樣趣味。同時,隨著郵輪產業的不斷發展,郵輪旅游與許多學科、概念都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以郵輪旅游為中心,游客體驗為載體,各種研究百花齊放,為郵輪旅游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基礎。
1 認同的涵義
不同的主體、視角、環境下,人們對認同的涵義和理解是不同的。《辭海》中對“認同”是這樣解釋的:認同在社會學中泛指個人與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們在交往過程中為他人的感情和經驗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經驗足以同化他人,彼此之間產生內心的默契[3]。《辭海》是從社會學方向對認同做出了定義,主要表述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勾稽關系。在《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中這樣定義“認同”:指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范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弗洛伊德最先使用這個概念。他認為凡是人們對他人的情況表示同情,或能體會他人的感情經驗,或待人如待己者,都可稱為認同。可見,弗洛伊德對認同的理解偏向心理學和人的情感方面,且范圍更加宏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無形中接觸到很多認同與被認同,小到個人的自我認同、身份認同、角色認同,企業的品牌認同、品質認同、價值認同,大到社會和國家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正是這些形式的認同,使得旅游者的心理保持一種正常的狀態,并生成各種愉悅。
2 文獻綜述
對于國內文獻,以“旅游”和“認同”為主題在中國知網進行搜索,搜到1225篇相關文獻(時間為2020年2月12日)。
國內針對旅游體驗過程中的認同研究相對較少,其中陳才提出的旅游認同概念模型,他認為:認同是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見現象,直接涉及人們對于“我是誰”或“我們是誰”、“我在哪里”或“我們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2]。陳才認為旅游認同如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一樣體現出一定的層次性,由下而上分別為:目的地認同、角色認同、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這種層次理論由外到內、由淺至深,最終歸咎于人類自身的自我認同,體現了一種人本主義的思想,也是反映出,旅游對人的影響最終是對旅游者自身靈魂的提升,情懷的熏陶。對于國內關于旅游與認同相關的文獻,盡管研究對象各不相同,比如古鎮、遺址、農家樂、少數民族景區等,學者們談到的相當多的還是文化認同。的確,當游客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領略不同的風土人情與宗教習俗,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體驗當地的風俗習慣,這種探知、理解、體驗的過程就是一種文化認同的過程。當然,在如今這個旅游業作為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力量的時代,旅游景區也在做出努力,為了迎合游客需要,傳統文化不斷包裝成游客需要的形式[5]。歷史文化旅游開發者對其細致挖掘,將歷史文化的深厚悠遠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給旅游者,讓旅游者的游覽行為不止局限于休閑與娛樂中,更多的是對能夠接觸與領略當地歷史文化的震撼與滿足,這就在無形中為旅游者與目的地的歷史文化直接構建了一條緊密聯結的溝通橋梁,這座橋梁便是旅游者的一份文化歸屬與自信之感[6]。
3 郵輪旅游中的認同
3.1混合文化認同
伴隨著旅游產品的多樣化及旅游行為的異質化,旅游進入了多元化發展階段,呈現出品項紛繁的態勢[7]。而郵輪旅游作為近幾十年才在中國興起的一種旅游方式,既包含著一般旅游的特征,又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人們的視線。對于郵輪旅游的文化認同,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十八世紀末的歐洲,從以交通運輸為主要目的,逐步發展為有著豪華裝潢、精致服務的旅游方式。在人們眼中,郵輪旅游成為了財富的彰顯、身份的象征。盡管郵輪在中國發展或多或少融入著中國元素,但不管是郵輪的外部造型、內部構造、活動服務或是娛樂設施都留有歐洲郵輪的影子,這些影子吸引著游客去探訪、去感受、去了解郵輪歷史的演變、郵輪文化的傳承。相對的,對于郵輪為迎合更多中國人的口味,進行的本土化發展,何嘗不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認同。對于中國文化而言,它的形成和演變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經過文化演變、融合形成了多種文化要素有機結合的文化整體[9]。而郵輪本土化,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文化差異,更好地將西方文化融入東方文明,從而使郵輪適應中國游客的口味。不同于一般的旅游體驗,文化的融合與多元共存,促進著傳統與現代的創造性結合,在郵輪旅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種混合多元化的體驗,給游客帶來了新奇、刺激、愉悅與無限遐想。
3.2 場所認同
郵輪旅游是一種郵輪與目的地結合的旅游方式,游客對場所從陌生到熟悉,從拘謹到從容自得。不得不說,郵輪旅游的場所是如此的特別,它連接海洋和陸地,室內和戶外,具有全方位和整體性,將視覺、聽覺、觸覺等完美的結合。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人種的人們在這里匯合,共同完成了這一場郵輪體驗。
旅游者對目的地的認同主要受到目的地意象、旅游動機與旅游經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在啟程之前,游客對目的地大多持有美好的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目的地認同的基礎[2]。事實上,在出發以前,游客已經懷揣著對郵輪的向往之情,并通過書籍、廣告、網頁或是口耳相傳等方式,了解關于郵輪的信息資料,進而在心中抱有期待和想象,這種期待與想象構成最初的場所認同。“奢華享受”“浪漫之旅”“休閑觀光”“經典海岸”“體驗之選”等是郵輪廣告的關鍵詞,也涵蓋了郵輪體驗的特征,這些特征以郵輪為載體,使游客從虛幻到現實,從想象到真正獲得體驗,加深了對場所的認同。此外,每個旅游地都有其獨特的地域文化、代表其文化的事物, 突出表現這些事物是重要的[10]。而郵輪旅游正是強化了其旅游方式的獨特性,游客參與郵輪旅游時,會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體驗,與以往的旅游相似度和重合度很低,因此游客會更加認同郵輪旅游的真實性。
3.3情感認同
體驗不是對客觀世界的映照和機械的反應模式, 而是富于多樣性、動態性和變化性的[11]。郵輪體驗更是如此。從微觀層面來看,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感的存在與個體的人的存在密切相關,一個人的情感結構決定了一個人的存在范疇;而從宏觀層面來看,情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情感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更是人類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生成的承擔者。相較于開闊露天的旅游地,郵輪旅游這種室內的旅游方式,將游客們聯系得更為緊密,而船上參與性、互動性的活動較多,又將游客與船上工作人員聯系起來。因此,游客在郵輪觀光的過程中,處于同一密閉空間中的游客,喜怒哀樂更容易被周圍的人、事、物影響,較日常生活也會有更多的情感變化。
英國心理學者沃爾特·米契爾(Walter Mischel)提出認知情感系統理論,一個物質上的認知可以使人的情感系統發生交互作用,并構成人格心理中的核心元素,從而決定人類的行為[12]。而郵輪旅游的生理體驗,最終都要歸于心理體驗和情感體驗,人們與冷血無情的動物的區別在于,人們會思考,有快樂悲傷,有七情六欲,人們的感受有時強烈,有時又是如此微妙。看到精彩的表演時人們會拍手鼓掌、大聲叫好,觀賞著海上壯闊的美景時會激動欣喜,遭遇插隊等糟心事時又會心生怒意等等,都是情感認同最直觀的體現。旅游情感體驗是旅游者對情感的體驗, 體驗是自己的, 所體驗的情感卻可以是他人的[13]。情感認同并不是轉瞬即逝,而是深深烙印在游客的記憶中,影響著游客對于整個郵輪旅游過程的評價。
3.4自我認同
現代認同的起點就是內在自我的起點,現代人必須處于自覺自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 而這種自主程度歸根到底需要獨立的私人性[14]。旅游本質上就是體驗, 即旅游體驗,而郵輪旅游, 包括分析郵輪游客的體驗世界和郵輪旅游體驗過程,正是游客認識自我的一種形式[15]。游客在整個旅游過程中,自我認同富于變化,和體驗效果、情感認同緊密聯系。 認同是一個過程,從認識到嘗試理解,再到感悟,最后才是認同。旅游活動為“自我”與“他者”的接觸提供了平臺,在時間、空間、歷史和文化的轉換中,體驗不同生活方式或生活環境,在與“他者”的對比和互動下,認同不斷被探索、建構和強化,認同危機得以擺脫[16]。有學者認為:與大眾旅游者相比, 背包旅游者具有較多個性鮮明的行為特征, 從而為自我認同的建構提供了現實保障[17]。的確,背包旅游相較于一般旅游更考驗人的意志與勇氣,當人們穿越重重阻礙到達最初的目標,會加深心中對自我的肯定。而對郵輪旅游來說,個性鮮明的體驗平臺區別“他者”和“自我”, 郵輪經營商精心開發航線、設計郵輪和選擇停靠港, 提供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 滿足游客個性化要求, 精心設計每一個環節, 注重體驗的整體氛圍和整體意境[15]。環境的烘托幫助游客更好地置身其中, 順暢體驗, 獲得滿意體驗,進而加深自我認同。
4 結論
有學者認為,旅游者從日常居住地來到另一個空間,從一種生活方式轉向另一種生活方式,所面對的不僅僅是適應環境變化的問題,而且潛意識中還面臨著“我是誰”的問題[2]。而在郵輪體驗中,通過所聽、所見、所聞、所感,游客們不斷強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在過程中感受到不僅是物質欲望的滿足,還有價值精神的升華,解釋了“我是誰”的問題。通過前期體驗的期待,旅途體驗的享受和后期體驗的回味,游客逐漸經歷混合文化認同、場所認同、情感認同最終歸于自身的自我認同,這一系列過程是流暢且一氣呵成的。當然,因個體對認同理解的差異,以及個體在郵輪旅途中具體經歷的不同,人們對整個旅游過程的體驗感知也是不同的。但正是因為如此,大家有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感知、不同的描述、不同的回味,才讓旅程不那么千篇一律,才讓書本、影視、照片的風景與真實的自我體驗如此不同,讓郵輪旅游更加具有吸引力,游客也更有探求的欲望,甚至流連忘返,正是在這種差異與不確定性給予旅程別樣的光彩,也讓個體的體驗成為自己獨一無二的身體與精神的財富。
參考文獻:
[1]陳詠梅,張夢娜.我國郵輪旅游市場推廣策略[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0(06):95-99.
[2]陳才,盧昌崇.認同:旅游體驗研究的新視角[J].旅游學刊,2011,26(03):37-42.
[3]夏征農.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1763.
[4]左冰.紅色旅游與政黨認同——基于井岡山景區的實證研究[J].旅游學刊,2014,29(09):60-72.
[5]郭文,王麗.文化遺產旅游地的空間生產與認同研究——以無錫惠山古鎮為例[J].地理科學,2015,35(06):708-716.
[6]常睿,段妍.大學生文化認同視角下歷史文化旅游核心價值塑造[J].社會科學家,2019(10):110-115.
[7]朱竑,楊夢琪.從旅游差異走向旅游認同(Tourist Identify)——中國旅游研究的本土化[J].旅游學刊,2019,34(10):4-6.
[8]尹新瑞.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工作賦權:文化相關性與本土化策略[J/OL].理論設:1-7[2020-02-20].https://doi.org/10.19810/j.issn.1007-4767.2020.01.016.
[9]余曉慧.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認同[J].西南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0,4(01):18-22.
[10]王佳俊,季佳鳳.文化創意旅游目的地地方認同探究——以田子坊為例[J].旅游縱覽(下半月),2018(10):69-72+77.
[11]樊友猛,謝彥君.“體驗”的內涵與旅游體驗屬性新探[J].旅游學刊,2017,32(11):16-25.
[12]于松梅,楊麗珠.米契爾認知情感的個性系統理論述評[J].心理科學進展,2003(02):197-201.
[13]鄒本濤.旅游情感體驗的內容分析[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32(09):21-27.
[14]查爾斯.泰勒,陶慶.現代認同:在自我中尋找人的本性[J].求是學刊,2005(05):13-20.
[15]蘭龍耀.郵輪旅游體驗分析[J].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13(03):77-78.
[16]趙志峰,李志偉.旅游研究中的認同話題——基于CiteSpaceⅢ的知識圖譜及可視化分析[J/OL].旅游論壇:1-6+12-14[2020-02-2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363.K.20191017.1533.004.html.
[17]余志遠,沈曉婉.背包旅游體驗中的自我認同建構研究[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35(1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