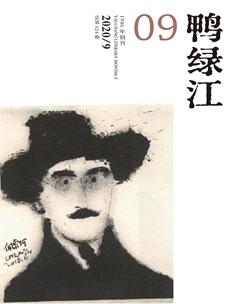現代小說與“故事新編”(對談)
陳培浩 王威廉 梁鼐
1
陳培浩:本期我們從梁鼐的小說《哈布特格與公牛角》談起。這個小說很有意思,特別是它跟余華《鮮血梅花》之間所構成的互文性關系。梁鼐的敘事語言非常老練圓熟,看得出你對余華的鐘情。不過,年輕作家在上輩作家的后面寫作都努力擺脫“影響的焦慮”,不愿讓人看出“影響”,希望另辟蹊徑、別開新境。所以,你這篇小說的構思和寫作背后有什么故事嗎?
梁鼐:很高興能與兩位老師對談,感謝《鴨綠江》給我這次機會。陳老師所言極是,我特別喜歡余華,深深地迷戀著他的敘述語言和敘事技巧。我讀過他所有的小說,有的不止一遍兩遍。《活著》的第一章我能完整地背下來。但是坦白地講,《鮮血梅花》不是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短篇,他的小說中短篇我喜歡《十八歲出門遠行》,長篇喜歡《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我的短篇小說《哈布特格與公牛角》與《鮮血梅花》形成了互文關系,是我沒有想到,也沒有意識到的,這正如我們忘記了吃過的每一頓飯是什么,但它給我們提供了營養,長成了我們的骨骼和肌肉。如果《哈布特格與公牛角》能夠具有文本之外的意義,與大師之作互文,幸莫大焉!
寫作《哈布特格與公牛角》是在今年三月初,正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時,我禁足在家,每天牽掛著武漢的疫情,時而欣喜,時而悲傷。那段時間,心緒不寧,讀我最喜歡的作家的書也讀不下去。我清晰地意識到我需要找一件事情做,穩住心神。我強迫自己坐在電腦前寫小說。這篇小說開始不是這個樣子,是另外一個樣子。開始,我寫作的題目是《遙遠的棉花地》,是月光下一片白花花的棉花地里兩個年輕人戀愛的故事,和這個《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一點兒關系也沒有。至于后來怎樣從一個小說跳到了另一個小說,我現在也說不太清了,可能是在構思《遙遠的棉花地》時,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念頭勾引著一個騎著黑色騾子尋找父親的青年闖進了我的腦海里。這個形象讓我激動不已,于是,我果斷舍棄了那個小說,重起爐灶,寫作《哈布特格與公牛角》。我絞盡腦汁寫下了第一句話:我是個收老物件的販子。第一句話定準了,小說的敘述腔調也就有了,剩下的只需要娓娓道來。
小說中的羅喜來是我喜歡的形象。我長久以來對喋喋不休、特別饒舌的人有興趣,比如莫言的短篇《木匠和狗》中的管大爺,電影《低俗小說》中塞繆爾·杰克遜扮演的黑社會殺手。我覺得這類人幽默詼諧,妙趣橫生,特別可愛。小說中羅喜來講了兩個故事,故事內容的設計并不難,難的是他為什么要講兩個故事。如果第一個故事不是真的,他為什么要編呢?這就需要人物行動的合理性,得符合邏輯。幾經修改,最后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是,他講第一個故事的原因是他希望“我”的父親能夠以那樣的方式繼續活在這個世上,而在得知“我”就是楊文生的兒子時,他講另一個故事,吐露實情,因為他已病入膏肓,需要把父親的遺骨交給我。
關于小說的結尾,我在寫作之初并沒有那么設計,沒想到用一個故事消解另一個故事,沒想到把真相弄得撲朔迷離。只想自己是一個釀酒師,清清爽爽地釀兩杯口味不同的酒,供客人品嘗。可是最后,我把兩杯口味不同的酒摻到了一起,成了雞尾酒。當“我”挖開父親的墳,除了看到父親的白骨外,我讓哈布特格也出現在那里。這個時候,小說就像有了生命,不受控制了,它自己走到了這里,走到了屬于它的終點。這可能就是小說創作中讓人迷醉的魅力。
我有四分之一的蒙古族血統,從小生活在漢地,這并不妨礙我對本民族文化和風俗的熱愛。小說中哈布特格譯成漢語是荷包的意思,是蒙古族青年女子贈給情人的禮物。我希望這篇小說也能成為我獻給讀者的禮物。它可能粗針大腳,樣貌丑陋,但里面包裹著我的一顆赤誠之心。
陳培浩:事實上,“影響的焦慮”和“故事新編”都是構造文學傳承的兩種方式,前者是以否認方式呈現的傳承,后者則是以接納的方式進行的重構。因此,不管是基于“影響的焦慮”對影響源的抹去,還是大大方方承認影響源的存在,后發敘事的價值和有效性全賴于創新。不管是“影響焦慮”還是“故事新編”,不能創造新質素的寫作就是平庸的寫作。如果讓你對比《哈布特格與公牛角》和《鮮血梅花》,你覺得《哈布特格與共牛角》有哪些新的創造呢?
梁鼐:其實“尋找父親”這個題材在小說領域并不鮮見,除了陳老師所說的《鮮血梅花》,還有國外比較著名的《佩德羅·巴勒莫》,當然還有很多,不在此一一贅述。最近重讀了《鮮血梅花》,即使是余華三十年前的作品,現在讀起來依然令人熱血沸騰。那種飄忽跳躍的語言,那種關于時間迷宮式的敘述,那種人性的深刻和宿命感,都給人一種天才乍現、天崩地裂的感覺。要說我的《哈布特格與公牛角》與《鮮血梅花》相比有什么創造性,單就某一點而言,也許《鮮血梅花》中的阮海闊最終知道了殺父仇人,而《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中的“我”對父親最終的死因或者最終的去向仍是一頭霧水,給讀者留下了巨大的留白。不知我說得是不是準確。
陳培浩:事實上,《哈布特格與公牛角》跟《鮮血梅花》的關聯性和差異性都是很明顯的。《鮮血梅花》是余華對武俠小說的“故事新編”,他用先鋒文學的語言和生命觀念給武俠小說經典的“替父復仇”敘事注入新質素。在傳統武俠小說中,“替父復仇”的故事已經累積成相當穩定的敘事模型,它傳遞的價值觀和文化邏輯既是“江湖的”,也是“傳統的”。這里面有善惡因果,有快意恩仇,有子承父業等因素。在一般的武俠小說中,不會出現惡人之子替父報仇殺了義人,這種敘事冒犯了“善惡果報”的倫理,會讓讀者不知所措。復仇敘事還隱含著一種非常前現代的邏輯,即子一代的人生毫無商量余地,必須去承擔父一代的使命,替父復仇被視為子一代不能拒絕的責任和義務。換句話說,“子”是沒有自己的,而只能在血緣和家族所規定的路線上行進。這種“前現代”的文化設定在五四新文學的視野中會顯得格格不入。五四文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就是子一代對父一代乃至整個家族的精神反抗。當然,替父復仇有某種越過煩瑣甚至不公的法制程序、倚仗自身力量自行裁決的快意恩仇意味,所以一直是受到民間閱讀追捧的。但替父復仇敘事一定是缺乏人文性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有一個譯名就叫《王子復仇記》,這個譯名是非常符合中國武俠傳統的,但它強調的是“王子復仇”這個層面,《哈姆雷特》這個譯名強調的則是哈姆雷特那種“to be or not to be”的精神沖突,兩者的精神層次是不一樣的。這可能是《哈姆雷特》這一譯名比《王子復仇記》更響的原因。說回到余華的《鮮血梅花》,這篇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1989年第3期。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武俠小說在中國大陸已經非常流行了。此時代表純文學界的余華以“戲仿”的方式重構了武俠小說,小說中那個奉母命為父復仇的兒子卻一再陰差陽錯地跟仇人錯過,他遇到殺父仇人時卻不知道他們就是仇人,等到他知道他們就是仇人時他們已經死于別人之手,他永遠失去了手刃仇人為父報仇的機會。所以80年代先鋒文學那種偶然性的哲學觀和生命觀就在武俠小說的復仇母題中替換了那種善惡因果和快意恩仇的因素,在當時是非常讓人耳目一新的。
王威廉:我對梁鼐的這個短篇特別感興趣。老實說,我在閱讀的過程中體會到了某種久違的閱讀的快感,那種快感是少年時代讀傳說故事時的興味盎然。在這篇小說中,一方面是先鋒小說的語言技法,一方面是某種民間傳說的調子,混雜在一起的時候,不乏某種喜劇的氣質。當然,故事的內核是悲劇,是尋找一個早已死亡的父親的敘事,但是風格所洋溢出來的快感具備了喜劇的氣質。這種模式倒是讓我想起了余華的《活著》,在《活著》開篇,恰恰也是一個“文化人”的角色去鄉下調研,然后讓富貴老漢自己開口說話,這種模式是意味深長的,這是一次“轉譯”。如果《活著》的開頭沒有這個文化館員的角色,而是直接讓富貴老漢開口敘事,這種敘事的風格會陷入到虛假的質疑當中。因為后邊的敘事暗示是經過加工轉述的,因此有相當的文學性。《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也是如此,讓知道父親去向的唯一老友開口講話,也具有一定的“轉譯”模式,從而將三個故事統一成了一篇小說。這三個故事便是主人公尋找父親的故事,以及老友講述父親去向的兩個故事,前一個故事是結構,后兩個故事是肉身,這三個故事彼此勾連乃至解構,才讓這篇小說在藝術上得以成立。
陳培浩:我再說說《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余華的《鮮血梅花》以“武俠”這種類型小說為接口,卻在語言和思想意蘊上解構了以往的武俠小說。但《哈布特格與公牛角》顯然沒有在“武俠”上做文章,它跟《鮮血梅花》的關聯在于將前者的“尋仇”轉換為“尋父”。《鮮血梅花》看似為父復仇,但小說以命運的偶然性解構了仇人的確定性,事實上也在解構“父”這個位置。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派,傳承了朦朧詩前輩的那種“弒父”情結,他們要在想象上砍斷過去與父輩的關聯,從而給自己創造一片無拘無束的天地。因此,余華對武俠小說的“故事新編”事實上是在武俠精神之外另開一桌,是現代文化立場與傳統文化立場的對話,是純文學與類型文學的對話。但梁鼐的《哈布特格與公牛角》就精神立場而言,依然是在余華《鮮血梅花》的精神延長線上:那種對確定性敘事的消解如出一轍。然而,二者還是體現出非常不同的文化精神:在余華那里,“父”和“父仇”其實是被敘事刻意流放的;而在《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中,主人公卻陷于欲“尋父”而不得的境地。在余華那個時代,他們迫不及待地想把“父親”所代表的權威位置搬開,所以他驅逐了確定性;但在梁鼐這里,卻暗含著一種對代表確定性、權威性的英雄之“父”的想象和向往只是敘事人陷于一種既向往又情知這不過是一種想象的尷尬境地。在這個意義上,《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也具有某種文化癥候意義。
王威廉:在《哈布特格與公牛角》中,主人公對父親其實也沒有抱著太大的情感,他是在母親臨終時,才發現母親居然還惦記著失蹤許久的父親。在此之前,他以為母親和他一樣,早都把父親放下了。他是接受了母親的臨終囑托才去尋找父親的,而不是主觀的意愿。這一點,在我看來很有意思,這個“尋父”是某種受制于感性情感的無奈任務,是帶有一定被迫性質的。這倒是與今天的語境暗合,曾經的尋根派是多么主動地走向山野大荒,去尋找文化精神的“父親”,但今天這種尋找也許只是出自于某種柔軟的囑托。在小說結尾,當“我”找到了父親的骸骨,挖出來的時候,“我被巨大的悲痛擊中了,眼淚刷刷淌下來。我聽到了自己無聲的哭泣。我現在才明白,原來我從來沒有忘記他,一直深深地愛著他,在心底最柔軟的地方裝著他。”這個時候,“我”與“父親”之間的情感聯系才得以重新建立。當然,如培浩所說,這里邊確實有著“父親”的浪漫化與英雄化想象,在關于父親的兩個故事里邊,前者是成全了一段美好愛情,后者是救了朋友的性命而犧牲了自己,據父親老友說,第二個故事是真的,但是在挖掘尸骨時,卻發現了來自于第一個故事的定情信物哈布特格,與其說這是在解構兩個故事,不如說,這是在更深的層次上讓兩個故事同時成立。
2
陳培浩:梁鼐,請談談你的寫作經歷好嗎?
梁鼐:從初中語文課堂上我的作文被老師當作范文朗讀那一刻起,我就立志當一名作家。我從小就喜歡讀書,那時鄉間書少,流傳最廣的是武俠小說,古龍、金庸、梁羽生、溫瑞安常常被我翻得飛邊卷頁。中學畢業,考上遼寧阜新的蒙古族師范學校以后,我經常去圖書館埋頭苦讀,在這期間我比較系統地讀了一些純文學書籍。我加入了學校的文學社,試著寫一些小小說,還到阜新籍著名作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享譽全國的謝有鄞家登門拜訪過。在校期間我就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小小說和散文。師范畢業以后,我回到原籍成了一名鄉村教師,在從教之余堅持讀書和寫作,買書和訂閱報刊成了我菲薄工資中很大一部分支出。2010年以前,我寫得比較雜,散文、小小說、詩歌都寫。2010年,我被朝陽市作協推薦到遼寧文學院中青年作家班學習,通過這次學習,我明確了方向,專攻中短篇小說的寫作。從那以后,我陸陸續續在一些期刊發了一些中短篇小說。我志大才疏,意志力也差,寫得不多。雖然從事文學創作的時間很長了,但還沒什么成績,還在學習中,在路上,繼續努力!
陳培浩:如果不按“70后”“80后”這樣的定義,我們大概屬于寬泛意義上的同代人。我們這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巨大影響。想請你談談你個人的先鋒文學閱讀史,也談談先鋒文學對你的影響。
梁鼐:確實是,我閱讀最瘋狂的時候正是先鋒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比較有代表性的先鋒小說如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余華的《世事如煙》《現實一種》,格非的《褐色鳥群》,殘雪的《山上的小屋》,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謎》,洪峰的《五色土》,等等,我都讀過。記憶深刻的一本書——《中國先鋒小說選》,陳曉明主編的,被我視若珍寶,里面就有洪鋒、格非等人的作品。先鋒文學給我提供了新鮮的閱讀體驗。
說有什么影響,先鋒文學那種詩意化的語言、新穎的結構、時間空間多重并進的講述方式、對故事的任意消解,可能或多或少對我的寫作產生過影響。如我剛才所說的,這種影響是不自知的,就像吃過飯變成營養供給我的身體。
先鋒文學是中國文學史進程中一個重要的節點,影響巨大,在今天的小說寫作中,仍然能看到一些作家在堅持先鋒文學寫作,比如李浩、陳鵬、陳集益等。只不過他們的先鋒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過去的先鋒文學更看重形式,只在意“怎么寫”,不在乎“寫什么”,而李浩等作家,將“怎么寫”與“寫什么”結合起來,讓內容和形式統一,甚至更看重內容,挖掘人性,關注人的命運。
陳培浩:你覺得“80后”這一代青年作家該如何從前輩的寫作中走出自己的審美路徑來呢?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梁鼐:嚴格意義上說,我還不算“80后”,我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但是在寫作上,我面臨著和“80后”一樣的問題,即怎樣寫出反映這個時代和社會的優秀作品,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在“60后”和“70初”為主導的當代中國文壇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覺得應該做到三點:一是學習,研讀經典的文學作品,磨煉自己的寫作技藝;二是要深入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到人間去體察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這樣筆下的人物才能接地氣,而不是執著于私人化和碎片化的書寫;三是要加強想象力,“80后”普遍沒有豐富的生活閱歷,這就要在作品中加強想象和虛構的能力。我們不可能每種生活都經歷,但可以靠想象去彌補。莫言在寫《紅高粱》之前,有人說他沒經歷過戰爭,不可能寫出關于戰爭的作品,但是莫言靠想象和間接得來的經驗寫成了《紅高粱》。以上三點,我愿與一些有志于小說創作的青年共勉。
陳培浩:中國作家以外,哪些外國作家構成了你的寫作資源呢?這里可能涉及你個人的外國文學閱讀史問題。
梁鼐:這個可以列出一大堆名字,像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福克納、卡夫卡、麥克尤恩、理查德·福特、巴別爾、卡佛、卡波特等等,這些作家的作品我多有涉獵,都或多或少的讀過。其中的《南方》《霍亂時期的愛情》《紀念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鄉村醫生》《立體幾何》《大瀑布城》、《鹽》《大象》《圣誕節憶舊》這些篇什是我的最愛,過一段時間就會讀一讀。
最近,我迷上了布魯諾·舒爾茨,這是一位天才而短命的作家。他的文字明凈而富有奇詭的想象力,讀完就像一場荒誕而又美妙的夢魘令人沉醉不已。《紐約客》評價他的語言中蘊涵了數學的精湛、古典的詩意和病態的抒情。我特別喜歡他的短篇小說《鳥》。
陳培浩:我們這個欄目叫“新青年·新城市”,請你談談你對“青年寫作”,或者是寫作的“青年性”以及“城市文學”這兩個話題的看法好嗎?
梁鼐:“青年寫作”已是當下文學生態的熱鬧景觀,很多重要的文學期刊都對“文學新生力量”表現了極大的關切,都在推出新人。像《鴨綠江》《作品》《青年文學》《花城》,文學的接力棒最終要交到青年人的手上。但是,青年寫作短時間內達到一定的高度還不現實,需要時間的積累,自身的磨礪,還需要老作家的“扶上馬,送一程”。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深入,“城市文學”會是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文學的發展主流。相較于“鄉土文學”,“城市文學”我認為還是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城市的意象、城市的萬花筒般的生活、城市百年未有的驚心變化和對于蕓蕓眾生的再塑造、城市人肉身和靈魂的悖謬,都是很好的書寫內容。
3
陳培浩:梁鼐的《哈布特格與公牛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故事新編”的話題,上面已經提及,這里不妨再繼續說說。魯迅對很多古代神話故事的重新敘述就結集為《故事新編》,故事新編的落腳點一定不是在新故事上,而是在新故事背后新的文化立場上。《故事新編》就是魯迅站在現代思想立場上,通過現代小說對古代神話的重敘,對歷史人物進行再評價。其中滲透著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對話和碰撞。除魯迅外,還有很多著名的“故事新編”。比如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就是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的“故事新編”。受到卡爾維諾的影響,王小波也對唐傳奇進行“故事新編”,像早期的《唐人故事集》和后來的《紅拂夜奔》《萬壽寺》都有著唐傳奇的人物原型。但王小波那種追求敘事的無限性,不斷推倒重來的敘事沖動,跟唐傳奇當然相去千里,它是王小波受后現代敘事方法和精神影響的結果。還有一種“故事新編”是作者自我生長過程中的“故事新編”,通過“故事新編”實現的并非文化精神的重構,而是寫作的自我完善。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麥家,麥家總是不斷改編或重敘自己以往的故事而生成新的作品。比如出版于2002年的《解密》,后來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提名,是麥家最早備受矚目的長篇小說。但《解密》是由之前的中篇小說《陳華南筆記本》長成的,《陳華南筆記本》之前又是生長于一部叫《紫密黑密》的短篇小說。通過不斷重寫以往的故事,使故事從一顆種子長成一棵小樹再長成蒼天大樹,這是另一種自我寫作譜系中的“故事新編”。
王威廉:應該是有兩種“故事新編”,一種是把過去的故事以現代小說的風格進行重新敘述,一種是以現代小說的風格去虛構一個過去的故事。前者更為常見,如你所舉例的那些,都是特別有意思的“再敘事”。我記得作家李馮一度以這種“故事新編”作為自己的主要創作方向,在大眾層面來說,李馮編劇、張藝謀導演的《英雄》便是這方面的當代代表作;后者實際上難度更大,在我的印象中,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哈扎爾辭典》。米洛拉德·帕維奇是塞爾維亞作家,他在小說《哈扎爾辭典》中將虛構能力發揮到了更高的地步,故事的明線就是圍繞著哈扎爾人的改宗進行,小說家把已知的哈扎爾史料編入故事中,又由此展開想象并虛構出新的故事,包括虛構的歷史、風俗和文獻。但好玩之處也是關鍵之處在于,歷史上確實有哈扎爾這個國家,它還是一度橫跨亞歐大陸的強國。這個民族在唐朝時期的突厥帝國崩潰后出現,衰落是在公元10世紀,也就是宋朝時期。這種逆向進行的“故事新編”,給人的觸動往往更加巨大,因為它所需要的歷史前提是非常少的。比如我們的許多故事新編,中國人會讀得津津有味,但對于中國文化以外的讀者來說,恐怕這種新編還要考慮到對歷史前提的交代,不然沒法上升到文學藝術的無礙境界。
陳培浩:事實上,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故事新編”就是每一代歷史必然的敘事沖動。如果一部小說的故事新編能跟文化史所進行的“故事新編”相遇,這部作品就獲得了浮出歷史地表的地緣。我曾說過,一部作品如果幸運的話,會遇到屬于它的時刻;如果足夠幸運的話,則會遇到屬于它的時代。不少作品雖擁有屬于它的高光時刻,但這個時刻卻是一整個時代的零余物,因此注定要在時代中堙滅。但有的作品,剛出場就遭遇了正在重構的歷史敘事,并且被選取作為這種敘事的典型節點甚至界碑,由此而享香火不盡。這里有歷史很無情的部分,它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由文學性本身決定的。20世紀80年代那一批先鋒作家某種意義上說實在太幸運了,他們一出場就碰到了文學史正在搞“故事新編”,他們當然就成了急先鋒上場,文學史給他們打造了一個非常新鮮的位置,這套文學史敘事至今仍在很大范圍中沿用,他們也就一直在這個經典位置上固若磐石。
王威廉:這也是提醒我們,“故事新編”的“新”并非任意之新,而是時代之新。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先鋒小說”與其當時所處的歷史重新敘事的時機肯定是分不開的。借助先鋒小說,歷史之舌重新有了滔滔不絕的饒舌欲望。歷史也必須記錄下這個時刻所說出的話語,盡管這種話語有可能因為時過境遷而重新失去了表達的欲望。小說敘事與歷史表達欲望之間的深層關聯,值得我們反復深入探究。我對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記憶猶新,在這里我想簡單聊聊這個小說。《生死疲勞》以佛教的“六道輪回”之說為結構,主人公在畜生道里的五次輪回對應于中國這五十年多來的當代史。“莫言”直接出現在小說文本中,莫言和藍解放一同講述三代人的家族史。《生死疲勞》的結尾具有強烈的象征色彩,主人公轉世成了一個擁有超強記憶力與語言能力的大頭嬰兒,一方面要繼續修正歷史,一方面又坦言只是為了滿足讀者的愿望,是莫言為故事續上的一個尾巴。《生死疲勞》充分展現了小說家的個人記憶在小說敘事當中參與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的快感,但同時,歷史記憶在這種個人記憶的復原中的確獲得了照亮,小說家之“我”的記憶和文化之“我們”的記憶扭結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歷史記憶上的瘢痕。
陳培浩:回到作家個體寫作上的“故事新編”,下面的提問或許不是多余的:什么是有效的“故事新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故事新編”?上面也有所提及,創造才是小說唯一的道德,不管故事素材是新的舊的,如果敘述沒有新意,如果文化立場沒有新創,這便是無效的重復,而不是有趣的新編。很多當代的影視劇的“新編”其實是“炒冷飯”,是對一個具有市場號召力的題材反復的無效開采。當然,我是從文學創造的角度來評價。影視劇其實很多時候是作為文創產品來運作,追求的不是精神和藝術的創造性,而是市場效益的最大化。借“故事新編”這個話題,我很想說:我們必須警惕文學寫作思維的文創化。
王威廉:今天的文學處境自然是艱難的,但我還是相信藝術的創造力有時會超越“時代之新”,而進入到“永恒之新”,那是非常難的。像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已經是經典了。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故事新編”涉及的是歷史再現的問題。后現代理論和賽博文化的出現,讓再現問題總是卷入更加復雜的闡述。比如在德里達那里,再現可被視為克服符號學的邊界而進行意義生產的過程;而在福柯那里,再現的話語要受到權力的改造,面臨著主體的多重闡述;在波德里亞那里,關于真實的思考跟賽博文化的聯系更加緊密。他以地域和地圖為例,傳統上是先有地域,然后地圖模仿地域;而在今天先有地圖(圖紙),地域模仿地圖(圖紙)出現了。這一點在賽博空間里更為明顯,比如網絡游戲空間的建構性。也就是說,“再現”不再讓世界只有“真實”和“虛假”兩種可能性,“再現”本身成為第三種世界形態。“真實”可以不斷被模仿出來,“虛假”可以被不斷設計出來,“再現”不再依賴真實和現實得到闡釋,“再現”本身具備了相對的獨立性。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寫作的人,如果還不能深入理解再現對于存在和世界意味著什么,其寫作則會與當代文化失去本質性的聯系。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歷史再現對于寫作主體的思想能力和敘事技藝有著非常高的要求。當代中文小說的創作中,可以看到一些中短篇小說抵達了相當的思想深度;但由于中短篇的篇幅所限,寫作與我們時代的豐富關系注定要由長篇小說來承擔。莫言、余華、韓少功、格非、蘇童……這些優秀的作家都有著跟時代具有緊密關系的長篇小說,他們甚至引領過時代的文化風潮。他們是幸運的,他們作為作家是“文革”后一個文化爆發時期的代表,但對于很多作家來說,因為個人創作的歷程稍晚,或是因為別的原因,他們沒能成為那樣的“代表”,但這并不能否定他們所取得的文學成就。特別是不能成為“代表”反而會讓寫作具有一種更加個人化的氣質,這種氣質在當代文化共識越來越稀薄的情勢下會更加顯示出藝術探索的珍貴性。
【責任編輯】 ?陳昌平
作者簡介:
陳培浩,副教授,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特支人才計劃青年文化英才,廣東省優秀青年教師,廣東省文學院簽約作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廣東省作協簽約評論家。已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文學史料》《文藝理論與批評》《南方文壇》《當代文壇》《文藝爭鳴》 《中國文學研究》《中國作家》《作家》《文藝報》《江漢學術》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幾十篇。論文多次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已出版《迷舟擺渡》《阮章競評傳》《互文與魔鏡》《歌謠與中國新詩——以1940年代“新詩歌謠化”傾向為中心》《嶺東的敘事與抒情》等著作。曾獲《當代作家評論》年度優秀論文獎、首屆廣東青年文學獎文學評論獎等獎項。
王威廉,先后就讀于中山大學物理系、人類學系、中文系,文學博士。著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生活課》《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譯為英、韓、日、俄等文字。現任職于廣東省作家協會,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導師。曾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廣東魯迅文藝獎等。
梁鼐,男,蒙古族,原名梁廣龍,生于1977年冬天,遼寧朝陽人,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2010年入遼寧文學院青年作家研討班學習。在《民族文學》《長城》《雨花》《山東文學》《滿族文學》《青春》等雜志發表小說多篇。有部分作品被《小說選刊》選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