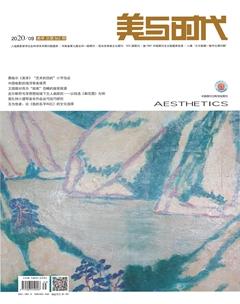中國電影的海洋審美境界
李會君 雷禮錫
摘? 要:1920年代以來我國電影的敘事空間從陸上城市、鄉村和山水拓展到了海洋,這種以表現濱海村鎮、海港、島礁、海上生產、生活、戰爭為題材的電影也拓展了藝術的審美空間,表達了海陸相依、人海共生、海洋家園等中國海洋電影自身獨有的審美意識。
關鍵詞:海洋電影;海洋美學;家園意識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2019年度人文社科項目“百年中國電影的海洋敘事與國家形象建構”(19Y101)階段性研究成果。
將海洋作為敘事對象,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古籍《山海經》就被視為用南方視野統轄山河江湖與海洋的敘事文本,是小說領域開展海洋敘事的源頭[1]。但是,19世紀以前我國文藝作品的自然欣賞與敘事,主要針對陸地山水,較少海洋景觀,如張晶所論,山水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文藝創作題材,已經成為主要審美對象,山水審美成為主要審美意識[2]。興起于20世紀的中國電影,激發了海洋敘事的持久熱情。1921年但杜宇執導的《海誓》,“以大海的波濤象征情海的不平,并力圖融畫入影,呈現海景之‘美”[3],是較早涉及海洋景觀的中國電影。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一批海洋題材電影,如《中國海的怒潮》《漁光曲》和《黃海大盜》,開啟了中國海洋敘事電影的發展歷程。此后,中國海洋敘事電影廣泛表現濱海(城市或鄉村)、海港、海灘、海岸、海濱、島礁等沿海區域的場景,形成了以沿海自然與人文景觀為基礎的海洋敘事電影體系。在21世紀,由于經濟、文化的全球化進程,中國電影在深海、近海、遠海等領域拓寬了海洋敘事的深度和廣度,成為電影產業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如2016年周星馳執導的海洋環保科幻片《美人魚》收獲票房33.92億元人民幣,2017年吳京執導的遠洋軍事動作片《戰狼Ⅱ》收獲票房56.8億元人民幣,先后開創中國電影史上30億級和50億級票房記錄。由此,涉及海洋敘事的中國電影備受關注,不僅被視為中國海洋美學的最重要內容之一[4],而且被視為海洋電影類型獨立發展的基礎[5]。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涉及海洋敘事的中國電影也是培育海洋審美境界、開拓自然與環境審美境界的重要媒介。
一、陸海相依
19世紀以前,我國以陸地山水為內核的審美興趣,不僅培育了歷史悠久的山水藝術傳統,形成了以山水詩、山水畫、山水園林為主的山水藝術體系,而且培育了歷史悠久的山水美學傳統,形成了崇尚道德比附的儒家山水美學、崇尚身體逍遙的道家山水美學、崇尚心靈冥游的佛教山水美學,由此確立了獨特的山水審美境界[6]。20世紀以來,隨著海洋電影的發展,傳統山水審美得到時空的延伸、精神的拓展,形成了陸海相依的自然與環境審美境界。
作為中國海洋敘事電影的先鋒,1934年蔡楚生編導的電影《漁光曲》,曾在浙江沿海漁鎮、漁港、海島如石浦、沈家門、普陀山等地取景[7],以便通過陸海相連的沿海景觀再現漁村生活面貌。在電影中,沿海景觀強化了敘事藝術的現實主義風格。如電影開頭用一個長達23秒由右向左的移動鏡頭,呈現沿海開闊的海面、眾多的漁船,再切入徐福的左手抓住一只木桶破冰取水的特寫鏡頭,然后畫面轉入一間殘破、簡陋、灰暗的民房。這里的沿海景觀消除了早期中國電影流行舞臺化表演必然形成的虛擬性,凸顯了漁民徐福一家的真實生存面貌,為電影展開敘述徐福一家三代遭遇各種悲慘生活場景,提供了現實的環境鋪墊。同時,沿海景觀也是電影敘事結構與節奏轉換的媒介。如徐福的母親病逝后,電影使用了一個沿海景觀段落,先是海水沖刷巖石的特寫鏡頭,再切入開闊的海面和沙灘,海的對面有連綿起伏的山巒,近處沙灘有筆直的椰樹;海面上有兩只小漁船,一只小船正揚帆行駛在遠處的海面,另一只無帆小船停靠在海灘,有兩個人正在船邊進行捕撈作業。畫面由此漸漸拉近,切入一個特寫鏡頭,表現兩個少年正在從事捕撈作業,他們正是已經長大的徐家孿生兄妹。由于景觀遠近、空間大小變化流暢,電影敘事顯得結構清晰,節奏自然。另外,《漁光曲》還使用意象化的海洋,表達人物與電影的精神意蘊。例如,徐福看到妻子生下一對孿生子女,臉上沒有一絲喜悅,反而為全家人即將面臨更加艱辛難熬的日子,顯露出無盡憂愁,表示“要是真的沒有法子好想,我只好到海上拼命去!”在這里,海洋成了人物精神沖突與命運不濟的象征。再比如,徐福的女兒在電影中多次吟唱同名主題曲,用反映漁民生活與勞動景象的歌曲,呼應曲折的情節,渲染凄婉的格調,并為悲慘的現實生活注入希望的底色,顯露電影的悲劇意味。
20世紀50年代后,伴隨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海洋敘事電影開始廣泛觸及領海范圍內的遠處與深處,島礁與深海景象被大量應用,其精神意蘊出現質的變化。如1955年王濱和湯曉丹執導的《怒海輕騎》,1959年尹一青執導的《海上神鷹》、嚴寄洲執導的《海鷹》、張錚執導的《海島之子》,都是敘述軍民聯手完成海上反特殲敵任務。其中,《怒海輕騎》主要講述海軍某基地第三炮艇大隊大隊長李龍江奉命率部偵察盤踞臥魚山島的敵方火力配備情況,在當地漁民熱情幫助和積極配合下,李龍江部成功完成敵情偵察,保障了陸海空三軍協同解放臥魚山島的戰斗任務。《海上神鷹》主要講述解放軍某部劉排長奉命率隊越海深入敵占島嶼進行偵察,最終在漁民幫助下,將活捉的俘虜押回,掌握了重要敵情,保障大部隊勝利解放了敵占島嶼。這些影片注重表現特殊的海洋地理與環境面貌,展現軍民團結、爭取勝利的革命情懷。如《怒海輕騎》以軍艦行駛在遼闊海面為背景推出片名,直觀點題,而影片開頭直接呈現洶涌的海浪沖刷島礁,拍打軍艦,氣勢撼人,暗示了海軍勇于迎接嚴峻挑戰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隨著海洋敘事電影的發展,海陸相連的海洋景觀在敘事藝術上日益增強。在1975年劉欣執導的海洋題材故事片《小螺號》中,開頭以開闊、明朗的萬里晴空為背景推出片名“小螺號”,然后鏡頭慢慢下移,并逐一顯示相關制作人員名單,之后的鏡頭自然地落在浩瀚的天空與遼遠的海面,呈現海天一體的壯闊景象,再切入海邊的萬頃波濤,并右移到淺灘,切入濃密的椰林;椰林中傳出了螺號聲,聽到螺號聲的少先隊員們奔出學校,跑向攀爬在椰樹上吹螺號的海龍,從海龍的口中得知,島上的石油鉆探隊正在樹立井架,要趕去看看。這里的敘事邏輯較為嚴謹、流暢,背景音樂顯得活潑、輕快,襯托了少先隊員們的新奇、期待。整個電影運用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海洋景觀,講述一群少年受海島石油鉆探活動的吸引,課后跑去參觀井架樹立的壯觀場景,然后熱心幫助鉆探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從中學到了石油鉆探的一些知識,懂得了鉆探工作面臨的自然風險與敵特威脅,領悟了鉆探隊員艱苦創業、勇于拼搏、無私奉獻的精神,開始組織訓練,站崗放哨,幫助鉆探隊挫敗敵特破壞活動,展現了建設新中國的自覺與豪情。
在中國電影的海洋敘事中,海陸相連的海洋景觀占據主流位置,可以說是國家疆域內的自然審美經驗從陸地向海洋的延伸。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1975年的電影《小螺號》,它以少先隊員視角敘述石油鉆探經驗的來源,包括李隊長曾經在內陸高原、沙漠地區從事鉆探的事跡,以及石油工人楷模王進喜在大慶油田的事跡。這表明,海上石油鉆探是陸地經驗向海洋世界的開拓應用,海洋經驗的根基來自陸地經驗。即使21世紀的海洋電影,陸地仍然被廣泛當作海洋經驗的支點。如2008年馮小寧執導的《超強臺風》,在表現海洋景觀時,頻繁使用陸地上連綿起伏的山巒作為背景,顯示海洋與陸地的緊密聯系。2016年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對海洋景觀的體驗與認知,主要源于陸地房產開發利益的驅動,本質還是由內向外、從陸地向海洋的延伸。
二、人海共生
在中國的海洋敘事電影中,陸地山川與海洋世界的聯系,不只是表現為地理環境上的陸海相連,更重要的是,海洋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領域,是實現人類與海洋和諧共生的重要保障。
20世紀以來,許多海洋敘事電影通過描繪普通英雄人物及其群體在海洋領域的作為,展現中國人面向海洋世界的生存與發展愿景。1962年王冰執導的《碧海丹心》講述解放軍某部連長肖汀所部,得到漁民的理解和支持,渡海擊潰敵艦隊,保障了大部隊登島作戰、解放海南。1962年林農執導的《甲午風云》,講述鄧世昌在水兵和平民支持下,英勇抗擊日本海軍侵略者。1975年錢江、陳懷皚和王好為執導的《海霞》講述海霞得到解放軍的關心和培養,組織海島民兵,配合解放軍粉碎敵特勢力侵擾海島的陰謀。1976年李俊和郝光執導的《南海長城》講述區英才帶領民兵,得到海軍支持與漁民配合,粉碎了國民黨敵特團伙企圖在南海登陸搞破壞的陰謀。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將海洋敘事電影中的英雄人物簡單地等同于一般敘事電影中的英雄人物。誠然,從政治與意識形態角度看,中國電影的英雄書寫經歷了從最初凸顯“高大全”神性特征的“完美型”英雄形象,到后來還原生活真實與人性本真的“缺陷型”英雄形象,再到回避英雄敘事甚至假借“袪魅”之風消解英雄的“非英雄化”傾向,及至2014年后出現了重新書寫英雄形象的“返英雄化”趨勢,試圖改變對英雄形象的過度消費與娛樂化,塑造有真誠信仰、公正、高貴的英雄形象[8]。但是,海洋題材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大多或顯或隱地涉及海洋科學知識與技術,不同于以身體能力為基礎的陸地英雄。對此,2009年趙浚凱執導的48集電視連續劇《滄海》有明確揭示,它講述三大解放戰役告捷之后,所向無敵的野戰軍某部獨立師紅六團奉命跨海登陸作戰,因缺乏基本的海戰經驗,九千多名將士全部壯烈犧牲,三營營長王本利因病未能參戰而僥幸存活,后改名王山魁,并在抗美援朝勝利后加入海軍,研究海洋知識,探索海戰方法,為建設強大海軍付出了智慧與辛勞。2008年馮小寧執導的電影《超強臺風》,顯示了類似的真理,人類要想面向海洋世界求生存謀發展,必須掌握海洋科學知識與技術。2018年林超賢執導的《紅海行動》,對中國軍人執行海上任務所必需的高精尖技術與知識有所展示,表明海洋英雄作為海洋生存與發展的保護神,是知識與技術的化身。
將海洋視為發展國民經濟、創造美好生活的契機,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電影的一個主題。1978年趙煥章、胡誠毅執導的《風浪》,講述造船公司為優先制造現代化的新漁輪或革命化的加工船(軍事指揮船),展開了不同勢力的較量,暗示海洋領域的經濟發展面臨嚴峻考驗。1978年李漢軍執導的紀錄片《潛海姑娘》,表現潛海姑娘們在海南島發展水產養殖業的生動場景,傳遞了海洋領域實現民富國強理想的新氣象。1984年滕文驥執導的《海灘》,講述一個以傳統插網打魚為生的濱海漁村,其十里海灘被征用九里,用于建設衛星城、新工廠,導致漁業蕭條,又遭遇新舊觀念、城鄉差異的沖擊和洗禮,上演了各種人物的不同命運,反映了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間存在的巨大沖突,表現了置身于傳統文明與封閉社會的人們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面臨的陣痛。
在人海關系主題上,中國電影還切入了物質利益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深層視角。如2016年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講述劉軒代表的人類地產開發計劃破壞了海洋生態環境,威脅美人魚的生存,使得美人魚族派遣珊珊前往阻止人類的填海計劃,而珊珊與劉軒在較量的過程中互生情愫,最終劉軒停止了填海項目,把自己的錢全部捐給了環保機構,表現了人類與海洋和諧共生的艱難而必然的選擇。
在人海和諧共生的主題上,中國海洋敘事電影并沒有局限于單純的中國利益,而是顯示了海洋文明背景下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感。例如,2017年上映的《海鷹戰警》,講述在巴拿馬注冊的洪都拉斯貨輪“海的主人號”,途經安達曼海域,被海盜劫持,因發動機故障停靠中國防城港進行維修,卻申請空倉,引起中國方面注意,后經公安部批準,成立代號“海鷹”的專案組,對“海的主人號”實施暫扣,對船員進行隔離審查,由此展開了跨國偵查犯罪分子的生死較量,展現了國際合作與發展領域的中國擔當。在2017年上映的《戰狼Ⅱ》中,中國軍人在海外執行拯救華僑撤離戰亂地區的任務時,還幫助外籍難民一同撤離,體現了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使命的自覺意識。
三、海洋家園
19世紀以前的中國山水藝術廣泛地表現了面向內陸世界的山水家園意識,如晉代陶淵明、唐代孟浩然等人通過山水詩表達濃郁的鄉土家園情結;晉宋之際宗炳、北宋郭熙等人通過山水畫論闡述明確的安居樂居理想。可以說,傳統山水藝術熱衷于描繪以山水為核心的自然景象,體現一種扎根于家國理想與信念的環境審美意識[9],這使得山水成了傳統家園意識的美學符號。20世紀以來,由于海洋敘事電影的發展,面向開放世界的海洋家園意識得以萌生。
縱觀20世紀中國電影的海洋敘事,有一個基本主題,那就是軍民團結、保家衛國,顯示了陸海相連、家國一體的家園感。1962年王冰執導的《碧海丹心》,講述解放軍某部連長肖汀率部追擊南逃敵軍,先行抵達海岸邊,發現當地所有船只已被敵軍炸毀,因籌劃船只的緊急命令在身,便強行征用他無意中發現的幾艘漁船,受到司令員的嚴厲批評,隨后展開了深入細致的幫扶工作,最終獲得漁民的理解和支持,并在漁民的幫助下進行海上練兵,掌握渡海經驗,取得了渡海擊潰敵艦隊的戰斗勝利,為大部隊登島作戰、解放海南創造了條件。1962年林農執導的《甲午風云》,講述1894年鄧世昌反對向日本侵略者求和偷安,在水兵和平民的支持下,指揮艦隊英勇抗擊日本海軍,終因彈藥不足,以身殉國,體現了國家與個人命運的強烈悲劇感,警示國人“落后就要挨打”。20世紀70年代,軍民團結捍衛領海主權的集體意志,在中國電影領域得到廣泛表現。如1975年錢江、陳懷皚和王好為執導的《海霞》,1976年景慕逵和張勇手執導的《南海風云》、李俊和郝光執導的《南海長城》,1977年張辛實和薛彥東執導的《風云島》、張景隆執導的《漁島怒潮》。這些電影無不體現了全民團結、保家衛國的精神宗旨。
歷史地看,中國海洋敘事電影在表現軍民團結、保家衛國的精神意蘊時,普遍存在一種反躬向內的家國意識。對此,涉及近代中國革命歷史題材翻拍的電影提供了典型案例。圍繞近代史上林則徐主持的虎門銷煙,1959年鄭君里和岑范執導的電影《林則徐》,凸顯了歷史與人物的悲劇性。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雖然來自海外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但電影側重表現近代中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狀況,使得林則徐和琦善成為鮮明的對立兩派。1997年謝晉執導的《鴉片戰爭》,再次重現海洋通道帶給近代中國命運轉折的禁煙事件,無論中國軍民英勇抗擊英國海軍侵略者的慘烈與悲壯海戰場面,還是持不同政見的林則徐與琦善后來在海邊互相道別并反省自我與國家命運的場景,無不顯露了近代中國政治與軍事在海洋文明面前的極端保守與脆弱。相比《林則徐》,《鴉片戰爭》加深了歷史與人文反思意識,但是,這種反思并未跳出相對封閉的傳統家國概念,導致對民族與國家命運的敘述未能獲得開放性的文化視野更新,容易凸顯家國命運的悲劇性,卻弱化家國精神的前瞻性。
開放的世界文明視野在21世紀中國海洋敘事電影中得到了清晰的表達。例如,2008年肖鋒執導的《海之夢》,講述濱海城市為申辦奧運會帆船比賽,不同職業和經歷的人們都參與進來,對人生、城市與海洋有了新的認識、期待,尤其普通民眾身上相對封閉的認知方式,受海外文化信息與經驗的影響,日漸開放,顯示了逐步融入開放世界與全球化進程帶來的精神變化。2012年,馮小寧編導的《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通過重新翻拍甲午海戰題材,嵌入海洋文明視角,反省中西文化差異,喚起對近代悲劇歷史的開放性反思,蘊含了由遠及近、由外向內的海洋文化認知與實踐,表明中國的富強需要開放的海洋文明。
在此基礎上,面向開放世界的家園意識在海洋敘事電影中日漸明朗。在2017年吳京執導的《戰狼Ⅱ》片頭中,鏡頭首先呈現高空俯瞰的一條河流,在兩岸之間彎彎曲曲,由窄變寬,一路穿過陸地,然后注入洶涌、廣袤的大海,再轉入西印度洋馬達加斯加海域,上演了一場深海搏斗的場面。片頭結束后,電影首先講述一個拆遷現場,既有專業機械面對“和諧拆遷”的紅布黃字標語正在扒房推墻,又有反對人群手舉白布黑字“保護家園”等標語,或圍在工地呼號,或通過張貼白布黑字標語“我要吃飯,我要家園,拒絕強拆”的村道涌向工地,而拆遷現場的中心,是一家三代正在祭奠他們的兒子、丈夫或父親,一位剛剛犧牲的特種兵。這個片段凸顯了深層、凝重的家園意識。再與片頭中退役特種兵在遠洋區域勇斗海盜的場景相對照,與整個電影講述中國軍人拯救海外華僑與難民脫離戰亂地區的主題相對照,可以看到,家園意識已經被賦予全球化的開放性語境,被賦予海洋文化的內涵。
在中國電影領域,關聯海洋的家園意識并不限于全球化的人類視野,還涉及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現代生態文明視野。2016年梁旋、張春執導的動畫電影《大魚海棠》,講述椿代表的巨大魚類和人類的神奇關系,例如,大魚是人的靈魂,所有活著的人就是海里的一條大魚;大魚屬于天空,他們從天而降,來到海底世界生活,海底世界的天空連接人類世界的大海;人的靈魂會在人間漂泊很久,最終來到海底世界的天空盡頭,接受大魚的掌管。大魚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其他人。如此說來,大魚有兩種天空,一是囊括人類與海底的天空,或稱天上、天,屬于宇宙世界;二是大魚所生活的海底世界的天空,也是人類靈魂的最終歸宿,屬于海洋世界。這意味著,海洋既是大魚和人類交集之地,也是人類的終極家園。如果說傳統藝術從莊子學說中找到了山水家園的依據,那《大魚海棠》就使得源于莊子學說的海洋家園意識更受到了關注。
參考文獻:
[1]倪濃水.中國古代海洋小說的邏輯起點和原型意義——對《山海經》海洋敘事的綜合考察[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0-15.
[2]張晶.宗炳與謝靈運:從佛學到山水美學[J].江西社會科學,2016(7):73-84.
[3]李道新.融畫入影與哲理探尋——但杜宇電影“美”的表現及其歷史貢獻[J].當代電影,2014(6):23-29.
[4]張法.怎樣建構中國型海洋美學[J].求是學刊,2014(3):115-123.
[5]房默.中國海洋電影:命名、理論依據及其現實問題[J].百家評論,2019(1):73-79.
[6]雷禮錫.傳統山水美學與現代城市景觀設計[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103-105.
[7]秦良杰.電影《漁光曲》外景地考證[J].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6):45-49.
[8]徐放鳴,王莎.新英雄敘事與中國形象的影像構建——基于《戰狼》與《紅海行動》的觀察[J].閱江學刊,2018(6):99-105.
[9]雷禮錫.中國傳統環境藝術的信仰精神及其現代使命[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95-98.
作者簡介:李會君,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影視美學。
雷禮錫,湖北文理學院美術學院教授、藝術美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美學、藝術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