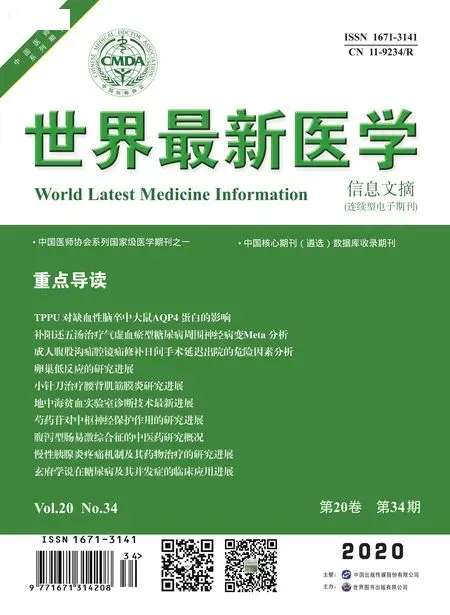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中醫藥研究概況
張曉艷,王會沙,郭喜軍,婁瑩瑩,霍耐月,丁曉坤,師虹艷
(1.河北省中醫院,河北 石家莊;2.石家莊市第三醫院,河北 石家莊;3.遷安市中醫院,河北 唐山;4.邯鄲市中醫院,河北 邯鄲;5.石家莊市中醫院,河北 石家莊)
0 引言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種以腹痛或腹部不適伴有排便習慣改變和(或)大便性狀異常為主要臨床表現且缺乏可解釋的形態學改變和生化異常的慢性功能性腸病。研究顯示:IBS 發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多發病,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降低生活質量[1]。根據其臨床癥狀,可將IBS 分為腹瀉型、便秘型、混合型、未定型,以腹瀉型(IBS-D)最多見。目前IBS-D 發病機制尚未闡明,西醫對于該病以對癥治療為主,治療效果欠佳,且病情易反復。近年來,中醫藥治療該病優勢明顯,治療方法較多,能有效緩解癥狀,降低復發率,不良反應少,現將其概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中醫學并無與IBS-D 相對應的病名,根據IBS-D 的臨床表現可歸屬中醫“泄瀉”“腹痛”“腸郁”“痛泄”等范疇。從諸多古代文獻對于這些疾病的論述看,IBS-D 的病因主要為感受外邪、情志失調、飲食不節、勞倦體虛等,如《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于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濕盛則濡泄。”《素問·至真要大論》曰:“暴注下迫,皆屬于熱。”說明風、寒、濕、熱等外邪是IBS-D 的病因之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云“喜則散,怒則激,憂則聚,驚則動,臟氣隔絕,精神奪散,以至溏泄。”表明情志失調也可形成IBS-D。《癥因脈治》曰:“飲食自倍,膏粱縱口,損傷脾胃,不能消化,則成食積,泄瀉之癥。”說明飲食不節亦為IBS-D 的致病因素。諸多原因導致脾失健運,形成水濕、食積、痰瘀等病理產物,阻滯中焦氣機,導致腸道功能紊亂,肝失疏泄,橫逆犯脾,脾氣不升則腹脹、腹瀉,腑氣通降不利則出現腹瀉,本病病位在腸,涉及肝脾腎三臟。現代眾多醫家總結前人理論并結合自己治療此病的臨床經驗,對本病的病因病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單兆偉教授[2]認為本病病機主要為脾虛濕盛,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主運化,胃主受納,脾以升為健,胃以降為和,若脾失健運,胃失攝納,則致水谷不化,清濁不分,混雜而下,則成泄瀉。李佃貴教授[3]認為情志失調、先天稟賦不足、飲食不節、感受外邪等因素導致濁毒內蘊,腸道傳導失司,治療應以化濁解毒為大法。徐陸周教授[4]認為,本病的發病基礎在于脾虛,臨證時又以脾氣虛和脾陽虛最為多見,故而補脾氣、溫脾陽當為該病的基本治療原則,并貫穿于該病治療的始末。
2 治療
2.1 辨證分型治療
谷春雨等[5]將80 例IBS-D 患者隨機分成兩組,治療組40例辨證論治:(1) 肝郁脾虛型,方選痛瀉要方加減;(2) 脾胃濕熱型,方選葛根芩連湯加減;(3) 肝郁氣滯型,方選四逆散;對照組40 例給予匹維溴銨治療,治療6 周后治療組的中醫證候積分比對照組下降更顯著,治療組總有效率90% 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7.5%(P<0.05)。劉鳳麗[6]將80 例患者隨機分為兩組,觀察組40例患者辨證分型為(1) 脾胃虛寒型,方選參苓白術散加減;(2) 肝郁脾虛型,方選痛瀉要方加減;(3)脾虛濕盛型,方選香砂枳術丸加減;(4)肝腎陽虛型,方選四神丸合附子理中湯加減,對照組采用口服匹維溴銨治療,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為95%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5%(P<0.05)。陳大權教授[7]將IBS-D 辨證分型為:濕熱型,溫膽湯主之;脾瀉型,參苓白術散主之;腎瀉型,四神丸主之;肝郁型,逍遙散合痛瀉要方主之;水濕型,五苓散主之,并指出臨床所見證型往往是一證或多證同時存在,應更根據具體情況隨證加減,兩方甚至三方聯合應用。任順平教授[8]認為IBS 以瀉為主時,多為脾虛濕濁內阻型,參苓白術散主之;以腹痛為主時,多為肝脾不調型,方選痛瀉要方合四逆散加減。
2.2 基本方加減治療
房志科等[9]運用痛瀉要方并隨證加減治療IBS-D,與對照組蒙脫石散治療進行比較,4 周后治療組癥狀積分降低程度明顯大于對照組(P<0.01),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1.84%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9.59%(P<0.01)。郝孝盈等[10]運用參苓白術散加味辨證加減治療70 例IBS-D,對照組70 例口服匹維溴銨、雙岐四聯活菌,治療8 周后,治療組總有效率98.57%優于對照組的91.43%(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腸道癥狀、生活質量、排便情況均有明顯改善,治療組優于對照組(P<0.05)。杜健等[11]采用烏梅丸并隨證加減治療30 例IBS-D,對照組30 例口服黃連素片,治療6 周后兩組腹痛、腹瀉評分均有下降,治療組改善情況優于對照組(P<0.05),治療組總有效率96.66%顯著高于對照組的90%(P<0.05)。梁瑞華等[12]將其收治的110 例IBS-D 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各55 例,其中對照組給予馬來酸曲美布汀片和雙歧桿菌,治療組服用柴胡桂枝干姜湯加減,試驗結果顯示:治療組總有效率98.18%顯著高于對照組81.82%,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3 中成藥治療
吳堅炯等[13]采用楓蓼腸胃康膠囊治療42 例IBS-D,對照組40 例給予安慰劑,4 周后結果顯示治療組總有效率為83.5%顯著高于對照組的18%(P<0.01)。旋寶秦[14]用痛瀉寧顆粒治療IBS-D,對照組口服復方阿嗪米特腸溶片、乳酸菌素片,治療6 周后,治療組總有效率98.3% 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6.7%(P<0.05)。徐海霞等[15]將90 例IBS-D 患者隨機平分為兩組,治療組給予參倍固腸膠囊1.8g,3 次/d,對照組口服匹維溴銨片50mg,3 次/d,2周后觀察兩組總有效率,其中治療組為93.3%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5.6%(P<0.05)。
2.4 中西醫結合治療
閆旭明[16]將80 例IBS-D 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36 例給予馬來酸曲美布汀膠囊,治療組44 例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逍遙散和五苓散,治療4 周后,治療組總有效率95.45%顯著優于對照組的86.11%(P<0.05)。陳麗萍[17]將132 例IBS-D 患者隨機平均分成兩組,對照組口服匹維溴銨片、蠟樣芽胞桿菌活菌膠囊,觀察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另口服升陽溫膽湯和補脾益腸丸,并使用中藥灌腸、穴位敷貼和針刺療法等中西醫結合治療,4 周后,對比兩組患者的生活質量顯示:觀察組患者的總體健康、生理功能、精神健康、情感智能各項得分情況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吳鳳英等[18]給予63 例非便秘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口服利福昔明片,另63 例觀察組患者在此基礎上聯合服用中藥湯劑,連續用藥30d,結果觀察組總有效率90.5%,對照組76.2,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5 其他療法
中醫治療IBS-D 方法較多,針灸、推拿、貼敷、灌腸、穴位注射等治療手段治療該病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充分體現了中醫治療方法的多樣性、靈活性。馮玉佳[19]對41 例IBS-D 患者給予中藥灌腸治療,灌腸方:黃柏10g,黃連10g,苦參10g,蒲公英10g,金銀花10g,野菊花10g,白花蛇舌草10g,蒼術10g,薏苡仁13g,香附7g,木香7g;對照組41 例行常規西醫治療,治療30 天后,觀察組總有效率95.1% 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3.2%(P<0.05),觀察組患者腹痛、腹脹、排便次數、大便性狀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武建華[20]采用溫針灸治療IBS-D36 例取穴天樞、關元、足三里、上下巨虛,對照組37 例給予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治療組總有效率91.66%顯著優于對照組的43.24%(P<0.01)。黃發樟[21]采用針刺神闕、中脘、天樞、氣海、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太沖,TDP 燈局部照射神闕,出針后督脈走罐治療IBS-D,對照組只采取針刺治療,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0.62% 顯著優于對照組的70%(P<0.05)。
陳亮亮等[22]運用脾胃培源方穴位貼敷治療32 例IBS-D,與對照組鹽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對比,結果顯示治療組癥狀積分改善優于對照組(P<0.05),治療組總有效率86.7%顯著優于對照組的65.5%(P<0.05)。
3 實驗研究
李雪等[23]研究發現,腸康方能顯著降低IBS-D 大鼠模型AWR 評分(P<0.05),降低血漿SP 水平(P<0.05),腸康方高、中劑量組結腸VIP 含量明顯升高(P<0.01,P<0.05),說明腸康方可能通過改善內臟高敏感性,降低血漿中SP 的水平,升高結腸黏膜中VIP 含量而達到治療目的。韓亞飛[25]通過對IBS-D 大鼠的研究發現,痛瀉安腸方可降低結腸組織PLC-γmRNA、TRPV1mRNA和PLC-γ、TRPV1 蛋白的表達,降低大鼠血清SP、CGRP 的水平,提示痛瀉安腸方通過下調PLC-y/TRPV1 信號通路的功能,抑制IBS-D 大鼠內臟高敏。
4 小結與展望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是消化系統臨床常見病、多發病,其發病機制尚未明確,被認為是一種多因素的生理心理疾病,雖沒有胃腸道的器質性病變,但嚴重影響生活質量。目前,中醫藥治療IBS-D取得了較好的療效,與西醫的對癥治療相比具有明顯的特色與優勢,如運用整體觀念、辨證論治、標本兼治、治療方法靈活多樣等,且不良反應少,復發率低,顯示出了良好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中醫藥治療IBS-D 仍存在很多不足:(1)在癥候診斷、辨證分型、療效評價標準方面,雖有一些共識意見,但仍缺乏統一的指標;(2) 多數研究設計不嚴謹,相對簡單,缺乏多中心、大樣本、雙盲、隨機對照、前瞻性研究,導致試驗研究結果說服力不強;(3)大多臨床研究時間較短,對治療該病的遠期療效觀察不足;(4)中醫藥多種方法治療該病的作用機制研究尚不明確,中醫藥療法治療該病目前仍以中藥復方為主,方劑藥理研究比較膚淺,缺乏理論依據。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進一步確定統一規范的癥候診斷、辨證論治、療效評價體系,探討設計更為合理嚴謹的科研方案,提供有說服力的數據,加強遠期療效觀察,明確中醫藥治療該病的作用機制,使中醫藥治療IBS-D 研究更為透徹,促進中醫藥治療該病的應用與推廣。
——中醫藥科研創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