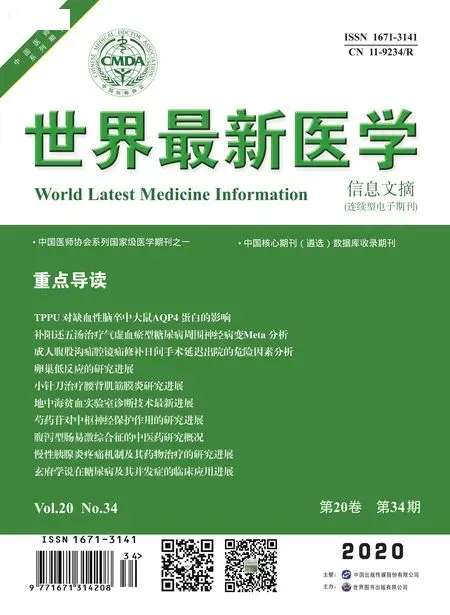腦鈉肽在房顫發生中的預測價值
劉玉婷,賈鋒鵬
(1.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慶;2.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重慶)
0 引言
心房顫動(簡稱房顫)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心律失常,在1999 年至2013 年間,房顫的住院率每年增長1%[1],房顫已成為全球健康關注的焦點。房顫會增加血栓栓塞、中風、心力衰竭等并發癥的風險,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及死亡率[2]。目前,識別有房顫發生風險的個體或其相關并發癥以及預測房顫復發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已作為心衰的生物標記物廣泛應用于臨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房顫與BNP 水平的增加有關。本文將對腦鈉肽在預測房顫發生中的作用進行綜述。
1 BNP 在房顫發生中的機制
腦鈉肽是指心肌細胞分泌的一類心臟神經激素,主要是由于壓力或容積負荷引起的心肌細胞壁張力增加而產生的[3],包括活躍的BNP 和不活躍的N 末端B 型利鈉肽原(NT-proBNP)。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腦鈉肽在房顫患者中較竇性心律人群高,且在房顫發生高危患者中更高[4]。在房顫患者中,BNP 主要由心房肌分泌[5],通過基因表達的變化進行調節,以應對多種刺激[6]。BNP 的分泌還可能與左房擴大及左房壓力升高有關[7]。此外,房顫患者中BNP 的增加可能與心律不規則和左房血流動力學改變有關[8]。還有研究表明,房顫易感患者BNP 水平升高可能是由包括全身炎癥在內的多種致病機制所驅動[9]。總之,房顫患者中BNP 水平的升高之間可能是多種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2 BNP 在房顫發生中的預測價值
2.1 BNP 對人群中房顫發生的預測價值
如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BNP 對人群中房顫篩查的價值。在最近進行的一項7173 名瑞典居民的篩查研究中,NTproBNP>125 pg/mL 在新發房顫(New-onset of atrial fibrillation,NOAF) 的檢測中,敏感性為75%,陰性預測值為92%[10]。在另一項研究中,使用124pg/mL 的NT-proBNP 截止值,陰性預測值為86%[11]。且其他兩項長時間大型研究表明,NT-proBNP 水平的增加與發生房顫的風險較高有關,NT-proBNP 的加入可能改善AF預測模型[12,13]。這些研究證明了BNP/NT-proBNP 在房顫檢測篩查標記物的價值,但其界值的統一性應在更多大型隊列研究中明確。
2.2 BNP 對急性冠脈綜合征后房顫發生的預測價值
NOAF 是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的常見并發癥,其發病率為2.3%-21%[14]。NOAF 是ACS 后預后不良的有力預測因子,也是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15]。NOAF 的確切原因尚未確定,缺血、心房灌注減少、左室舒張末壓和左房壓升高被認為是可能的潛在機制[16]。BNP 與ACS 患者NOAF 的關系已經在不同的研究中進行了研究。盡管結果不一,但最近一項由6000 名ACS 患者組成的薈萃分析結果顯示,在ACS 患者中較高水平的NT-proBNP 可能與更大的NOAF 風險相關[17]。BNP/NTproBNP 可能是預測ACS 患者新發房顫的有用生物標記物。然而,考慮到現有研究中存在的矛盾,BNP/NT-proBNP 是否能預測ACS后NOAF 發生風險以及是否需在NOAF 高危人群中進行抗凝治療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2.3 BNP 對非心臟心胸外科術后房顫發生的預測價值
房顫是普通胸外科手術后最常見的心律失常,發生率5%-25%[18]。據報道,術后房顫(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POAF)與死亡率提高、住院時間延長和術后長期生存率降低有關[19]。胸外科手術POAF 的確切生理病理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認為心肌再灌注損傷、炎癥和自身神經纖維功能障礙是POAF 風險增高的病理生理學改變[20]。多項研究表明血漿BNP/NT-proBNP 水平對POAF 的預測有一定價值。一項對包括10 項研究1844 名患者在內的薈萃分析顯示,BNP 水平升高對POAF 預測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5%和80%,且術后NT-proBNP 比術前BNP 水平有更好的預測價值[21]。另一項對接受心胸外科手術的患者進行的薈萃分析進一步證實了術前BNP 水平升高與POAF 風險增加之間的關聯[22]。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術前BNP 水平超過59 pg/mL 可能與非心臟胸外科手術患者POAF 的發生有關[23]。根據目前的證據,圍手術期對BNP/NT-proBNP 的評估似乎可用于識別大型心胸外科手術POAF 高危患者,BNP/NT-proBNP 水平可能可以作為一個輔助標準來決定是否有必要采取預防措施,如開β受體阻滯劑或胺碘酮等抗心律失常藥物來治療POAF。然而,適當的閾值及血液評估時間等尚需進一步的探究。
2.4 BNP 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房顫發生的預測價值
房顫是最重要的卒中危險因素之一,高達20%的缺血性卒中歸因于房顫[24]。此外,房顫相關性卒中更為嚴重,與死亡率和復發率增加相關[25],故房顫的檢測對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至關重要,從血小板抑制劑換為口服抗凝劑可以有效預防復發事件[26]。然而,目前對房顫尤其是對短暫和無癥狀的陣發性房顫發作的診斷具有挑戰性[27]。盡管有充分的文獻證明,增強及延長動態心電圖監測(Enhanced and prolonged Holter-ECG monitoring,EPM)顯著提高了陣發性房顫的檢出率[28],但EPM 不舒適、數據分析耗時、EPM 在腦卒中患者中的成本效益低,且目前衛生資源有限。因此,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每個病人都能接受EPM。BNP 水平在急性卒中患者中明顯升高,被認為是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住院期間NOAF 的預測因子。Hiroshi 等人回顧性分析222 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48 小時內的臨床資料,多變量分析顯示,BNP 是檢測pAF 的獨立預測因子之一,ROC 曲線示BNP 曲線下面積為0.80[29]。最近,Katrin 等人對373 名60 歲以上竇性心律且無房顫病史的急性腦缺血患者測定基線及3 個月后BNP 水平,并進行EPM 或常規腦卒中隨訪,結果顯示,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測定的BNP 水平可預測卒中患者中AF 風險的增加,大大減少EPM 篩查的次數[30]。結合目前的研究,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檢測血漿BNP/NT-proBNP水平可能有助于指導其抗凝治療指征,預防再次卒中的發生,但目前尚需進一步研究明確其臨床實際應用。
2.5 BNP 對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房顫發生的預測價值
在肥厚型心肌病患者中,BNP 水平升高與房顫的存在有關,但關于BNP 在預測房顫發生中的作用的證據很少[31]。在對70 例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平均隨訪53.09±1.87 個月的調查中,評估了不同參數(包括左房相功能、P 波離散度和NT-proBNP 水平)對房顫發展的預測價值。結果表明,NT-proBNP>720pg/mL 對房顫的預測有60%的敏感性和70%的特異性[32]。目前通過評估血漿BNP/NT-proBNP 水平以確定高危患者的證據較少,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2.6 BNP 預測ICU 患者房顫的發生
重癥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 患者房顫的發病率高達5-15%[33],Walkey 等人對49082 例嚴重敗血癥患者進行的回顧性研究發現出現NOAF 時,中風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較高[34]。然而,這些人群中房顫發生的生物標記物相關數據很少。一項對非心臟ICU 患者的研究確定NT-proBNP 水平的增加是NOAF 的獨立預測因子,且使用5.6 pg/mL 作為臨界值在檢測NOAF 中有65.2%的敏感性和82%的特異性[35]。在另一項對ICU 患者進行的調查中,NT-proBNP ≥600 pg/mL 是ICU 入院前3 天新NOAF 的獨立預測因素之一[36]。目前在ICU 中使用血漿BNP/NT-proBNP 水平預測房顫的證據尚不充分,且腦鈉肽水平受感染等因素影響較大,需要進一步評估。
2.7 BNP 預測心衰患者房顫的發生
全球心衰患者人數的迅速增長。超過一半的晚期心衰患者有房顫,房顫的出現預示著預后更差[37]。對涉及53969 名患者的16 項研究進行薈萃分析發現,合并房顫的心衰患者與竇性心律心衰患者相比,房顫的存在與全因死亡率獨立相關[38]。因此,在心衰患者中識別NOAF 高危個體很有必要。Vasile 等人對101 名射血分數保留的心衰(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HFpEF)患者進行分組后發現合并房顫組患者NT-proBNP 水平明顯高于竇性心律組(1639.12±993.03pg/mLvs 843.40±938.05pg/mL)[39]。且有研究表明,HFpEF 患者并發房顫與左心房大小和鈉尿肽增加有關[3,40]。此外,Kazutaka 等人分析了1170 例急性心衰患者表明NOAF 是1000 天死亡率和HF 事件的獨立預測因子,但多元logistic 回歸分析未發現BNP 與NOAF 獨立相關[41]。目前僅表明在心衰患者中房顫導致血漿BNP/NT-proBNP 進一步升高,但其對新發房顫的預測價值尚不明確。
3 小結與展望
強有力的證據表明,BNP/NT-ProBNP 與房顫發生有關,它們在不同情況下預測新發房顫的作用已經被許多研究小組深入研究,發現它們在篩查房顫高危個體及預測新發房顫風險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們容易獲得且比較便宜,適合臨床廣泛應用。將血漿BNP/NT-ProBNP 水平納入各類房顫風險評估模型中,提高風險預測能力和預后評估能力是當前研究的熱點。然而,要將其應用于臨床實踐還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