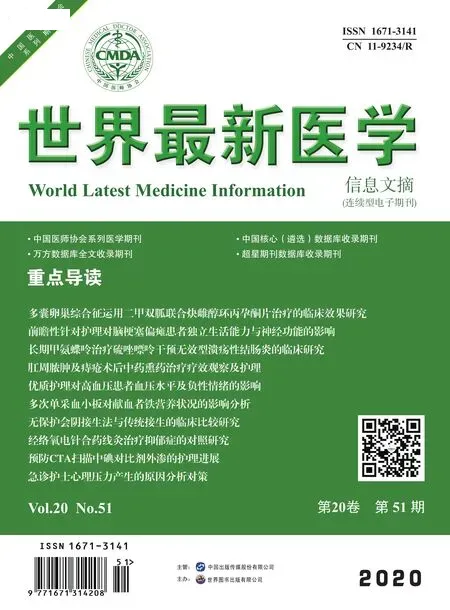非單胺類藥物治療抑郁癥的分子生物學機制研究進展
邊志達,李慧,王帆,康毅敏,李存保★
(1.內蒙古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2.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3.新疆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新疆 烏魯木齊)
0 引言
抑郁癥(Depression)是一種高度異質性、廣泛流行的嚴重精神疾病,嚴重影響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1]。根據WHO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抑郁癥已影響全球逾3.5億人,由此導致的直接治療成本及間接成本急劇升高,造成了沉重的社會經濟負擔,預計到2030年抑郁癥將位列世界疾病負擔的首位[2]。
抑郁癥發病機制尚未明確,目前學術界對抑郁癥發病機制的假設是基于大量臨床治療手段的應用。藥物治療在癥狀改善與治愈等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及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等單胺類藥物于上世紀末推出,逐漸成為治療抑郁癥的一線藥物。目前認為SSRI類及SNRI類藥物主要通過增加突觸間隙中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多巴胺(Dopamine, DA)等神經遞質水平來減輕抑郁癥狀[3]。然而,約1/3的抑郁癥患者病情并未因上述藥物的服用而出現明顯改善,這表明抑郁癥潛在發病機制的復雜性。與此同時,非單胺類藥物在減輕抑郁癥患者癥狀,改善其預后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因此探究非單胺類藥物治療抑郁癥發病的相關分子生物學機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就非單胺類抗抑郁藥物的分子生物學機制的相關假說做簡單綜述。
1 COX-2抑制劑和TNF-α拮抗劑的抗神經炎性假說
早期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IL-6等炎性因子常出現明顯增加,且患者在應用炎性因子制劑干擾素α后,常出現明顯的抑郁癥狀[4]。另外,抗抑郁藥物可以顯著改善炎癥引起的抑郁行為。因此,有學者認為抑郁癥可能是一種慢性炎癥性疾病。
選擇性環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 COX-2)抑制劑是一類新型非甾體抗炎藥物,因其能夠選擇性地抑制COX-2活性,被廣泛用于類風濕關節炎的抗炎治療。目前認為,COX-2抑制劑可能通過抑制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PGs)合成,增加內源性大麻素,降低其代謝產物前列腺素甘油酯水平,進而減輕患者的抑郁癥狀。該研究認為COX-2抑制劑可能通過抑制上述炎癥因子對吲哚胺雙加氧酶(Indoleamine Dioxygenase, IDO)的作用,扭轉IDO通過色氨酸代謝影響對5-HT合成的抑制。IDO能夠將色氨酸代謝為喹諾酸和kynurenic酸。喹諾酸是谷氨酰胺能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 NMDA)受體的強激動劑。細胞因子誘導的喹諾酸水平升高可能損害突觸可塑性,從而導致抑郁癥的認知障礙和記憶障礙。目前在臨床治療過程中,對使用單胺類抗抑郁藥物瑞博西丁或氟西丁治療的抑郁癥患者加用COX-2選擇性抑制劑塞來昔布能夠顯著改善患者的抑郁癥狀,并且能夠明顯降低抑郁癥患者的IL-6血清水平。上述研究提示海馬COX-2通路可能是抑郁癥治療藥物開發的一個新靶點。
除COX-2抑制劑可單獨或與SSRIs聯合應用于抑郁癥的治療外,對TNF-α的相關藥物研究同樣為探索炎癥及抑郁癥之間的相關性提供了新的依據。目前認為TNF-α可通過涉及初級傳入神經的快速傳輸途徑穿過血腦屏障或直接作用于HPA軸,改變CRH、ACTH等的水平,抑或通過刺激IDO激活血清素轉運體與抑郁癥的病理生理學相聯系[5]。雖然TNF-α拮抗劑尚未正式應用于抑郁癥的臨床治療,但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相信不久的將來TNF-α拮抗劑也將在抑郁癥治療過程中起到相應的作用。
2 谷氨酸能受體調節劑與谷氨酸能假說
2000年,Berman等[6]基于前人研究開創性的運用NMDA開放通道阻滯劑氯胺酮對抑郁癥患者進行單次靜脈注射,發現患者體內產生即時和長期的抗抑郁作用,拉開了人們對谷氨酸能在抑郁癥中發揮作用的相關研究的序幕。
氯胺酮是一種非競爭性的谷氨酸能NMDA受體開放通道阻滯劑。當NMDA受體處于開放狀態時,氯胺酮與NMDA受體結合。直至通道關閉后,受體方可因內源性配體重新激活而于通道孔內緩慢解離。由于γ-氨基丁酸(Gamma Aminobutyric Acid, GABA)能神經元比錐體神經元更具有代謝活性且NMDA受體處于開放狀態的可能性更高,Duman等[7]認為氯胺酮會率先通過與GABA能神經元上的NMDA受體結合,阻止中間神經元激活,進而抑制錐體細胞在大腦中產生有針對性的谷氨酸突增。研究表明,氯胺酮可激活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的信號傳導及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釋放,激活突觸后AMPA受體,通過增加大腦額葉皮質層V錐體神經元的樹突棘數量,促進突觸和脊柱神經元形成[8]。
截至目前,氯胺酮已逐步應用到臨床治療當中,但氯胺酮的類精神病性副作用及藥物濫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其在臨床中的廣泛使用。因此,具有快速氯胺酮類抗抑郁作用但耐受性較好的代謝型谷氨酸受體(Metabolic Glutamate Receptors, mGluRs)調節劑被逐步開發并運用到了臨床。mGlu2受體位于突觸前末端及突觸后位點,可抑制谷氨酸傳遞。mGlu2/3受體拮抗劑可能通過促使谷氨酸增加并使內側前額葉皮質的mTORC1信號增強,產生類氯胺酮樣的快速抗抑郁反應[9]。這一發現可能為NMDA受體功能的調節提供了替代方法。
3 褪黑素MT1/2受體激動劑與神經可塑性假說
目前學術界將神經可塑性定義為神經系統通過重組其結構、功能和連接來對內在或外在刺激做出反應的能力[10]。長期服用抗抑郁藥物通常能夠有效逆轉抑郁癥患者發作期海馬體積的明顯減小與海馬樹突狀萎縮以及細胞死亡的增加,并延緩BDNF表達的降低等[11]。褪黑素(Melatonin, MT)受體激動劑阿戈美拉丁(Agomelatine)被發現可以選擇性地增加腹側海馬的細胞增殖和神經發生,并提高新生細胞在整個海馬的存活率。
阿戈美拉丁可能通過刺激海馬齒狀回的神經發生,減少額葉前部和額葉皮質由于急性應激引起的谷氨酸釋放增加,并與上述的谷氨酸能假說相聯系。阿戈美拉丁可通過促進細胞增殖和BDNF mRNA表達提高海馬腹側新形成細胞的存活率。與此同時,長期的阿戈美拉丁治療對調節海馬體和前額皮質中BDNF水平明顯好于一般SSRI類藥物。
上述對抑郁癥治療的神經可塑性假說的相關研究同樣為神經源性化合物是否有希望改善某些不良神經認知并發癥提供了大量依據。NSI-189這一新型神經源性化合物已逐步投入臨床前實驗中。
4 結論與展望
大腦結構以及神經化學變化是抑郁癥和情緒障礙的重要特征。這些變化或可通過行為及藥物治療來阻止或逆轉,但需進一步確定這些改變的分子信號通路,再開發更新的、更安全的治療藥物。大量非單胺類藥物已逐步應用于臨床,為減輕患者癥狀,改善患者預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短期內,具有良好療效的藥物開發可能會繼續依賴于經驗數據和意外發現,而非基于對疾病病因的全面了解。因此,在開發治療抑郁癥的新藥物療法方面仍然存在著大量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