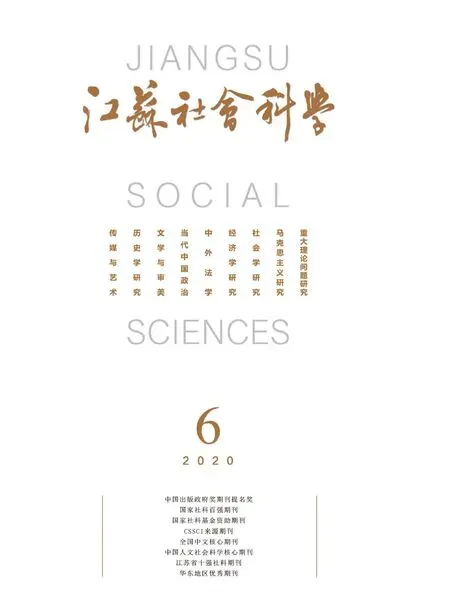鄉村文化振興與鄉村共同體的再造
朱志平 朱慧劼
內容提要 鄉村共同體作為當代中國城鄉關系和鄉村發展的歷史基礎和鮮明底色,是鄉村記憶的情感基礎,更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和強大助力。以組織形態為表征的制度約束和以倫理規范為內核的文化約束始終貫穿于鄉村共同體的歷史演變之中。城鄉要素的頻繁流動、個體化傾向、禮俗衰敗和村民自治組織的異化給鄉村共同體帶來挑戰。當前,要利用鄉村文化振興來再造鄉村共同體,以黨建文化引領鄉村集體,以家庭文化重塑鄉村倫理,以公共文化激活公眾參與,以文化產業助力鄉村發展,最終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
鄉村是鄉村社會各部分有機聯結的共同體,集生產、生活、文化和社會等多種功能于一體。傳統鄉村的共同體屬性明顯,內生于傳統鄉村的宗族、倫理、文化等因素對鄉村共同體的建立和維持有著積極作用,但在社會轉型背景之下,鄉村共同體逐漸式微。在現代化和城鎮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鄉村人口、資本等快速流入城市,許多鄉村出現凋敝的頹勢。為了重新激活鄉村發展的活力,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發展關乎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而農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基石,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托和實踐場域。只有在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去理解鄉村社會的變遷,從歷史的視野去發現和認識鄉村共同體,才能夠更好地發現鄉村共同體的內在邏輯及其當代價值,認識鄉村共同體再造對鄉村振興的積極意義,最終助推鄉村社會的全面發展。
一、鄉村共同體及其當代價值
(一)鄉村共同體的相關研究
“共同體”(Gemeinschaft)一詞最早是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來的。在《共同體與社會》中,滕尼斯區分了作為本質意志的共同體和作為選擇意志的社會[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8頁。。滕尼斯認為,共同體的特征包括:①意志類型是本質意志-情感動機型;②意志取向是整體意志;③行動方式是傳統的行動;④互動表現是本地網絡,呈現密集型;⑤生活范圍是家庭、鄉村或城鎮;⑥維護手段是和睦感情、倫理和宗教;⑦結合性質是有機的方式[2]參見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修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共同體的概念區別于以目的動機型的選擇意志和法律契約作為維護手段的社會。通過共同體與社會的劃分從一個側面描繪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共同體概念在一開始并未有地域屬性,滕尼斯僅指出共同的生活范圍往往在家庭、鄉村或城鎮。美國學者將“Gemeinschaft”譯為“community”,隨后學界普遍認可“community”作為地域共同體的概念。深受芝加哥學派社區研究傳統影響的費孝通教授將“community”譯為中文“社區”[3]焦若水:《人文區位與位育中和——中國社區理論發展的理論淵源與民族品格》,〔南京〕《學海》2014年第4期。,“共同體”才與“社區”真正聯結起來。費孝通所區分的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實際上是共同體和社會的變體。
在費孝通等人的引領之下,中國學者發現,傳統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村正是共同體的寫照,兼有滕尼斯所述的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這三種共同體的特征。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勾畫出的傳統鄉村中的“差序格局”“無訟”等關鍵詞[4]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9頁。,標識出中國農村作為地域共同體的重要特征。但日本學者對中國鄉村的共同體性質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清水盛光、平野義太郎、戒能通孝和福武直等人曾開展了一場關于中國是否存在村落共同體的論戰。平野義太郎和清水盛光認為中國的村落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具有顯著的村落共同體性質;戒能通孝、福武直強調,中國農村中并不存在對村民具有巨大制約作用的社會規范,村民的關系是擴散性的,村落本身不是共同體,而僅僅是一種結社性質[5]參見李國慶:《關于中國村落共同體的論戰——以“戒能-平野論戰”為核心》,〔北京〕《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6期。。盡管如此,中國學者普遍認可中國傳統鄉村的共同體性質[6]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0頁。。他們認為,傳統鄉村是生產性的、以農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基礎的地域共同體[7]文軍、吳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傳統村落的轉型及其鄉村性反思》,〔北京〕《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4期。,更是以傳統家族主導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社會生活共同體[8]項繼權:《中國農村社區及共同體的轉型與重建》,〔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還是鄉土社會的文化觀念、民間信仰組成的文化共同體[9]季中揚、李靜:《論城鄉文化共同體的可能性及其建構路徑》,〔南京〕《學海》2014年第6期。。
在社會轉型背景之下,中國鄉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鄉村共同體也隨之發生變化。當代鄉村共同體的學術討論中主要有村落終結論和村落再生論這兩種觀點。村落終結論認為,傳統村落在空間、社會結構和組織方式上面臨著失序和解體,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10]李培林:《巨變:村落的終結——都市里的村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村落再生論認為,傳統村落的共同體本質和網絡關系可以借助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力量呈現新的形式,實現再生[11]文軍:《重構中國傳統村落的社會意義》,〔濟南〕《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9 期。。盡管兩種爭論尚無定論,但學者們普遍指出當前鄉村共同體的衰敗[12]梁晨:《鄉村工業化與村莊共同體的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傾向。在面臨非農化、市場化和城鎮化三大壓力下,鄉村共同體逐漸式微[1]吳業苗:《鄉村共同體:國家權力主導下再建》,〔西安〕《人文雜志》2020年第8期。,學者們提出從國家權力主導[2]吳業苗:《鄉村共同體:國家權力主導下再建》,〔西安〕《人文雜志》2020年第8期。、主體性建構[3]毛綿逵:《村莊共同體的變遷與鄉村治理》,〔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社會組織建設[4]連雪君、呂霄紅、劉強:《空心化村落的共同體生活何以可能:一種空間治理的視角》,《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共同情感[5]劉祖云、李烊:《在鄉村振興語境下培育“情感共同體”》,〔南京〕《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等多元角度來重構鄉村共同體。
傳統鄉村是集生產、生活、文化和社會等功能于一體的社會生活共同體。鄉村共同體在鄉村社會內部事務管理和外部風險應對上有重要影響,促成鄉村文化、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等內生性因素在鄉村社會運行和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在中國,鄉村共同體一度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在當下,以村民自治組織為主干的鄉村共同體越發松散,鄉村社會原子化趨勢愈發明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原先鄉村共同體所扎根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傳統鄉村共同體作為自治主體的歷史地位和價值,表明鄉村共同體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重要價值。因此,回到鄉村共同體的歷史演變及其軌跡,不僅可以掌握鄉村社會變遷的主線,深刻認識當前鄉村社會發展和轉型的現實背景,而且可以嘗試通過鄉村共同體的重構來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從而促進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
(二)鄉村共同體的當代價值
傳統鄉土社會作為鄉村共同體的典型形態已經發生了變遷,但是當代中國鄉村依然存在著共同體的基礎。在大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契機之下,鄉村共同體建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為鄉村建設和長遠發展提供強大的力量源泉,這是鄉村共同體當代價值的體現。
鄉村共同體是鄉村變遷的鮮明底色。按照滕尼斯的共同體理論,中國傳統鄉村是建立在本質意志,也就是情感動機的基礎之上。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和差序格局的行動規范是中國鄉村的歷史底色。宗族充當著集體的代言人,既保障家庭的基本權利,又約束族人的日常行為。隨著宗族和傳統文化的式微,鄉村社會在社會轉型之中呈現前所未有的變遷,但鄉村共同體的屬性又并未全然消亡,倫理觀念和宗族組織依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能夠成為鄉村社會發展軌跡的重要基礎。
鄉村共同體是鄉村記憶的情感基礎。鄉村記錄著社會的變遷過程,是鄉愁生發的載體。作為共同體的鄉村本身就承載著國人對傳統鄉村的記憶、想象和期待。一旦鄉村共同體衰亡,那么鄉村就會變成建筑和人口的生活空間,很快會被城鎮同化,鄉村記憶和鄉愁也會隨之消失。鄉村記憶是農業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鄉村不僅僅是地域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還是情感的共同體。只有文化和情感的共同體繼續存續,鄉村文明和鄉村文化才能得以延續和發展。
鄉村共同體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出臺,提出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來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指出,鄉村振興要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國家權力、市場、社會資本等多元主體進入鄉村時,想要保障農民的權益,發揮多元主體的合力,就必須構建強有力的鄉村共同體,讓鄉村共同體成為農民實現主體作用的載體,成為農民分享鄉村振興紅利的平臺。鄉村共同體不僅僅能夠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還能夠在與市場等多元主體的互動、合作和交流中充分發揮能動作用,為鄉村振興注入強大的內生力量,讓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獲益。
因此,鄉村共同體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和現實價值。鄉村共同體作為當代中國城鄉關系和鄉村發展的歷史基礎和鮮明底色,是鄉村記憶的情感基礎,更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和強大助力。
二、鄉村共同體的歷史流變與生成路徑
(一)鄉村共同體的歷史流變
要了解鄉村共同體的現實流變必須回到中國鄉村的歷史。中國鄉村在歷史洪流之中主要有三種歷史形態。第一種歷史形態是傳統鄉土社會,這一社會形態持續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部落和氏族轉化為宗族,農耕文明建立起來,人們聚族而居。生活在鄉土中的人們被血緣和地緣聯結起來,宗族是集體利益的代表,也是共同體發揮作用的載體。正如秦暉所說,中國古代“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1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2頁。。在傳統鄉土社會,宗族既是社會制度系統,又是文化系統,以孝道為核心的倫理是宗族治理的根本。而國家權力并沒有進入鄉村,除了管理納稅和征兵外,國家權力幾乎沒有辦法涉足宗族內部事務。此時的宗族是治理實體,設有主管和財務,會定期或者不定期召開宗族大會,有專門的族田、族產,管理族內的公共事務。宗族可以通過族規家訓等方式來教化族人,也可以用宗族產業來開辦私塾。
在傳統鄉土社會,宗族具有很強的排外性,適合小農經濟為主的傳統農作方式。傳統鄉土社會的宗族就是鄉村共同體的體現。這些都符合滕尼斯對共同體生活形態的表述——人們基于情感動機,在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聯結下形成共同體,人們生活的空間主要在鄉村,互動關系網絡是本地網絡,互動規范是和睦感情、倫理和對祖宗的信仰,宗族有集體意志,并具有很強的約束力[2]參見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修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在傳統鄉土社會后期,隨著工業城市的崛起和連綿不斷的戰火,鄉村共同體依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后,政府開展了對農村的改造,取締了土地私有化制度,建立了生產互助組織。原先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宗族共同體不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于是,集政治、經濟、社會于一體的人民公社應運而生,中國鄉村共同體經歷了第二種形態。人民公社打造了一個圍繞集體生產為核心的鄉村共同體,人們利用集體的生產資料來進行生產,按照生產力來分配勞動成果。此時,以制度驅動的鄉村共同體在傳統鄉土社會的共同體基礎上發生了異變,人們依然在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聯結之下共同生產生活,但是互動規范不再是傳統的倫理規范,而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倫理,鄉村文化在此時處于弱勢地位。
改革開放時代,人民公社解體,市場經濟體系隨之建立,中國農村迅速建立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第三種形態的共同體隨之產生。此時,傳統倫理和宗族有所復蘇,但經濟基礎已然不在,鄉土社會的血緣和地緣關系聯結紐帶越來越松散,無法再發揮強有力的村落控制作用,只能依靠村民自治組織來管理集體的事務。但村民自治組織雖然是村民自發組成的社會組織,但是由于缺乏經濟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鄉鎮政府的指導和經費支持,制度和文化的約束都呈現式微的狀態,鄉村共同體逐漸衰弱。
(二)鄉村共同體的生成路徑
從傳統鄉土社會到農村集體化時期,再到改革開放后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三種形態的鄉村共同體演變,以組織形態為表征的制度約束和以倫理規范為內核的文化約束始終貫穿于其中。制度和文化是鄉村共同體的兩個重要維度,代表了社會控制的制度約束和情感合力。美國社會學家羅斯提出“社會控制”的概念,認為社會控制是每個組織不可或缺的機制,因為社會控制可以保證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一致性,使社會系統能夠穩定、有序的持續運行[1]〔美〕E·A·羅斯:《社會控制》,秦志勇、毛永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頁。。鄉村共同體的生成同樣需要依靠制度和文化這兩種社會機制。一方面,制度約束明確鄉村與鄉村之間的邊界,對共同體中的個人提出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對人際交往、日常生活、公共領域等方面的規范做出詳細指導和規定;另一方面,以柔性和普遍性為特性的文化對制度約束提供有益補充,又讓人們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統一體,形成內在凝聚力。因此,制度和文化是鄉村共同體的兩個重要生成路徑,共同作用于鄉村共同體的發展和變遷。
從制度-文化這一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鄉村共同體變遷的內在邏輯。傳統鄉土社會中,以孝道為核心的倫理觀念發揮積極的作用,規范人們的日常交往,同時又讓人們緊密地聯結在宗族的周圍;以宗族為表征的制度發揮重要功能,管理集體事務,發揮集體意志。此時,文化和制度在某種意義上是合一的,建立在倫理本位上的文化通過宗族這一組織形態來發揮重要作用。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和具有約束力的制度的聯合,傳統鄉土社會的共同體屬性是最強的。進入集體化時期,宗族的組織形態和文化內聚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國家權力發揮著強大的制度約束,讓人們緊密地聯結成為一個以生產為主的鄉村共同體。當然,倫理觀念和傳統文化規范并非消失了,只是文化主要退居家庭之中,在集體中很少發揮較強的約束。改革開放以后,原先的倫理文化有所復蘇,但已經難以發揮明顯作用,而村民自治組織建立在自發組織的基礎之上,文化約束和制度約束都處于較弱的水平,鄉村社會控制屬性減弱,鄉村共同體走向衰弱。
通過制度-文化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生產方式對鄉村社會控制的方式有一定的影響,進而對鄉村共同體的發展變遷產生作用。傳統鄉土社會是建立在以倫理和宗族基礎上的鄉村共同體,而當前,倫理和宗族都難以發揮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功能,因此,鄉村共同體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

三、鄉村共同體的困因及其突破
(一)鄉村共同體衰弱的原因
鄉村共同體的衰弱已經成為農村研究者普遍認同的事實[2]毛丹:《村落共同體的當代命運:四個觀察維度》,〔北京〕《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1期。。在城鎮化背景之下,鄉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動,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三留守”群體給鄉村共同體的維持和發展帶來極大的挑戰。但真正給鄉村共同體帶來挑戰的則是來自于城鄉要素的頻繁流動、鄉村的個體化傾向、禮俗衰敗和村民自治組織的異化。
第一,城鄉要素的頻繁流動。傳統鄉土社會建立的以倫理和宗族為基礎的共同體與小農經濟形態相匹配,而集體化時代制度驅動的鄉村共同體則建立在農業集體化的生產方式基礎之上。在兩種鄉村共同體形態對應的生產方式下,鄉村都是處于相對封閉和區隔的狀態,鄉村社會內部的同質性較高,缺少與外面社會的溝通和交流,較少受到城市、工業等現代化因素的影響,因此能夠發揮制度和文化的合力。但城鄉越發頻繁的流動使得人們的異質性程度不斷上升,也讓在地的文化和制度缺乏對流動人口的約束。鄉村凋敝表明鄉村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衰弱,鄉村人口和產品等要素越來越多地流向城市,頻繁的流動使得鄉村難以建立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控制機制。
第二,個體化傾向。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個體化傾向開始逐漸融入鄉土社會中的自我,出現了社會原子化趨向[1]呂方:《再造鄉土團結: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與新公共性》,〔天津〕《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集體觀念淡化。個體化傾向下的行動邏輯是超越理性的。以村委會選舉來看,制度設計中的村委會選舉是個人出于對候選人增進集體利益的能力的肯定,因為增進集體利益就是增進個人利益。但個體化傾向的個人并不一定會給有可能為集體帶來利好的候選人投票,因為另一個候選人給予其一定的經濟利益。個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行動,實際上是由于增進集體利益的承諾的價值要低于其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正如孟德斯鳩曾說過的那樣“當我們看到選票可以賣錢的時候,不應當感到驚奇”[2]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1頁。。
第三,禮俗的衰敗。在傳統鄉土社會,禮俗文化充當鄉土社會治理的重要職能。禮俗文化的衰敗不僅僅是因為法律、制度等嵌入鄉土社會,一定程度上撼動了禮俗的主導,它的衰敗還受到自我主義傾向本身的影響。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交換關系擠壓原先的圣俗關系,讓禮俗文化的社會性土壤發生改變,自我行動就會傾向于選擇能夠用于解釋和指導其行動的道德體系,法律和契約關系對農村市場交換行為和社會互動行為都具有很強的約束力。于是,原先的“克己復禮”不再存在,農村居民不再約束自己遵從禮俗,而是在自身利益的基礎上選擇性地接受“禮”的約束。從鄉村治理的角度來說,法律和契約的確定性能夠為鄉村社會的穩定和治理帶來更為穩固的制度支撐,禮俗文化的衰微是必然的。但是,熟人社會對法治的過度依賴,會弱化傳統的禮俗文化。
第四,村民自治組織的異化。村民自治的制度設計在于通過村民選舉出集體利益的代表人來管理集體的事務,但實際操作中,部分地區的村民自治組織出現了異化現象。半行政化[3]王麗惠:《控制的自治:村級治理半行政化的形成機制與內在困境——以城鄉一體化為背景的問題討論》,〔北京〕《中國農村觀察》2015年第2期。、賄選[4]仝志輝:《分利型村治中的賄選與村級權力正當性——基于L村選舉史的討論》,《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派系斗爭[5]盧福營:《派系競爭:村委會選舉面臨的新挑戰——以浙江白村的一次村委會選舉為例分析》,〔北京〕《中國農村觀察》2005年第1期。給村民自治的實現帶來阻礙。村民并未將村委會作為集體利益的代表,而是把村委會作為國家權力和資源配置的中介,因此會將村干部視為領導者,而不是集體利益的代理人。村民自治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代理和被代理的關系,而出現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村民自治制度作用的發揮。此外,村民自治也并非關注所有人的利益,村民集體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村干部和鄉村精英的影響。
(二)文化振興與鄉村共同體的再造
隨著“項目制治理”[6]折曉葉、陳嬰嬰:《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和治理邏輯——對“項目進村”案例的社會學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在農村的普遍施行,鄉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源政策的主導方和村集體的代表方之間的互動,也就是政府和村民委員會成為影響鄉村治理和鄉村共同體的重要因素。村民委員會作為村集體利益的代表,其工作重心轉移到爭取項目上來,因為項目就意味著村集體的公共利益。但實際上,以村民自治制度為核心理念的村民委員會注定只能為鄉村共同體提供弱制度的支持,而無法像集體化時期那樣發揮強有力的制度約束力,因此,要再造鄉村共同體必須對當前農村“弱制度-弱文化”的現狀做出改變,這種改變要以文化為主,兼顧制度。通過構建強有力的文化規范,強化現有制度的約束,再造鄉村共同體。江蘇徐州的馬莊村在鄉村文化振興和共同體的再造上有著值得借鑒的經驗。
首先,以黨建文化引領鄉村集體。村民委員會-村小組的模式為政策的上傳下達、村集體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宣傳提供便利,但無法建構強有力的集體,且缺乏“自下而上”的渠道和空間,隸屬于鄉鎮黨委又管理村內黨員的村黨支部則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村黨支部可以利用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組織優勢,積極吸收和發動村內黨員,讓黨員動員其家庭成員和親屬,形成廣泛而且全面的社會動員網絡;還可以利用黨組織活動、黨員聯席會以及黨群關系的優勢來充分吸取群眾意見與訴求。以黨建文化引領不僅僅可以彌補村民自治組織可能的低參與,廣泛動員村民參與到集體事務和集體活動中來,還可以發揮組織優勢,讓政府和黨組織的政策、理念等得到迅速傳達和執行。馬莊村村黨委下轄7個黨支部,黨員120名。馬莊村創造性提出“一強三帶”工作法,積極利用鄉村黨組織和黨員,為村集體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一強”是指強戰斗堡壘。馬莊村積極開展黨員隊伍建設,利用支部和黨員評獎評優增強黨員服務意識。此外,馬莊村還實行“黨員聯系戶”制度,每戶人家都有聯系的黨員,每名黨員都有包干聯系戶。每月25日為黨員活動日,實行黨員積分制管理,開展農村黨員“掛牌亮戶先鋒行”、黨員干部志愿夜巡、“十佳黨員”評選等活動。支部黨員積極配合村黨委和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為服務集體事務貢獻重要力量。
其次,以家庭文化重塑鄉村倫理。傳統倫理觀念約束力的普遍減弱在家庭文化的衰退中可見一斑,推動鄉村共同體的再造必須要重建鄉村倫理規范體系。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也是鄉村社會的縮影,重塑家庭文化就是重塑鄉村社會的文化和倫理觀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通過家庭倫理觀念的重塑“推己及人”,為建構集體的文化和倫理奠定基礎。傳統鄉土社會的人倫觀念在當下盡管有所削弱,但依然對農村居民具有普遍的影響,對約束和指導村民行為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通過重塑傳統倫理觀念可以建構具有集體約束力和集體認同感的社會規范。因此,要充分利用傳統倫理規范,重塑“孝老敬親”的家庭倫理觀念,以村規民約的形式對村民行為做進一步的引導,構建和諧的家庭關系和人際關系。1989年,馬莊村創造性地實行“家庭檔案制管理”。家庭檔案涉及村民家庭遵守村規民約、完成集體任務、參與村內事務和公益活動等方面內容,村民組長根據村規民約和村兩委工作要求,負責對每個家庭的平時表現進行打分并記錄在檔,每月一公布、年底亮總分。積分管理辦法中,“參加義務勞動加2分,參加升旗儀式加2分,……鄰里吵架扣2分,不參與村組活動扣2分”。用記分的方法評選出“十佳好婆婆”“十佳好兒媳”“最美家庭”“五好家庭”和“十星級文明戶”等榮譽人物和家庭。
再次,以公共文化激活公眾參與。公眾參與是個人參與集體生活的基礎,也是鄉村共同體的必然表現,只有普遍的公共參與才能夠讓農村居民真正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教育。公共文化具有廣泛的約束力和號召力,通過構建公共文化不僅能夠豐富農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可以讓農村居民積極參與到集體事務中來,培育集體意識和集體觀念。培育公共文化需要物質保障和制度保障,物質保障是指公共文化活動的空間和相關資源資金的支持;制度保障則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來保障公共文化活動的參與和持續性。更為具體的,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可以通過打造鄉村大禮堂、村史館等公共空間,也可以通過民俗活動、鄉村晚會等形式來積極開展文化活動。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馬莊時充分肯定了馬莊的文化振興成果。自1988年組建農民樂團以來,馬莊農民樂團分別在意大利、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參加比賽交流,在國內外先后演出8000余場次。馬莊村建有村史館1座,占地面積380平方米,村史展示以“馬莊文化”為主線,包含歷史沿革、黨的建設、先進文化、經濟建設、社會建設、鄉村治理、榮譽薈萃等部分,村史館還懸掛有馬莊的村歌《馬莊之歌》的詞譜和曲譜。馬莊還建有村文化禮堂,舞臺面積80平方米,禮堂配有中式座椅150把。周末舞會、燈光廟會、農民運動會、升旗儀式等活動定期舉行,村民積極參與,讓集體文化活動成為馬莊特有的文化風景。
最后,以文化產業助力鄉村發展。打造鄉村共同體是要通過共同體的建設助力村集體的發展,增進村民福祉,因此鄉村文化振興初具規模后就可以將鄉村文化打造成文化產業,通過特色文化品牌、產業來產生經濟效應,促進鄉村產業的發展。鄉村特有的民俗文化、自然風光、歷史文化資源等都可以被納入到鄉村產業體系中來,培育觀光農業、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創意產品等文化產業和衍生品,進而以文化振興為契機助力鄉村經濟發展。通過文化產業建設又可以反過來培育鄉村共同體的意識和認同,形成合力助推鄉村振興。馬莊村打造了以馬莊文化創意綜合體、香包文化大院以及民俗文化廣場、潘安湖婚禮小鎮、高效農業園等為一體的鄉村文旅產業。在非遺中藥香包傳承人的帶領下建立非遺中藥香包的產供銷體系,帶動全村200 余人就業。村里建成香包主題客棧、香包廣場和香包手工坊,年產值超千萬。發揮中藥香包品牌效應,建有100畝中草藥苑。
通過建構以黨建文化、家庭文化和公共文化為主體的鄉村文化,農村居民與村集體緊密地聯結了起來,村民積極廣泛參與集體事務,為鄉村共同體的建設和發展建言獻策。文化產業的發展更是助推集體經濟的發展,為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和組織振興注入了強大的經濟動力。
四、結語:鄉村共同體再造與文化振興之路
鄉村共同體建設是解決鄉村凋敝、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以組織形態為表征的制度約束和以倫理規范為內核的文化約束是鄉村共同體的兩個重要維度,是鄉村共同體生成的重要路徑。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城鄉要素的頻繁流動、鄉村的個體化傾向、禮俗衰敗和村民自治組織的異化等趨勢,使傳統鄉土社會的鄉村共同體逐漸衰弱。當前,鄉村共同體形態的制度約束和文化內聚力都處于較弱的水平。重構鄉村共同體必須要在制度和文化兩個方面入手,以文化振興為主,兼顧制度建設。
優化鄉村制度體系。農村集體化時期的經驗表明,單靠制度的強力約束,而不依靠文化的方式存在較大弊端,只有在制度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夠推動鄉村共同體的發展。在市場化和城鎮化浪潮的背景之下,以村民自治制度為核心的鄉村制度遭遇低度參與,難以發揮強有力的制度約束。要防止村民自治制度的異化,杜絕村委會或村干部一言堂,必須充分發揮黨委領導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優勢,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通過黨員實現政策的下達和村民訴求的上傳,積極動員農村居民參與集體事務的討論。要充分利用黨的基層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合力,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讓黨員成為引領和推動鄉村共同體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鄉村文化的振興是鄉村共同體建設的重心。文化是鄉土社會的根,也是鄉村共同體內在凝聚力和認同感的源泉。要重塑鄉村社會的主流文化,打造黨建文化、家庭文化、公共文化、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體系,鼓勵通過村規民約、“紅白理事會”、鄉賢[1]季中揚、張興宇:《新鄉賢:基層協商民主的實踐主體與身份界定》,〔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等多樣化文化建設形式參與到集體事務中來,構建社會文化的主體性地位[2]王春光:《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社會文化主體性——以40年農村發展和減貧為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通過文化體系的建構為鄉村社會治理和公眾參與注入強有力的群眾基礎和情感基礎,為培育農村居民積極參與集體事務提供凝聚力和認同感的支持。打造強有力的鄉村共同體,更好地發揮鄉村社會多元主體的優勢,才能夠讓農村居民真正地成為鄉村的主人翁,真正地發揮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作用;才能夠讓鄉村的文化振興、產業振興、組織振興和人才振興形成合力,助力鄉村的全面振興和發展,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