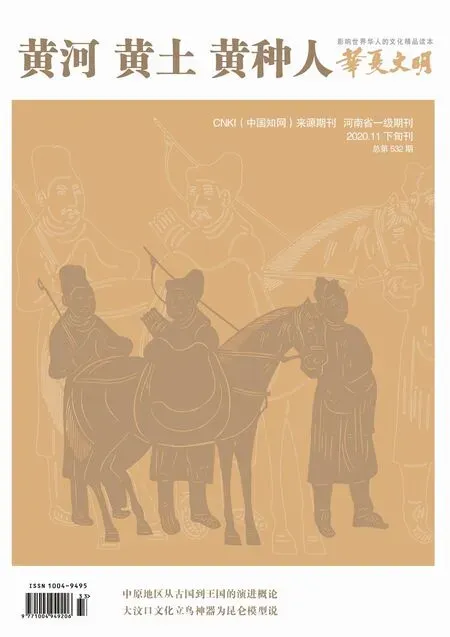中原地區從古國到王國的演進概論
□鄭杰祥
“古國”一詞是前輩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史學概念,其文化內涵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1],這種“政治實體”戴向明先生又稱之為“雛形國家”[2],它是人類歷史從原始社會步入文明時代重要的過渡階段。 這個歷史階段早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并提出各種名稱對此加以概括。 摩爾根將其稱為“部落聯合”階段,馬克思稱之為“部落融合”階段,塞維斯稱之為“酋邦”階段,蘇秉琦先生稱之為“古國時代”,筆者認為根據中國文獻記載的傳統稱呼,應稱之為“部族”或“部族方國”階段[3]。
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4]176,意即國家政權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志。 在我國具體歷史條件下,從部族方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就是夏王朝的建立。 夏王朝是我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具有中央王權性質的國家政權。 它的建立,標志著我國若干萬年的原始社會至此結束,數千年的文明時代自此開始,這是我國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夏王朝所創造的夏文化主體, 就是現今學術界所稱的二里頭文化,其中作為王都的二里頭遺址以其規模之大,文化內涵之豐富,在迄今發現的早于二里頭文化的所有文化遺存中既是前所未有的,在同時期的所有二里頭文化遺存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王都是國家政權的重要載體,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充分體現著我國歷史上的部族方國時代至此結束,夏王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王權性質的國家政權正式出現于世間。
夏王朝具有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世襲制的、政權和族權牢固結合的、崇尚禮制的、 相對統一的中央王權的基本特征,這些基本特征在部族方國時代已經迅速滋生和發展。 根據《史記》記載,我國歷史在夏王朝之前, 曾存在著黃帝至堯舜禹時代,也可稱之為以黃帝為首的“五帝時代”;從考古學上說,大約相當于中原地區(指狹義的中原地區即今河南地區)仰韶文化晚期和河南龍山文化時期,應當就是我們所稱的部族方國時代或五帝時代。 當時的中原地區,氣候溫和,土壤松軟而肥沃,極適宜于人們從事農業生產。 文獻記載與現有的考古資料證明,這里的人們早已從事以農業為主的生產勞動,過著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生活。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任職部族首領之時,他在經濟上首先率領群眾“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集解》引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即根據季節氣候的變化,種植五谷, 規劃四方土地以安定群眾生活。堯繼任首領之時,繼續“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正義》釋此說:堯根據季節變化,慎重地教導群眾春季種植粟谷, 夏季種植黍菽,秋季種植小麥,冬季勞動收獲。 《史記·夏本紀》記載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時,仍然“卑宮室致費于溝淢”,“令益予眾庶稻, 可種卑濕”,即自己的住室修建得十分簡陋,把剩余物資用來構筑灌溉莊稼的田間水渠,又令伯益向群眾發放稻種,在低洼的田野里種植稻米,發展農業生產。 《論語·憲問》也說:“禹、稷耕稼,而有天下。 ”即二人親自耕耘農田,種植莊稼,因而被廣大群眾擁戴為首領。 當時的人們重視農業,也被考古資料所證實。 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區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原始文化遺存中,出土的生產工具皆以農業生產工具為主,并在鄭州大河村、洛陽孫旗屯、澠池仰韶村、駐馬店楊莊、淅川下集等諸多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遺址中,都發現有粟和稻的遺物[5],充分說明當時的中原地區原始農業早已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
《史記·五帝本紀》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 ”說明從黃帝到舜禹,都是源于同一族屬,以后各自建立起自己的方國政治實體, 互相之間有著密切的血緣關系,從而為夏王朝及其以后的歷代王朝的世襲制奠定了根基。 《五帝本紀》又云:黃帝又“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帝舜時也是“眾民乃定,萬國為治”。 《左傳·哀公七年》也說:“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 ”“萬國”言其眾多之義,眾多方國之中,當也存在著不同血緣關系的政治實體。 古人早已認識到“男女同姓(結婚),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故《五帝本紀》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女”。 《正義》:“西陵, 國名也。 ”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其后人“帝嚳娶陳鋒氏女”等,西陵氏等都應屬于與黃帝族不同血緣關系的部族,也都建有自己的方國政治實體。 這些眾多的部族方國,占據著一方土地,對內作為血緣親族的族長,管理著同族的民眾,對上則類似于后世的地方官員, 在一定程度上聽從黃帝等首領的差遣,并時而聚會,共商“國事”,從而在黃帝所轄范圍內形成一個政權與族權相結合的相對統一政體。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社會財富有了越來越多的剩余,這些剩余財富逐漸被氏族、部落和部族各級首領所占有, 于是氏族成員之間出現了貧富分化,私有制由此而產生。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貧者卑賤,富者尊貴,整個社會開始分化為貧賤、富貴家族不同的群體。 為了保護和占有更多的財富, 富貴家族采取各種措施讓全社會承認這種分化的客觀現實,并使之制度化, 其中一種措施就是導致禮制的產生。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任職首領之時,命“伯夷,以汝為秩宗”。 “伯夷主禮,天下咸讓”。 《集解》引鄭玄曰:“主次秩尊卑”也,《正義》引孔安國云:“秩,序;宗,尊也。 ”由此可知, 伯夷所主管的禮制的實質就是維護等級制度下的平和社會, 既要人們遵守客觀存在的各階層富貴、 貧賤、 有尊有卑的社會秩序, 又要讓人們下對上要尊敬, 上對下要和睦,互相禮讓,使社會安定存在下去。
私有制的產生,激起人們的貪欲,一些富貴家族為了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開始把充分民主的為全民服務的部族會務,逐漸改造成為強權機構, 并建立自己的親兵衛隊,用來對內保衛安全,對外掠奪強取。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早在黃帝時代已是“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其中“炎帝欲侵凌諸侯”,又云“而蚩尤最為暴”。 《新唐書·黨項傳》記載當時處于部族方國階段的黨項族也是“以姓別為部,一姓又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而拓跋氏最強……然好為盜,更相剽奪”。 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全,于是防衛性環壕、城堡開始產生。 《史記·封禪書》云:“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 ”《事物紀原》引《黃帝內傳》云:“帝既殺蚩尤,因之筑城闕。”《世本·作篇》云:“鯀筑城。”《初學記》引《吳越春秋》云:“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 ”《太平御覽》卷一九二引《博物志》云:“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 ”考古資料證明,在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的中原地區確已開始出現多座城址。 中原地區的城址是在環壕聚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早在裴李崗文化時期,人們已開始在自己的聚落周圍挖筑壕溝,以防御水災與野獸的侵襲, 但逐漸認識到把挖出的土堆積一旁,也可起到防御作用, 于是加工建起了圍墻,同時也逐漸質變為以防御外敵侵犯為主的城堡。 到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工作者仍在河南的淅川溝灣,洛陽王灣,鞏義雙槐樹,滎陽青臺、滎陽汪溝,鄭州大河村等遺址發現有環壕聚落遺存[6]44。 20 世紀90 年代,在鄭州市西北的西山, 發現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城址,這是在中原地區迄今所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座古城。 城址呈不規則形,南部已被破壞, 城墻坐落在挖有倒梯形的基槽之上,殘長260 余米,寬3~5 米,高1.7~2.5 米,墻體采用方塊版筑法層層夯打而成。 城墻外有壕溝環繞, 壕溝以內全城面積3 萬余平方米。西城墻和北城墻發現有城門,門寬10 余米。北城門外側筑有東西向護門墻,護門墻以南發現有道路通向城內。 城內西北部發現一座呈扇面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東西長約14米,南北寬約8 米。 基址北側有一座數百平方米的廣場, 這里應是一處部族首領的住地。 城內東南部發現多座陶窯遺址,應是當時的制陶手工業作坊遺跡。 城外西郊和北郊發現有當時的墓地[7]。 20 世紀初,在淅川縣龍山崗也發現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8]。進入河南龍山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現已發現了10 余座城址,從南而北計有淮陽平糧臺、郾城郝家臺、平頂山蒲城店、新鄭人和寨、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溫縣徐堡、博愛西金城、輝縣孟莊、濮陽高城和戚城、安陽后崗和柴庫等城堡遺址[6]15-16,這些城址繼承了仰韶文化時期的筑城技術, 多是先挖基槽, 在奠實基槽之上層層夯筑高起的城墻。城址周圍發現有同一時期的各類遺址,形成該城的中心區位。 城址多呈方形,城墻開有城門,墻外挖有城壕,壕間留有通道,便于人們出入。 城內發現有大小不同的房基、窖藏灰坑、墓葬及各類遺物等。 以登封王城崗城址為例:該城位于嵩山南麓、潁河以北,東側有一條穿過嵩山的南北大道, 直達豫南地區。 考古工作者首先在這里發現一座面積約1 萬平方米的小城, 其后又在小城周圍發現一座面積約34 萬平方米的大城, 兩城略有早晚,但皆屬于龍山文化晚期,這是中原地區迄今所發現的最大一座龍山文化城址。 城址呈長方形,其中小城建筑是先挖有倒梯形基槽,在基槽之上層層夯筑建起城墻;大城則是平地起建,即在生土之上或遇有文化層則挖去熟土之后層層夯筑建起墻體。 城外挖有城壕,只是南面和東面為自然河流潁河與五渡河水所代替。 小城內中西部發現有夯土建筑基址, 基址下面發現埋有人骨的奠基坑,顯然是一處部族首領的居地。 居地周圍發現有眾多灰坑,有些灰坑可能是一般平民的居住房基。 城址內出土有陶器、 骨器、蚌器、玉器與殘銅片等[9],玉器、銅器應是部族首領使用的禮器。 淮陽平糧臺城址是中原地區迄今所發現的一座最為規整的龍山文化城址,該城位于黃淮平原之上,面積約5 萬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北偏東6°,城墻首先用褐色土夯筑墻壁, 然后在墻壁外側堆土,層層夯筑成寬厚的城墻,墻外有壕溝。 南北城墻中段開有城門,南門兩側筑有用土坯砌成的門衛房,門道路土下面埋有陶制的排水管道,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創新性設施。 城內東側南部發現有房基, 其中F4 號房基是一座用土坯砌墻的高臺建筑,應是一座部族首領的住地。該房基近旁H15 灰坑內發現有銅渣, 附近可能有冶煉制作銅器的作坊,城內東南、東北和西南部發現有陶窯,應是當時的手工業場地[10]。
城堡是凸起的防御建筑,是古代最先進的防御體系。 龍山文化時期是中原地區出現的第一次建城高潮, 雖然現已發現的10 余座城址實際上遠不止這些,但已是仰韶文化時期的數倍。 城堡群的出現,反映著當時的敵對集團攻伐不已,征戰連綿,整個社會形成混亂局面。 社會混亂影響著各地人們之間的互相交流,破壞著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社會各個階層的不安。 為安定社會秩序,以黃帝為首的部族集團努力削平這些內亂。 《史記·五帝本紀》云:當時“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 ”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從而使社會恢復到安定局面。 形勢發展到舜的時期,舜對原有的部族議事會加以進一步改造,各位部落首領分工任職,統一服從舜的調遣;舜將所轄各地劃為行政區域,由當地強勢部族首領擔任行政長官。 這些首領盡職盡責,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史記·五帝本紀》云:舜任“皋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谷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 不失厥宜……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 意即分工任職的皋陶主管法律,執法公平,人民佩服;伯夷主管禮儀,各階層互相謙讓;垂主管工程,工匠們皆做出成績;伯益主管山澤,山澤得到開發;棄主管農業,莊稼茂盛,五谷豐收;契主管教化,大眾和睦相處;龍主管外事,遠地方國首領皆來請服;各地行政首長也認真負責,無人違規。 其中禹的功勞最大,他負責治理洪水,安定社會,分別各地行政區劃,各地向中央繳納的賦稅合情合理。 于是整個社會出現相對穩定統一,舜乃預先推薦禹繼承自己的大位,各族首領對此皆衷心擁護,無有異議。 禹繼承大位之后, 繼續加強以自己為主的部族行政權力,《大戴禮記·五帝德》云:禹“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意即禹任命皋陶、伯益協助自己,率領軍隊討伐無道無德的人們。 于是各地的人們,都來尊敬服從于禹。 再者,正如恩格斯所說:“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要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4]170-171舜、禹的時候又設立刑獄等強制機關,《新語·道基》又云:“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 ”意即皋陶作為法官開始建立監獄, 懲罰罪犯;有賞有罰,以此辨別好壞是非,并檢出邪惡,消除淫亂, 使廣大群眾都敬畏法律的威嚴。《史記·夏本紀》又云:皋陶“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意即皋陶命令群眾皆以禹的言行為榜樣,如有違背,刑罰處治。 據此可知,舜、禹時期軍隊的建立、法律機構的設置以及皋陶、伯益等成群官吏的出現,完全改變了部族議事會的性質,造就了“雛形國家”的具體形態。 禹更以此為基礎,根據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 開始打破傳統的禪讓制,讓自己的兒子啟繼承首領大位, 秦嘉謨輯補《世本·紀》云:“禹崩,子帝啟立。 ”《帝王世紀》云:禹“始納涂山氏之女,生子啟即位”。《孟子·萬章上》又云:“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 朝覲頌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曰:‘吾君之子也。’……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史記·夏本紀》又云:禹“以天下授益……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 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啟在眾人擁戴之下,登上王位,繼承父業,開拓創新,以自己的賢明才干,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削平有扈氏叛亂,開啟后世歷代王朝世襲制的先河,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相對統一的中央王權性質的夏王朝國家政權,推動著我國古代社會進入新的文明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