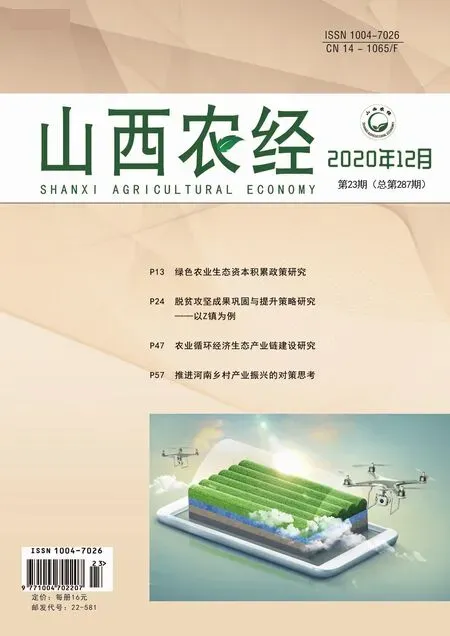“十三五”時期山西省農民收入變化情況及進一步增收的對策建議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1 “十三五”期間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現狀
1.1 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情況
由表1 可以看出,2016—2019 年,山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0 082 元增加到12 902 元,增加了2 820 元,名義增長28.0%,年均增長8.57%。2020 年上半年為5 797 元,同比增長3.1%,比2019 年同期增加173 元,增幅有所回落。工資性收入平穩增長,增速逐漸加快(2020 年上半年增速大幅回落),由2016 年的增長5.7%提高到2019 年的增長6.3%。2020 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增長速度大比例下降,同比下降至0.3%。經營凈收入增長較快,由2016 年的2 730 元增加到2019 年的3 396 元,增加666 元,增長24.4%,年均增長7.55%。財產凈收入同步增長(2020 年上半年降幅明顯),由2016 年的149 元增加到2019 年的210 元,增長了40.9%,2020 年上半年則比上年下降11.7%。轉移凈收入保持穩定增長,2019 年達到3 198 元,比2016 年增加1 199 元,增長59.98%,年均增長16.96%[1-2]。
1.2 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逐步拉大,增速升中有降
“十三五”期間,山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的比值持續下降,從2016 的81.5%下降到2019 年的80.5%,2020 年上半年降至71.8%。2014 年以來,山西省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三五”期間,隨著山西省政治、經濟環境逐步向好,到2018 年增速比全國快0.1 個百分點,2019 年比全國快0.19 個百分點。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山西省農民收入增速(3.1%)急速下降。
1.3 從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邊5 省(自治區)橫向比較來看,山西省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高于陜西省,與其他省份差距較大
據統計,2016—2019 年,在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邊5 省(自治區)中,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除略高于陜西省外,均低于其他省份,位列第8 位,2020年上半年退居第9 位。2019—2020 年上半年,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邊5 省(自治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見表2。

表1 2010—2020 年期間山西省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源和所占比重
與中部6 省相比,山西省(9.80%)的增速慢于安徽省(10.15%),快于湖南省(9.24%)、湖北省(9.44%)、江西省(9.24%)、河南省(9.64%)。與周邊5 省(自治區)相比,山西省的增速慢于內蒙古自治區(10.72%)、陜西省(9.93%),快于河北省(9.56%)、河南省(9.64%)。2020 年上半年,山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797 元,與排在第1 位的安徽省相差2 884 元,差距進一步拉大,且增速全面放緩。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大的湖北省外,山西省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其他中部及周邊省(自治區)。
1.4 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十三五”期間城鄉收入比總體好于全國平均水平
2016—2019 年,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為17 270 元、18 344 元、19 285 元、20 360 元;2020 年上半年為10 305 元。從城鄉居民收入比來看,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由2016 年的2.71 下降到2019 年的2.58,下降了0.13;2020 年上半年,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比反彈至2.78,比全國高0.1。總體來看,“十三五”期間,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比好于全國平均水平。
2 山西省農民增收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2.1 經營性收入增長影響因素明顯
一是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山西省土壤貧瘠、水資源短缺、自然災害時有發生,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弱[3]。
二是農業生產成本高但收益低。山西省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仍然以小農戶家庭經營模式為主,戶均地面積小,生產效率非常低,農業資源無法實現最優配置,農業生產成本及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嚴重擠占了農民的收入空間,單靠種地增收很難。
三是新品種、新技術推廣應用困難。隨著外出打工農民不斷增加,“空心村”越來越多,農民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新品種、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困難,經營性收入增長乏力。
四是經常發生農產品沒有銷路的現象。由于產銷市場信息渠道不暢,供需錯配、產銷脫節,農產品賣難時有發生[4-5]。
五是非農經營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大。非農收入中,鄉村旅游及工商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由于疫情的沖擊,許多農家樂停辦,工商業或多或少受到影響,相關從業農戶的非農經營收入均下降。
2.2 工資性收入增速下滑
一方面,企業停工、停產對農民外出務工影響大。受疫情影響,山西省農民工本地務工和外地務工返崗受阻,多數勞動密集型服務產業無法按時復工復產,直接影響到2020 年的農民收入。
另一方面,山西省農民文化水平、非農生產技能和綜合素質偏低,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較為陳舊保守,難以適應新業態崗位的快速變化,農民崗位層次低,就業不穩定,收入少。
2.3 財產性收入增長瓶頸難破
一是農村房產和農民土地等資產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為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收入,來源渠道單一,土地資產價值得不到顯現。
二是山西省部分村辦企業、合作社等集體經濟普遍經營不善,經濟效益低下,農戶獲得的股份分紅收入較少[6]。
2.4 轉移性收入增長后勁不足
一方面,農村低收入人口主要依賴于轉移性收入,雖然目前山西省貧困縣已全部摘帽,但是大部分脫貧人口仍然收入較低。隨著脫貧攻堅的完成,政府各項政策補貼速度以及力度將會逐漸減弱,財政投入也由集中式投入轉入常態化投入,轉移性收入增長不容樂觀。

表2 2019—2020 年上半年中部6 省及山西省周邊5 省(自治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比較
另一方面,山西省外出務工農民需要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費用,食品、房租以及子女教育費用支出較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轉移性收入。
3 對策建議
3.1 挖掘農業潛力,增加農民經營性收入
全面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出山西省農產品“特、精、優”發展道路,促進三產融合,向第二、三產業要收益。進一步穩定農資價格,提高農業生產率,在農業經營成本上尋求增加收入的空間,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7-8]。
3.2 加大勞務培訓力度,提升工資性的收入比重
山西省連續舉辦了多次勞務培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已經形成勞務品牌。下一步要注重提升勞務培訓的質量和效果,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有針對性地加強新興產業領域和新型服務領域的培訓力度。
3.3 釋放改革紅利,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
想要切實提高農民收入,必須把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放在突出位置,有序推進農村宅基地、土地以及集體產權制度的政策改革,逐漸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應推動權力下放和基層先行先試,推動發達城市和地區的資金以及資源要素向農村流動,激活農村內在動力[9]。
3.4 分類施策的扶持措施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對農業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考慮到不同農業主體不同的利益訴求,應當對各群體進行區別對待、分類施策,有針對性地采取幫扶政策。重點做好對農村雙創工作的支持力度,積極出臺并完善符合當地特色且針對返鄉農民創業的配套服務體系,實現農民在家門口就業,拓寬增收渠道。同時,對生活條件比較困難的農民家庭做好援助工作,防止因疫返貧現象的發生[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