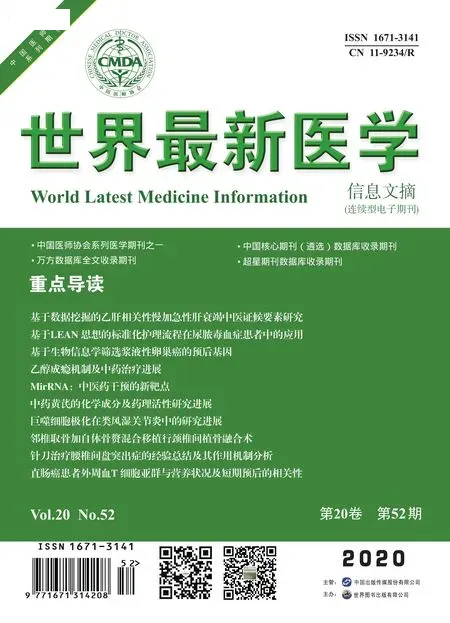膽管擴張癥的病因及發(fā)病機制研究進展
張小冬,楊景瑞,周江,王璐,張乾,王家興,劉少杰,溫波,任建軍通訊作者)
(內(nèi)蒙古醫(yī)科大學附屬醫(yī)院,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 引言
膽管擴張癥(biliary dilatation,BD)也被稱為膽管囊腫,是一種少見的膽管原發(fā)性病變[1],主要表現(xiàn)為涉及膽管,包括肝內(nèi)膽管和肝外膽管在內(nèi),發(fā)生單發(fā)或多發(fā)性擴張[2-4],擴張膽管的最大內(nèi)徑大于正常人同年齡組上限[5]。腹痛、上腹部包塊和黃疸為BD的臨床三聯(lián)征,但三者同時出現(xiàn)較為少見(約20%~30%)[6]。患者以女性居多,大約是男性的3倍[7]。10%到30%的BD會發(fā)展成惡性腫瘤[8-10],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因此,預防BD的發(fā)生至關重要。目前,BD的病因及發(fā)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主要有胰膽管合流異常、胚胎發(fā)育異常、胃腸道神經(jīng)-肌肉內(nèi)分泌異常、遺傳學因素、膽管上皮異常增殖等學說。本文就國內(nèi)外現(xiàn)有的BD病因及發(fā)病機制研究進展予以總結(jié)。
1 胰膽管合流異常學說
胰膽管異常合流學說是目前比較公認的致病學說。胰膽管合流異常(pancreaticobiliary maljunction,PBM)是指胰腺和膽管在解剖上連接在十二指腸壁外,胰管和膽管產(chǎn)生更長的共同通道,十二指腸乳頭肌不能對連接處產(chǎn)生作用,隨著兩個管腔內(nèi)壓力的變化,胰液和膽汁之間發(fā)生反流,產(chǎn)生各種病理損傷[11]。PBM最早是由Kozumi等[12]于1916年在尸檢中發(fā)現(xiàn)并報道。1969年,Babbitt等[13]通過胰膽管造影在先天性膽管擴張患者中證實了胰膽管合流異常,首次提出了PBM是BD的病因?qū)W說,他認為,胰膽管合流異常時胰液反流對膽管壁持續(xù)的刺激作用導致膽總管遠端水腫,最終形成纖維化而造成狹窄,另一方面,胰酶的消化作用破壞了膽管壁的結(jié)構,導致膽管局部擴張。據(jù)報道,44%~91%的BD患者中存在PBM[14]。正常情況下,胰管內(nèi)的最大壓力為3-5kPa,而膽管內(nèi)的壓力為2.5-3.0kPa[15],胰管內(nèi)壓力往往大于膽管內(nèi)壓力,PBM發(fā)生時,由于壓力梯度的作用,胰液往往會反流到膽管中,Sugiyama等[16]對PBM患者的膽汁成分進行檢測,發(fā)現(xiàn)了膽汁中的高胰淀粉酶現(xiàn)象。胰液反流到膽管中發(fā)生各種病理生理變化,Kaneko等[17-18]認為,胰腺分泌胰蛋白酶原和胰石蛋白(lithostathine),PBM發(fā)生時,這兩種物質(zhì)進入膽管,胰蛋白酶原通過未知的機制被激活為胰蛋白酶,胰蛋白酶將原本可溶性的胰石蛋白轉(zhuǎn)化為不可溶解的形式,這種蛋白質(zhì)聚集形成蛋白栓,蛋白栓阻塞在遠端膽管狹窄部位或胰膽管匯合口,導致膽管內(nèi)壓力升高,形成擴張。部分學者制作PBM的動物模型,觀察到胰液對膽道壁有明顯的破壞作用,反流的胰液刺激膽管上皮,產(chǎn)生一系列慢性炎癥反應。吳宙光[19]對收治的BD患兒膽管組織和血清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IL-32表達上調(diào),IL-32作為一種前炎癥細胞因子,它的上調(diào)在BD患者的炎癥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有著重要的意義。Sang等[20]系統(tǒng)地評估了擴張膽管中平滑肌的分布,約75%的病例觀察到無肌或散在肌纖維作為最常見的兩種平滑肌分布模式,他們認為膽管反復發(fā)生慢性炎癥和傷口愈合后,部分膽管的平滑肌肌束顯著丟失,并被纖維組織取代,不均勻分布的平滑肌束收縮時,某段膽管粗大的肌纖維可能導致暫時的、反復的功能性梗阻,從而導致腔內(nèi)壓力增加、膽管壁損傷和最終的擴張形成。另外,胰液對膽管壁長期的破壞作用,也可能使更多地暴露在胰液中的下段膽管纖維化甚至狹窄,擴張膽管遠端的最小直徑與近端的最大直徑之間呈負相關[21],此外,Diao M等[22]通過壓力傳感器行術中膽總管腔內(nèi)壓力檢測,發(fā)現(xiàn)遠端狹窄呈囊狀擴張的BD患者膽總管腔內(nèi)壓力往往會更高。Kaneko等[23]使用6例存在PBM的BD患兒和4例正常兒童的膽囊上皮細胞進行全基因表達分析,經(jīng)實驗驗證,發(fā)現(xiàn)長鏈非編碼RNA——UCA1和Bcl2修飾因子——BMF在BD患兒中均呈高表達,認為UCA1和BMF在BD患者中差異性表達是胰膽管連接異常的病理生理因素伴隨的分子學改變。PBM往往伴隨膽管擴張,但是隨著無膽管擴張的PBM患者以及無PBM的膽管擴張患者被檢出,以及基于動物和臨床的研究結(jié)果,PBM作為BD的病因?qū)W說受到了質(zhì)疑[24-26],有文獻統(tǒng)計,近三分之一的 PBM患者并沒有發(fā)生膽管擴張的現(xiàn)象[27]。Tahar等[28]應用20只迷你豬(minipigs)制作PBM模型,模型在術后5個月經(jīng)T管造影未見肝內(nèi)外膽管擴張,一直到術后20個月也未觀察到膽管擴張性損害。此外,對于在出生之前診斷的BD病例來講,此時胰腺并不具有分泌胰液的功能,胰液也就不可能逆流到膽管內(nèi)損傷黏膜,這就說明胰液反流不是導致BD的根本原因,與胰膽管合流異常學說相矛盾[29],因此該學說仍存在許多有爭議。
2 胚胎發(fā)育異常學說
Yotsuyanagi等[30]認為BD是由于早期胚胎膽管空泡化不均所致:在胚胎發(fā)育原始階段,膽總管為一個無腔的固體結(jié)構,此時如果某段膽管細胞產(chǎn)生更強烈的增殖,這段膽管就會隨著發(fā)育的差異性增殖及管腔內(nèi)的壓力不均勻變化形成局部擴張。這個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顯得很合理,但是很難取得合適的標本設計相應實驗進行驗證。Benhidjeb等[31]在1996年報道了一例在妊娠29周時經(jīng)常規(guī)超聲檢查發(fā)現(xiàn)胎兒膽總管囊腫,囊腫通過膽囊管與膽囊相連,最大直徑為18mm,這一病變在出生后不久由超聲檢查得到證實,14周后囊腫直徑增大至34mm,16周患兒接受腹部手術,對囊腫標本行組織學檢查,示纖維組織壁增厚,有壞死區(qū),但術中抽吸囊腫內(nèi)液體,行細菌學和化學檢查,發(fā)現(xiàn)囊腫內(nèi)液體無菌,并且未查到淀粉酶成分,經(jīng)膽管造影顯示胰膽管連接處無異常,Benhidjeb等證明了BD的發(fā)生可起源于胚胎期,這種起源于胚胎期的BD,一定程度上與胰膽管異常合流導致BD的學說相悖。
3 胃腸道神經(jīng)-肌肉內(nèi)分泌學說
Shallow等[32]于1943年發(fā)現(xiàn)BD患者膽管壁上的神經(jīng)節(jié)細胞較正常明顯減少,且存在缺陷,這種改變類似于巨結(jié)腸,他以此作為BD的病因。 Kusunoki等[33]通過對正常膽總管和擴張膽總管進行研究,也發(fā)現(xiàn)了囊腫遠端膽總管壁內(nèi)神經(jīng)節(jié)細胞明顯缺少這一現(xiàn)象。Hall[34]等發(fā)現(xiàn)BD患者膽管壁上的神經(jīng)分布減少程度與患者的臨床癥狀嚴重程度及囊腫的體積大小成正比關系。卡哈爾間質(zhì)細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ICC)是消化道慢波活動的起搏細胞及基本電節(jié)律的主要傳播細胞,參與胃腸道神經(jīng)信息的傳遞以及動力學改變[35]。段建飛[36]通過取BD患者的膽總管和正常膽總管組織標本進行實驗對比,發(fā)現(xiàn)卡哈爾間質(zhì)細胞在BD患者中表達更低,另一方面他用突觸素(Synaptophysin, SY)標記神經(jīng)纖維和突觸,發(fā)現(xiàn)BD患者膽管中神經(jīng)纖維和突觸表達量更低。Rebecca R. J報道了一例編碼腸平滑肌肌動蛋白γ2的基因(ACTG2)的致病性突變,導致原發(fā)性內(nèi)臟肌病的病例,患者合并慢性腸道假性梗阻,肥厚性幽門梗阻以及膽總管囊腫。徐偉立等[37]發(fā)現(xiàn)膽總管遠端狹窄段腸神經(jīng)節(jié)細胞、神經(jīng)纖維、卡哈爾間質(zhì)細胞的分布以及神經(jīng)-肌肉傳導均存在異常,他們認為胚胎發(fā)育期不明原因?qū)е铝四c神經(jīng)系統(tǒng)發(fā)育異常,使平滑肌舒縮功能失調(diào),長期處于痙攣狀態(tài),遠端狹窄,最終導致了BD的發(fā)生。但是這一理論并不能解釋遠端非狹窄型BD患者的發(fā)病機制。目前這一學說被部分學者認可,但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4 遺傳學研究
BD患者的男女比約為1:4,有部分學者認為BD是由X性染色體顯性遺傳決定其特征。石田等[38]綜合日本報道的3組家族性先天性膽管擴張癥,分別為:父女、母女,姐妹,并且在三組中同樣地發(fā)現(xiàn)PBM的存在。BD中肝內(nèi)膽管先天性擴張被稱為Caroli病,已被廣泛認知為一種罕見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由位于染色體6p12的PKHD1基因變異所致[39]。王小林等[40]檢測了30例BD的擴張膽管組織標本 ,其中有4例發(fā)生點突變,DNA測序發(fā)現(xiàn)K-ras基因點突變發(fā)生在第12位密碼子,形式為甘氨酸(GGT)——天冬氨酸(GAT),他們所做的研究中K-ras基因突變率為13.3%,同樣地,國外也有類似的報道,突變率為11.1%-33.3%[41-42]。Kotalova R報道了1例17q12染色體序列重復的BD患者[43]。然而,Schweizer等[44]對患有BD的1對母女進行了染色體分析,結(jié)果中并未發(fā)現(xiàn)染色體的變異。目前來看,想要進一步評價基因的遺傳變異因素與BD之間的關系,尚需收集更多類似的家族病例,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5 膽管上皮異常增殖學說
膽管上皮細胞的過度增生是引起膽管擴張的主要機制之一[45-46]。K-ras基因是一種Ras原癌基因,P21是一種抑癌基因,兩者編碼的蛋白質(zhì)均參與細胞的G1-S 期之間的周期調(diào)控,當K-ras蛋白升高,P21蛋白降低時,往往會導致細胞增殖活性加強,甚至產(chǎn)生惡性增殖[47-48]。周良等[49]對比擴張的膽管組織和正常膽管組織標本發(fā)現(xiàn)BD患者P21蛋白的陽性率降低,K-ras蛋白的陽性率增高,膽管上皮細胞發(fā)生異常增殖。轉(zhuǎn)化生長因子β1(TGF-β1)和堿性成纖維生長因子(bFGF)在組織細胞的正常生長、調(diào)節(jié)細胞的增殖遷移、細胞外基質(zhì)形成及促進損傷修復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50]。李斌德[51]等發(fā)現(xiàn)BD患者膽管組織中TGF-β1和bFGF表達量明顯增高,且與膽管粘膜細胞脫落程度,囊壁增生、肥厚程度,炎癥細胞浸潤程度密切相關,充分證明了兩者參與了膽管擴張的形成過程。另外,增殖細胞核抗原Ki-67作為細胞周期標志物在BD患者膽管、膽囊粘膜組織中也呈現(xiàn)高表達[52]。端粒長度縮短表明細胞周期加快,BD患者中同樣檢測到了這一結(jié)果[53]。microRNA-200家族通過轉(zhuǎn)錄抑制因子ZEB1和ZEB2來抑制上皮向間充質(zhì)轉(zhuǎn)化(EMT)[54-55]。當microRNA-200下調(diào)時,上皮細胞間黏附力降低,并使得部分上皮細胞獲得成纖維細胞樣特性[56]。有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57]:BD的發(fā)病機制可能與miR-200家族沉默有關,通過ZEB1介導的EMT激活發(fā)揮作用。PCNA是DNA聚合酶δ的輔助蛋白,存在于細胞核中,與DNA復制及細胞的增殖周期密切相關[58],董蒨等[59]在BD患者膽管組織中檢測出了PCNA的高表達,說明膽管異常擴張時,已經(jīng)有了膽管細胞的高增殖表現(xiàn)。欒明月等[60]通過PCK大鼠對BD中的一型Caroli病進行研究分析,發(fā)現(xiàn)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VEGF)在PCK大鼠膽管上皮細胞中呈高表達,VEGF可增強PCK大鼠膽管上皮細胞活力,提高內(nèi)皮細胞遷移能力和管腔形成能力,他們認為VEGF不僅能直接誘導膽管上皮細胞增殖,而且能促進血管內(nèi)皮細胞的增殖和遷移,最終導致新生血管形成,新生的血管通過旁分泌作用,再次促進膽管上皮細胞增殖,最終導致膽管擴張。
6 小結(jié)
綜上所述,BD的病因及發(fā)病機制尚未明確,存在多種學說,各學說之間并非完全獨立,存在著多種聯(lián)系。目前來看,大多數(shù)學者從解剖學角度對BD的病因及發(fā)病機制進行了闡述,而關于BD的分子學發(fā)病機制研究在國內(nèi)外的報道中相對較少,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