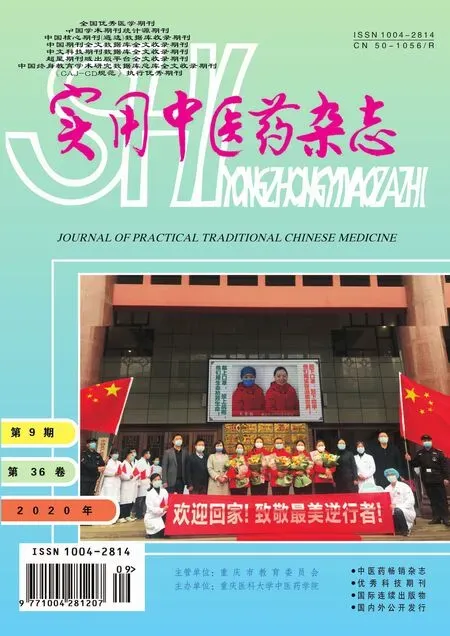汪受傳治療咳嗽變異性哮喘經驗
薛 飛,汪受傳
(山東省煙臺市中醫醫院萊山扶正堂中醫經典門診,山東 煙臺 264000)
咳嗽變異性哮喘又名過敏性咳嗽,屬于不典型、隱匿性哮喘。臨床以干咳、嗆咳、少痰甚至無痰為主要臨床特征,常在夜間和(或)清晨發作,運動、遇冷空氣后咳嗽加重。汪受傳認為本病當屬“風咳”范疇。“風咳”之“風”主要指稟受于先天、潛伏于體內、受外風誘導而發病的“伏風”。“伏風潛伏、外風引動”為病機。發作期治以宣肺、祛風、止咳,自創經驗方金敏湯加減治療。緩解期根據患兒體質差異,治以補肺、益氣、御風,用玉屏風散加味治療。
1 疾病認識
古代醫家對本病的認識。咳嗽變異性哮喘中醫古籍雖然無相同病名,但有相關類似的描述,如“風咳、風痰”等。如《禮記·月令》說:“季夏行春令,則谷實鮮落,國多風咳,民乃遷徙。”[1]首次提出了“風咳”之名。又如《諸病源候論·咳嗽諸病》說:“一曰風咳,語因咳,言不得竟是也。”[2]論述了“風咳”的相關臨床特點。對于治療,《臨證指南醫案·咳嗽》提出“辛以散邪,佐微苦以降氣……”[3]。《雜病源流犀燭·咳嗽哮喘源流》說:“一曰風嗽,風乘肺也,其脈浮,必兼鼻塞,流涕聲重,口干喉癢,憎寒發熱,自汗惡風,煩躁,語未竟自咳,宜款冬花散、金沸草散。”[4]
現代醫家的認識。王烈將干咳少痰,反復發作的咳嗽,稱為“哮咳”[5]。晁恩祥認為本病以少痰、干咳為特征,命名為“干咳”、“嗆咳”、“風咳”等[6-7]。徐榮謙認為本病具有“善行而數變”之風證的特點,臨床以“宣肺、化痰、止咳”為治法,療效顯著[8]。張驃認為本病病機為“風、痰相合”為病,且以“風邪”為主[9]。洪佳璇等認為本病反復發作,易導致痰氣互結,瘀血內生。血瘀是關鍵要素之一[10]。陳培英強調“補腎”之法治療本病的重要性,臨床自擬“補腎化痰湯”臨床療效確切[11]。多數醫家以虛實論治本病,分別給予宣肺、化痰、健脾、養肺等治法。
2 治療思路
伏風潛伏、外風引動。汪教授所言之“伏風”,源于先天之稟賦,平時深潛于體內無異于平人,但當有外邪(風邪)侵襲,或者異氣、異味、異物所引動,則隨之被觸發而發病,稱之為“伏風”。“伏風”稟賦于先天,平時深伏于內,難以疏散,不易消除,而成諸風疾之主因。對多種他人接觸無異之氣、味、物等,一有所觸則宿疾隨即引發。諸如鼻涕、鼻癢、清嗓、咳嗽、痰少、喘息、哮鳴、膚癢等,皆為“風”之特征表現。因此可以歸于“風病”范疇。引發宿疾的因素很多,如感受風邪、辛辣食物、刺激性氣味、油漆、花粉、動物皮毛等,唯有“風邪”為要。此即“外風引動伏風”而發病之主要病機。說明這類患兒自有其異于常人的特應性發病體質。
祛風宣肺,止咳化痰。風咳發作期用金敏湯。藥用蜜炙麻黃3g,蜜炙紫菀6g,天冬10g,桑白皮10g,五味子6g,炙烏梅6g,膽南星6g,黃芩10g,炙甘草3g。方中炙麻黃解表宣肺、止咳平喘,蜜紫菀清肺化痰止咳,膽南星逐風化痰,天冬生津養肺,黃芩、桑白皮解熱清肺化痰,炙烏梅、五味子斂肺生津。諸藥合用,共奏祛風宣肺、止咳化痰之效。
固表御風,未發先防。本病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反復發作,纏綿難愈。因此緩解期仍需要堅持治療,以改善其“異稟”之體,同時應注意預防外感,清淡飲食,避免再次觸及過敏原等,同時配合中藥以固肺、補氣、堅表。多以玉屏風散加味治療。
3 驗案舉隅
李某,男,15歲,2018年9月1日初診。2個月前因感冒后出現干咳,少痰難咯,伴鼻塞,咽痛,大便干,2~3日一行。舌質紅苔薄白,脈浮數。口服清宣止咳顆粒、肺力咳口服液、丙卡特羅等半月余效果不佳,仍反復咳嗽,鼻塞。胸片示雙肺紋理增重。中醫診斷為風咳,風束肺絡證。治以祛風宣肺,潤肺止咳。藥用炙麻黃9g,蜜紫菀9g,天冬15g,桑白皮12g,桔梗6g,蒼耳子6g,五味子9g,炙烏梅9g,膽南星9g,黃芩9g,炙甘草6g。10劑,水煎,分3次飯后溫服。服藥后鼻塞好轉,咳嗽減輕,繼續調理中。
孫某,女,7歲,2017年12月16日初診。確診咳嗽變異性哮喘病史2年,每年立秋前后發作或加重,經中、西醫治療效果不佳。無明顯誘發因素出現咳嗽甚至喘息,受涼或劇烈運動后加重。證屬風咳,肺脾氣虛證。治以益氣補肺,健脾御風。方用玉屏風散加味。黨參10g,清半夏10g,茯苓12g,炒白術12g,僵蠶9g,蟬蛻9g,防風9g,黃芪20g,大棗6g,炙甘草6g。10劑,水煎,分2次飯后溫服。治療后諸癥好轉,劇烈活動后亦無明顯咳嗽、喘息。上方繼續調理10天,并配合口服玉屏風散顆粒以預防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