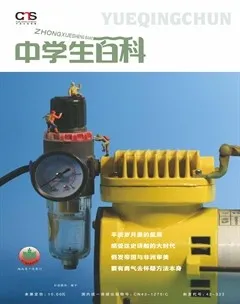假發帝國與非洲審美
三木
1
在非洲這幾年,最令我頭疼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的頭。嗯,我的意思是說理發。
盡管在非洲理發館遍布大街小巷,幾乎是除了啤酒館之外的第二存在,但是我從來沒有勇氣走進去。因此在非洲這些年,頭發都是我自己打理的。
為什么呢?因為我實在是不敢相信他們的理發師。
并不是出于嫌棄或者說是瞧不上,而是源自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如果行走在非洲的街頭,你會發現十個非洲的小伙子其中有九個理著一模一樣的光頭。
顯然,當地的理發師對剃成光頭以外的男性發型是比較陌生的。
不過,這不能怪理發師,也不能怪非洲的審美。非洲人長著一頭細密卷曲、貼著頭皮生長的頭發,這種頭發長長了以后會蓬亂得跟雞窩一樣,很不好打理。所以當地的男性基本上會剃光頭,女性則會扎小辮,或者用假發來挽救自己的花容月貌。
對于中國人來說,假發可能在生活當中是一種比較少見到的,又或者說是在一些特別的場合才偶爾見到的東西,其適用人群也只是少數。
假發之于非洲女性,卻如同口紅之于中國女性。
現在的中國姑娘如果要出門約會,口紅是標配。在非洲也是一樣,妹子出門肯定是戴著假發的,沒戴的話,要么說明你們關系足夠親近,要么就是她根本不想見你。
2
在非洲,家里沒有三四頂假發的女人不好意思說自己懂生活;沒有定時去理發店換一套假發編的新發型只能說明錢包過于窘迫。當一個女生推遲了和我的約會,其理由往往是勞神費時的編發工作還沒弄完。
假發可以說是啤酒之外的第二剛需,理發店分布密度僅次于小酒館的事實就能證明這一論斷。
非洲女性對假發的喜好,催生出一個龐大的假發市場——2017年,非洲的發制品消費額達到了43億美元以上。我在法蘭西城所認識的每一位女性都深度參與進了這個數十億美元級的大生意中。
我的女性朋友小R,只要我見她次數間隔一周以上,她就會換另一頂頭發出現在我面前。比如說今天是個直發,下回換個卷發;今天是黑色頭發,下回換個金色頭發;今天是長發,下回換個短發;今天扎個小辮,下回換個爆炸頭。以至于有時候我一下子都認不出她來。
其他我常能見到的姑娘也是不時出現一夜“長出”一頭長辮的情況。像她們這樣的年輕姑娘,一般的發式是將假發接在真發上,然后貼著頭皮編成或粗或細的小辮。小姑娘則會在小辮上串上各種彩色的珠子和其他小發飾,走起路來一顛一顛的,甚是可愛。
除了編成小辮的假發,也有現成的發套,多半是大波浪或者直發。大波浪尚顯自然,而廉價的直發則常常會一綹一綹地聚在一起,同時在頭皮上留下一個PS新手練習摳圖一樣的生硬的發際線。
然而對直發的迷戀似乎某種程度上蒙蔽了她們的雙眼,好像假發只要是直的,以上這些缺點都可以視而不見。
3
盡管對假發充滿了熱愛,但當非洲人見到真發的時候還是非常羨慕的。
我就有過很多這樣的經歷。一些尚不曾見多識廣的年輕人,他們會頗有禮貌地問我可不可以摸一下我的頭發。我當然會滿足他們這個小小的請求。
如果對方是一群孩子,就成了羊入虎口,每個人都爭先恐后地過來摸頭。當然這都不是惡意的,只是一種好奇。他們是想要感受一下這種烏黑亮麗、修長平直的真發究竟是什么樣的。
大概每一個游走在非洲基層的慈眉善目的中國人,特別是長發飄飄的東方佳人,都會有類似的經歷。
當來自兩萬公里外的原生直發從非洲女性指間絲滑而過的時候,作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假發消費群體中的一員,她們終于有了一個標準,可以對市面上的各類參差不齊的假發發質做出一個終極裁斷,但是也只能在心中發出一聲羨慕而絕望的嘆息。
對于非洲以外的人來說,一頭漂亮的原生頭發是引以為傲的,而非洲人通常認為美的頭發卻是人造的。
這其中固然有發質的原因,但歐洲式金色卷發和東亞式黑色直發的流行,多少隱喻著非洲人對自己身體的不自信。畢竟在北京的街頭能看到留著“非洲辮”的中國人,要遠少于在法蘭西城里看到的戴著直發發套的非洲人。
這種在“將什么定義為美”中對自身的否定,更明顯地體現在了他們對膚色的偏好中。
4
我一個非洲哥們G君,有一個黑白混血的女朋友,姑娘的爸爸是法國人。他經常會很自豪地在社交網絡上曬混血女朋友的照片,平常也會不時地跟朋友炫耀。并且,他的女朋友在學校中也是非常受歡迎。
這不是個例,實際上所有在非洲生活的混血人和膚色更淺的人總是會更受異性青睞。
只要有機會,非洲人就會想娶一個白人女人作為自己的妻子,或者說嫁一個白人男性作為自己的丈夫。如果真的能實現的話,這是一件能為自己的家族爭光且非常有面子的事情。但之所以很多人沒有這樣做,只是因為他們缺少社會資源、缺乏社會地位而已。
這種對于淺膚色的追求,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皮膚漂白”文化。
聯合國的一項調查表明:非洲第一人口大國尼日利亞有77%的女性正在使用各種皮膚漂白產品,這一數字在鄰國多哥也達到了59%。在加蓬,另一家機構作出的調查顯示:在16~40歲的青年婦女中有六成人在努力漂白自己的皮膚。
我們要注意,中國常見的美白,很多情況下只是因為皮膚被曬黑了,或者說是有點發紅、發暗,所以會使用各種美白產品,而非洲人,是真的在漂白自己的皮膚。
盡管同樣生活在非洲大陸的古埃及人早在三千年前就開始有意識地美白自己,但如今盛行在非洲的皮膚漂白文化則非古已有之,而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現象。
20世紀60年代,化學工業的發展才為廣大愛美的非洲女性提供了一個可以往自己的臉上涂抹各種皮膚漂白產品的機會。但這類廉價且缺少規范化管理的美白產品中往往含有超標的對苯二酚,在清除了皮膚中的黑色素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疥瘡、毛囊炎等皮膚病和顏色深淺不一的斑塊,嚴重者甚至還會患上皮膚癌。
即便如此,各種“危言聳聽”的社會新聞還是阻擋不了前赴后繼的漂白大軍。
5
按照科特迪瓦一位社會學家的說法,非洲婦女這么做是為了“變得更像西方人”。
深色皮膚的同胞,似乎長期以來就是一個落后的存在。長期積貧積弱,深色的皮膚無法喚起他們對于自己族群的認同感和自信心,但是地中海和大西洋對面的西方人,卻被蒙上了一層美好的面紗,隱喻著美麗、有力、高級、財富、文明等。
特別是自從大眾傳媒普及以來,電視、廣告和雜志中充斥著美好的白人女性的形象,這使得上述的聯想更加深入人心。積極愛美的女性開始漂白自己的皮膚,之后更多的女性也被從眾效應帶動了起來。
當然,日益壯大的皮膚漂白文化同時也觸發了激烈的反對的聲音。當地的朋友L君曾經給我展示了幾張漂白失敗的女人的照片,鄙夷地將這些崇洋媚外的女性批判了一番。在和女生小A聊到這個話題時,她則自豪地宣稱她就喜歡她自己的膚色。
一些和他們持有同樣想法的人,在法國,在非洲,成立了各種反皮膚漂白的社會組織,更加大聲地反對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審美。
與此同時,也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倡導摘下假發。
這固然是件好事,可是也從側面反映了非洲人自我認知時的尷尬境地。對皮膚漂白的反對聲,某種程度上是不安且無奈的非洲人被迫做出的姿態,是在缺少話語權的環境下尋找自我認可。
6
制造業界有句話:“一流企業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賣技術,四流企業做產品。”同樣的道理,放在世界范圍內的審美話語權中依舊適用。
如今的世界,審美的主流標準仍然是由西方人制定,在“將什么定義為美”這個話題上,非西方文明缺少發言權。
然而,世界也在向著一體化同時也是“再地方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包括非洲、中國在內的所有非西方文明,需要認真思考這個一體化與多元化同在的矛盾語境,并努力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現代化的自我認知。
編輯/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