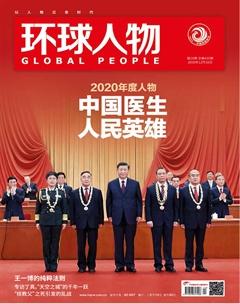沈括,絕世才學抵不過低情商
李開周
說起沈括,想必大家都熟知,他寫過一部《夢溪筆談》,被英國科學史大牛李約瑟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上最卓越的人物”。在科學發現上,他確實卓越。
他最早發現了磁偏角,最早記錄了活字印刷,最早對海市蜃樓做出光學解釋,最早對滄海桑田做出地質學解釋;他設計出更加精確的實驗方法,重新驗證了《墨子》里記載的小孔成像;他發現了石油的用途,還用石油燃燒后的煙塵試制出第一批油墨;他擁有縝密的數學頭腦和強大的計算能力,獨立推導出高階等差數列的求和公式,還準確算出在不靠“打劫”的情況下,圍棋棋局的演化總數是3的361次方。
最神奇的是,沈括還搞過“天氣預報”。在《夢溪筆談》中,他記錄了公元1076年某一縣城發生龍卷風的情況,是東亞關于龍卷風方面的最早記錄。當時有一段時間,京城久旱,宋神宗讓沈括推算哪天會下雨,他斷言“雨候已見,期在明日”(《夢溪筆談·象數》)。意思是說皇上請放心,明天就會下雨。到了第二天,果真下起雨來。
眾所周知,天氣預報是一項復雜的大工程,需要海量儀器對溫度、濕度、風速和大氣環流進行實時觀測,再將觀測數據代入計算模型,才有可能給出比較準確的預報。沈括生活在宋朝,既沒溫度計,也沒計算機,他是怎么預報天氣的呢?
沈括預報天氣,用的不是氣象學,而是中醫理論。這套理論叫做“五運六氣”,五運即五行,六氣則是風、寒、濕、暑、燥、火。傳統中醫將年、月、日、時變成天干地支,又把天干地支轉化成五行,再用六氣來描述病人的癥狀特征,最后根據五行生克來推算病人該在什么時辰吃什么藥。沈括把這套理論用在天氣預報上,強行將天干轉化成五運,將地支轉化成六氣。比如說,某天是庚丑日,庚對應五運里的金,丑對應六氣里的濕,金能生水,再碰上濕氣,必定下雨。
五運六氣能不能預報天氣呢?肯定不能。這里面的邏輯漏洞非常明顯:干支紀日每60天循環一次,難道每逢庚丑日都會下雨嗎?就算下雨,難道會在全國一起下嗎?沈括自己也發現了這個漏洞,所以他又補充一句:“皆視當時當處之候”(《夢溪筆談·象數》),意思是說預報天氣不能光靠五運六氣,還要觀察當時當地的氣候。那天,他幫宋神宗預報天氣,恰逢久旱不雨,連陰了好幾天,突然一日轉晴,太陽光強烈,這才推斷出次日會下雨。
在《夢溪筆談》里,沈括成功預報天氣的例子僅這一個,他卻據此認定自己的理論顛撲不破。將個案當成鐵證,是他搞研究的風格。
有一次,朋友生病發燒,沈括開出藥方,讓人服用鐘乳石的粉末。之后朋友退燒,沈括便將鐘乳石治發燒的方子寫進醫書《沈存中良方》。發燒只是癥狀,病因千差萬別,鐘乳石或許能消除某個病人的發燒癥狀,對其他病人卻未必有效,甚至還會有害。
作為一個“搞科研”的人,沈括不但不了解鐘乳石,也不了解許多自然現象。比如,他認為風是“木氣上升”形成的,木能生火,所以風也能生火。他還不加驗證地采信民間流傳的許多說法:白雞到了嶺南會變黑雞,麥子受潮會化成飛蛾,月食時看不到河蚌和蛤蜊。由此看來,沈括也會盲從和輕信,這違背科學家應有的懷疑精神。

戴紅倩/繪
沈括甚至還迷信算命。他曾推算自己的命運,結論是“括死時頗熱鬧”(張耒《明道雜志》)。意思是他去世前會有高官厚祿,去世后會被風光大葬。實際上呢?他中年被罷官,晚年被流放,臨死前精神失常,最后凄凄慘慘地死在了流放地。
所以,從現代科學體系來論,沈括并不算嚴謹意義上的科學家。通讀全本《夢溪筆談》,會發現這是一部博物學書籍,既有卓越的科學發現,又有搞笑的偽科學,還摻雜著沈括在政治、財政、農業、歷法、醫藥、音樂、詩詞等領域的議論。如果非要給沈括一個頭銜的話,“博物學家”也許比“科學家”要合適。
不過,跟宋朝其他士大夫乃至整個古代中國的士大夫相比,沈括都算是一個罕見的能人。
年輕時,沈括在京城當小官,幾個大臣爭論太陽是圓球還是圓片,沈括不但給他們提供了正確答案,還現場演示了推算日食的方法。后來他被派到北方邊境督造兵器,不但改進了弓弦的制造工藝,還改進了士兵射箭的要領——拉滿弓弦,以勾股定理為依據,瞄準遠方的靶子,十有九中。再后來,宋遼兩國談判疆界,互不相讓,始終無果。沈括一聲不吭,去樞密院調閱檔案,從一封遼國致大宋的國書里找到了對大宋有利的證據,遼國使臣啞口無言。當時,宋神宗龍顏大悅:“微卿,無以折邊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1)。即如果不是沈愛卿出手,怎能結束這場疆界之爭呢?
沈括性格上謹慎、怯懦,力求自保,容易讓人覺得反復無常。這最終導致他個人信用破產,在守舊派和變法派里外不是人。兩派固然視同水火,但在鄙視沈括這件事上,立場卻出奇的一致。
沈括如此聰明能干,多多少少和家世有關。他出生在杭州一個世家大族,祖上在五代十國時期就被吳越國王重用。他父親在大宋當官,先后擔任縣長(縣令)、市長(知州)和省長(轉運使)。父親生了兩個兒子,他是次子,出生很晚,比哥哥的兒子還要小。他哥哥名叫沈披,從縣長做到副省長(安撫副使),在興修水利方面功績卓著。沈披的兒子沈遘和沈遼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沈遘不到20歲就中了榜眼,擔任過開封知府;沈遼則是書法名家,曾教授王安石書法。后來,沈遘、沈遼和沈括三人并稱“三沈”。說起來沈遘、沈遼比沈括成名更早,但名氣不如后者,以至于后來元朝人修《宋史》,誤把沈遘當成沈括的哥哥,還濃墨重彩地給沈遘立傳,卻將沈括的傳記附在沈遘之下。
宋朝世家大族喜歡彼此通婚,沈括家和王安石家也不例外。從親戚關系上講,王安石算是沈括的表侄,但王安石年長,比沈括早進入官場。1063年,沈括進京參加中書省考試(相當于明清時期的“會試”),主考官是蘇東坡的親家范鎮,副考官是王安石。那一年,沈括考中進士,按照慣例,拜考官王安石為師。幾年后,王安石變法,遇到司馬光保守派的極力阻撓。兩派各執己見,水火不容,沈括自然站在王安石這邊,很快成為王安石“新黨”花名冊中排名第十五的干將,為新法擂鼓助威、奮力疾呼。
在人浮于事、思想迂腐的大宋士大夫群體中,沈括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技術官僚”。他博學多才,聰明多智,為人謹慎,事事謀定而后行,既不保守,也不激進,把王安石交辦的所有工作都做得又快又好,深受王安石的青睞和器重。后來,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夸獎他 “謹密”,意思是性格謹慎,做事縝密。
但對王安石的變法,沈括也并不完全贊同。根據基層當官的經驗,再加上精密的大腦,他很快就看出變法的諸多漏洞。但囿于王安石是上司,兩人又有師生情誼,他不敢正面反對,也不敢稟報皇帝。直到1074年,變法失敗,王安石被罷相,聽聞大臣吳充要當宰相,他才偷偷跑到吳充府上,以三司使的身份向其上書,歷數新法的種種弊端,提議廢除一些變法措施。
在王安石看來,沈括有話不當面說,等自己下臺才說,屬典型的小人行徑。1075年,王安石復出,在宋神宗跟前對沈括的評價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4)。所謂“壬人”,就是像水一樣變動無常的小人。王安石說沈括反復無常,品德敗壞,勸皇帝把沈括趕出朝廷。不久,沈括就被貶至宣州,此后一蹶不振,被一貶再貶,最后去了潤州。正是在潤州的夢溪園,他完成聞名中外的科學巨著《夢溪筆談》。
沈括果真是小人嗎?未必。他頂多是情商低,性格上謹慎、怯懦,力求自保,容易讓人覺得反復無常。他這種性格,在官場上自然行不通,最終導致個人信用破產,在守舊派和變法派里外不是人。兩派固然視同水火,但在鄙視沈括這件事上,立場卻出奇的一致。我們看宋人筆記,保守派罵沈括奸詐陰險,變法派也說沈括有才無德,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信用破產的后果很嚴重。后來,宋哲宗即位,大赦天下,但朝中人紛紛上書歷數沈括罪行,宋哲宗便主張誰人都可赦,唯獨沈括不可赦。可見他的“小人”形象已深入人心,即便他天文地理、音樂醫藥、律歷占卜等才學絕世,再耀眼的光芒也會被遮蔽掉。
沈括(1031年—1095年)
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漢杭州錢塘縣(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官員、科學家。出身于仕宦之家,1063年進士及第,授揚州司理參軍。宋神宗時參與熙寧變法,歷任太子中允、三司使等職,晚年移居潤州(今江蘇鎮江)。代表作《夢溪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