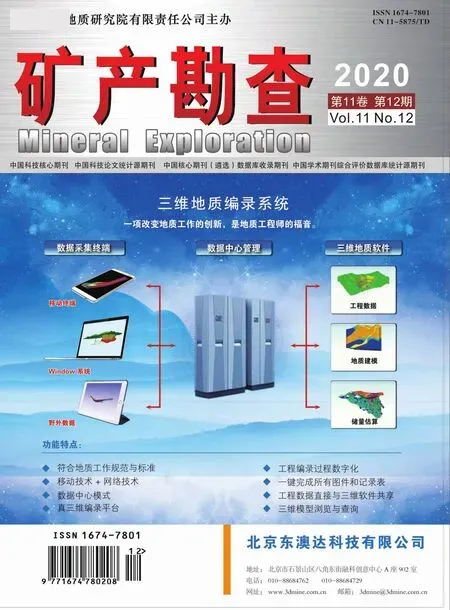云南省耕地“非糧化”現狀及其生態環境效應
楊朝磊,李燦鋒,田瑜峰,周洪,何建寧,劉建平,馬一奇
(1.中國地質調查局昆明自然資源綜合調查中心,云南 昆明 650100;2.中國地質調查局軍民融合地質調查中心,四川 成都 610000;3.中國地質調查局海口海洋地質調查中心,海南 海口 570100;4.中國地質調查局西安礦產資源調查中心,陜西 西安 710000)
0 引言
“非糧化”指的是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逐漸改變為種植利潤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的現象,這些土地雖然仍屬于耕地的范疇,但其種植糧食作物的性質已發生轉變。近年來,中國耕地“非糧化”的演化趨勢日益突出,已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如易小燕和陳印軍(2010)、張茜(2014)和王沖(2016a)等研究者分別對中國河北、河南與山東等糧食主產區的“非糧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分析,并提出了預防耕地過度“非糧化”的措施建議;朱忠貴(2011)、何蒲明和全磊(2014)則研究了中國耕地“非糧化”、“非農化”的形成機制與原因,同時分析了耕地“非糧化”可能帶來的危害,尤其是針對國家糧食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解析。耕地“非糧化”是價值觀念、人口規模、消費結構、消費水平等社會要素與區位條件、水熱條件、氣候類型、土地資源稟賦等不同自然資源要素相互耦合的綜合作用結果,因此,造成耕地“非糧化”現象發生的因素往往較多,楊瑞珍等(2012)、曾雅婷等(2018)、趙小風等(2019)、武舜臣等(2019)充分總結了當前耕地“非糧化”的形成主因,包括種植業結構變化、種糧比較效益偏低、土地流轉法律政策不夠完善、地方政府對種糧缺少支持、農地管理監督制度缺乏、土地流轉成本高、農戶認識局限以及水、土、熱自然資源稟賦分配等多種因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短期來看,耕地的“非糧化”“非農化”確實給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如陳江龍和曲福田(2006)就曾指出耕地“非農化”顯著提高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以云南省為例,該省的鮮花份額占全國市場份額的50.00%以上,2018 年全省鮮花種植總面積為11.4 萬hm2,綜合產值為525.90 億元,給花農帶來的直接收入更是高達124.80 億元①云南省綠色食品發展中心商省花卉產業專家工作組.2018.2018 年度云南花卉產業發展公報[Z].https://www.sohu.com/a/327576006_644801.,如此高的經濟效益,既增加了農戶的收入,同時也為地方GDP 的提高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非糧化”顯著提高了耕地的經濟利潤產出,但由該現象長期演變所引起的自然環境惡化,尤其是對生態環境服務功能造成的影響與破壞卻少有人注意,長此以往,勢必會對自然生態的保護與重大生態工程的實施產生嚴重影響,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目前,國內不同學者針對耕地“非農化”的生態價值損失機制已開展了部分研究,同時建立了估算生態價值損失的方法與模型,如楊振等(2013)、陳娟等(2013)、任平等(2014)分別以江漢平原、陜西、四川等地為案例進行了分析,計算出了農地“非農化”造成的生態價值損失,許恒周等(2013)則研究了耕地“非農化”對碳排放的影響,提出了農地“非農化”水平的提高會顯著增加農業碳排放量的觀點,總體來看,前人對耕地“非農化”的研究已相對較為成熟,而對耕地“非糧化”的研究,尤其是針對該現象所造成的生態價值損失與環境負面效應卻關注較少,基于此,該文選擇云南省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系統的數據收集,解析該省耕地“非糧化”的時空演化現狀,以“非糧化”現象作為研究背景,結合水生態環境、土壤環境、大氣環境變化狀況,深入分析與研究該現象長期演變所導致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而為云南省實施耕地保護、環境保護等重大生態工程提供基礎資料與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云南省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地處21°8′~29°15′N,97°31′~106°11′ E 之間,東部主要與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相鄰,北部緊鄰四川,西北面為西藏自治區,該省山多地少,地形以山地高原為主,地勢上西北高東南低,山地占了全省面積的84.00%,高原占10.00%,2018 年全省土地調查面積為3831.89 萬hm2,其中農用地面積為3291.67 萬hm2,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85.90%。云南省除滇西北屬于高原山地氣候外,其它區域基本屬于亞熱帶和熱帶季風氣候,全年日溫差大,年溫差小,干濕季分明,降水在季節上和地域上分配極不均勻,地形氣候特征差異大,區內分布有瀾滄江、紅河、怒江、珠江、長江、伊瓦洛底江等諸多水系。全省生物資源十分豐富,2018 年森林面積為2311.86 萬hm2,覆蓋率達60.30%,森林蓄積量19.70 億m3,濕地總面積60.60 萬hm2。從社會經濟發展來看,云南省當前共下轄16 個州市,2018 年全省總人口為4829.50 萬人,人口密度為122.50 人/km2,城鎮化率47.81%,生產總值17881.12 億元,占全國比重2.00%,其中,第一產業2498.86 億元,第二產業6957.44 億元,第三產業8424.82 億元。
1.2 數據來源
本次研究工作所涉及的數據主要來源于1989—2018 年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云南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摘要》、《中國農產品價格調查年鑒》、《中國農業統計資料》、《中國農業年鑒》與《云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資料。
2 研究方法
為全面研究云南省耕地“非糧化”現狀,更進一步地對“非糧化”時空演變特征進行解析,分別引入“糧作比例”與“糧作比例變動強度”兩個概念。其中,“糧作比例”是反映耕地是否“非糧化”的重要標志,即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與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比值,“糧作比例”越小,耕地“非糧化”越嚴重。“糧作比例變動強度”指的是“糧作比例”的年變動強度(王沖,2016b),其計算公式主要為:

式(1)中Qa為a年時的“糧作比例”,Qb為b年時的“糧作比例”,T為a和b之間的相隔年份,即T=b-a,K表示“糧作比例變動強度”。論文其他樣本數據的分析則主要運用SPSS 軟件的偏相關與雙變量相關性分析功能進行處理,其中,雙變量相關分析是研究2 個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影響)程度,不排除其它變量的影響,而偏相關分析是在多變量的情況下,對一些變量進行控制,剔除其對其它變量的影響,從而衡量多個變量中某兩個變量之間的線性相關程度,因此,在研究2 個變量之間關系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其它變量對兩者之間的影響,這樣才能將兩者真正的關系顯現出來,SPSS 軟件分析功能中的相關性分析可以充分實現這一需要。
3 耕地非糧化
3.1 耕地情況
農業用地主要包括耕地、林地、園地、牧草地及其它農業用地等,在云南省的農業用地中以林地的分布面積最大,2018 年為2300.13 萬hm2,占土地面積的60.00%,耕地面積則為620.91 萬hm2,占土地面積的16.20%(圖1a)。1989 年全省耕地總面積為282.28 萬hm2,直到1998 年,云南省的耕地面積都保持在較低水平,10 a 間只增加了11.25 萬hm2,1998 年之后,全省耕地數量迅速增加,一年之間的增長量達345.23 萬hm2,耕地總面積快速上升至1999 年的638.76 萬hm2,往后的20 a 間,該省的耕地總面積均保持在600 萬hm2之上。相較1989 年,2018 年全省耕地面積共增加了338.63 萬hm2,增長率為119.96%,年均耕地增加量為11.29 萬hm2(圖1b)。從整體來看,云南省的耕地資源十分緊缺且集約化利用水平整體偏低,利用方式相對粗放,坡度小于8°且適宜耕作的壩子(盆地)僅占土地總面積的6.00%,人均耕地面積較低,2018 年僅為0.128 hm2,全省紅壤系列的土地占該省總面積的55.32%,由于紅壤其本身的有機質分解較快,因此土壤肥力和產出效能均較低,而一些地區的土地質量更是在加劇退化。其次,該省的耕地還大多以旱地為主,比例高達74.90%,對水資源的需求十分巨大,這對于水資源量十分緊缺的云南省而言,從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該省農業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云南省城鎮化、工業化快速擴張,人口不斷增加,導致用地需求的剛性增長,供需矛盾日益加劇,嚴重增加了耕地的壓力(曾維軍等,2016;趙曉園和李學坤,2018),數據顯示,2003 年云南省建設用地為74.91萬hm2,而2018 年已增至112.24 萬hm2,15 a 間增加了49.80%,嚴重擠占了壩區的部分優質耕地。土地資源分布不均衡,區域發展不協調,土地質量與土地生態整體不高,再加之水土流失、石漠化、旱澇災害等環境因素的影響,云南省耕地資源保護情況日益嚴峻(彭爾瑞等,2009;袁磊等,2015;陳展圖和楊慶媛,2019),對該省2020 年保住598.00 萬hm2的耕地保有量和495.40 萬hm2的基本農田目標提出了巨大挑戰。
3.2 農作物現狀
3.2.1 糧食作物
云南省是農業大省,也是農業弱省,其高海拔的地理環境兼具低緯氣候、季風氣候與山原氣候的特點,農業發展獨具優勢,比較適宜種植水稻、茶葉、烤煙等農作物以及一些中草藥材(董曉波等,2016),但該省山多地少,農業耕地質量普遍不高,尤其是其梯田形的地形因素限制,使得農業機械化難以展開,無法實現高效的農業產出。從農作物種植上來看,云南省1989 年農作物種植面積為436.00 萬hm2,2018 年為689.08 萬hm2,較往年增加了253.08 萬hm2,平均每年增加84360.00 hm2,糧食作物種植方面,1989 年為352.70 萬hm2,2018 年為417.46 萬hm2,較往年增加了64.76 萬hm2,平均每年增加21586.67 hm2,在糧食產量方面云南省也基本實現了保持穩步增長的良好趨勢,2004 年糧食總產量已突破1500.00 萬t,1989—2018 年的30 a 間,平均糧食增長率達2.87%,2006—2015 年更是實現了總產量的“十年連增”,2018 年全省糧食產量為1860.54萬t(圖1b),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2.80%。

圖1 云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基本情況
從糧食產量來看,云南省雖然保持了較好的增長趨勢,但在糧食資源的保障方面卻出現了許多問題,全省糧食供需一直呈現“緊平衡”的態勢,即糧食的供需達到或基本達到平衡狀態,糧食自給率一直較低,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從全國來看,人均糧食占有量至少為400.00 kg 時,糧食安全才有保障(張利國,2010),云南省人均糧食占有量多年處于400.00 kg 以下,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圖1c),尤其是作為主要口糧的稻谷增長較慢,難以與人口增長速度保持同步。從不同州市來看,全省的糧食供需區域性矛盾十分突出,糧食產出主要集中在大理、紅河、曲靖、昭通、文山等地(圖2),迪慶、怒江、麗江等州市則因氣候惡劣,土地貧瘠,產糧一直較低,其余地區如西雙版納、德宏、普洱等州市因地理因素的限制,經濟作物種植面積逐年擴張。近年來,云南省工業用糧、飼料用糧更是在不斷增加,糧食調入量逐年上升,糧食缺口不斷加大(圖1d),據省財政廳公布的信息顯示,2018 年全省糧食調入量已達554.80萬t,耕地數量減少,質量不斷退化,糧食種植面積逐年壓縮,使得全省的外部調入糧食連年增長,對外依存度不斷升高,十分不利于云南省高原農業的平衡發展。
3.2.2 經濟作物

圖2 云南省2018 年不同州市糧食占比分布圖(數據來源:2018 年云南省統計年鑒)
經濟作物具有成熟期短、收益高、氣候適應性強、可全年種植的特點,所以經濟作物在不同區域內均可大面積播種且復種指數往往較高,云南省屬于立體氣候,對于種植經濟作物具有優越的自然環境,一些傳統的經濟作物不僅是局部地區的重要經濟支柱,同時也是該省的重要產業支柱。近年來,隨著農業生產成本的不斷上升,種糧比較效益的持續低下與經濟作物高額回報所帶來的刺激作用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戶從事經濟作物的生產,全省的種植業結構發生了大范圍調整。近15 a 的數據顯示,該省茶葉、水果、蔬菜、烤煙、油菜等主要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均在不斷增加,尤以蔬菜的增加幅度最為明顯,15 a 間增長了146.11%(表1)。從不同州市的經濟作物種植情況來看,2004—2018 年全省的油菜種植面積穩步上升,除德宏、大理兩個州市的種植數量有所下降外,其余地區的油菜面積均保持穩定或呈增長趨勢,2018 年油菜種植面積最大的州市為曲靖、保山和文山(表2),分別占總面積的29.85%、11.59%、13.11%;甘蔗屬于云南的傳統優勢經濟作物,全省除迪慶因氣候影響未種植甘蔗外,其余州市都有分布,近年來,玉溪、保山、昭通、麗江、西雙版納、大理的種植面積均有所下降,而昆明、曲靖的種植面積則一直較少,部分年份已無人種植(表3);烤煙作為云南的主要經濟作物,全省除昆明、玉溪、昭通略有減少外,其余州市的種植面積均保持穩定上升,2018 年以曲靖、玉溪、楚雄三個州市的種植面積最多(表4);蔬菜是近年來增長最快的經濟作物,這與云南省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從數據來看,2004—2018 年該省16 個州市的蔬菜面積都在上升,其中,增長最快的是文山市,2018 年已達19.60 萬hm2,較2004 年增長了14.55 萬hm2,文山也成了云南省蔬菜種植面積最大的州市(表5)。
(2)用戶上傳需要存證的文件,將文件的關鍵信息寫入到合約文件類中去,以此建立用戶和數據的對應映射關系。

表1 2004—2018 年云南省主要經濟作物種植情況

表2 2004—2018 年云南省油菜種植情況

表4 2004—2018 年云南省烤煙種植情況

表5 2004—2018 年云南省蔬菜種植情況
3.3 非糧化現狀
糧作比例是反映耕地是否“非糧化”的重要標志,從云南省1989—2018 年的農作物與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數據中可以看出,云南省的農作物種植面積正逐年上升,但糧作比例卻逐年下降,耕地“非糧化”的趨勢在不斷增高(圖3),2009 年,全省農作物種植物面積已增長至600.00 萬hm2以上,而至2018 年的10 a 間糧食作物種植面積卻始終保持在400.00 萬hm2左右,難以保持同步的上升趨勢。從時間上來看,1989 年全省糧作比例為0.809,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在農作物中的所占比重依然較大,這與當時的農業產出、社會經濟有很大關系,由于糧食單產較低(1989 年為2830.71 kg/hm2),農戶只能依靠大面積的糧食種植來保證糧食產量,全省的糧作比例直至2005 年依然保持在較高水平,而到了2018 年糧作比例已下降至0.606,年均下降0.67%,其中2006、2011 與2017 年的糧作比例下降程度最多,較上一年下降范圍均接近4.00%(表6)。
從不同州市來看(表7),1989—2018 年,云南省16 個州市的農作物種植面積均在上升,但大約有接近40.00%州市的糧食作物種植面積在下降,不同州市均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耕地“非糧化”現象,糧作比例的變化強度更為顯著,以1989—2018 年30 a 間的統計數據為基礎,從糧作比例變動強度方面來分析非糧化的空間分布特征。從表8 中可以看出,16 個州市中大理、怒江、昭通、曲靖的糧作比例年變動強度較小,其中昭通市的變動強度僅為-0.098%,說明這些州市的耕地種植結構相對穩定,而昆明、楚雄、玉溪、臨滄、文山、西雙版納、德宏州等州市的糧作比例變動強度則較大,尤其以玉溪市的“非糧化”趨勢最為突出,變動強度為-1.493%,根據不同州市的糧作比例變動強度,將它們分為5 個等級,分別為昭通(-0.098%~-0.550%)>大理、怒江、曲靖、保山、迪慶、麗江(-0.551%~-0.837%)>普洱、紅河、西雙版納(-0.838%~-0.995%)>德宏、臨滄、楚雄、昆明、文山(-0.996%~-1.492%)>玉溪(-1.493%)(圖4),從總體來看,整個研究區的糧作比例年變動強度均為負值,這顯示在農作物種植體系中,隨著種植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區內糧食作物的面積和在下降,在整個種植結構中的比重正被不斷壓縮,耕地“非糧化”的趨勢在逐步擴大。

圖3 1989—2018 年云南省農作物種植情況(數據來源:1989—2018 年云南省統計年鑒)

表6 1989—2018 年云南省耕地糧作比例變化趨勢

表7 1989—2018 云南省各地市作物播種面積變化
4 生態環境效應
基于1989—2018 年的云南省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糧作物種植面積、糧作比例、化肥使用量等統計數據,運用SPSS 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偏相關與雙變量相關性分析,具體分析結果見表9 與表10。從表9 中可以看出糧食作物面積與化肥使用量的相關系數為0.884,而經濟作物與化肥使用量的相關系數為0.977,表中數據均通過了0.01 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化肥使用量與經濟作物的相關性要比農作物更為顯著,而從糧作比例來看,其與化肥的相關系數為-0.956,二者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10),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農業化肥的使用量主要與經濟作物在農作物種植體系中的比例有關。當選擇糧作比例與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為控制變量進行偏相關分析時,經濟作物與化肥的相關系數為0.477,同時通過了0.05 的顯著性檢驗,這與雙變量分析的結果相一致。綜上所述,該文認為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是影響農業生產化肥投入量的主要因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越大,化肥投入量越多。

表8 1989—2018 年云南省“糧作比例”年變動強度相關情況
當前,云南省農業面源污染已十分嚴重,研究顯示自2000 年后該省的農藥使用量增加幅度不斷上升(吳曉波和馬庭矗,2010),農藥的濫用亂用加之廢棄農藥包裝的隨意丟棄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土壤污染與水源污染(李永文,2017),2015 年云南省化肥施用強度達806.18 kg/hm2(楊連心等,2018),遠遠超過原國家環境保護局2007 年印發的生態縣、市、省建設指標(修訂稿)中化肥施用強度小于250.00 kg/hm2的評價標準,其中,10 個州市已屬于中等風險區(楊連心等,2018)。可以看出,當前,云南省的農業污染已經對自然環境保護與重大生態工程的實施產生了嚴重影響,而由“非糧化”趨勢擴張所導致的環境負面效應必然會加重當前農業面源污染的威脅,亟須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視。

表9 SPSS 雙變量分析結果

表10 SPSS 偏相關分析結果
4.1 土壤環境
耕地“非糧化”使得云南省的種植業結構發生了大范圍的調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與糧食作物相比,經濟作物的化肥施用量要高出其61.50%(李家康等,2001),以云南省2014 年的研究數據為例,該省農作物中N+P2O5+K2O 化肥施用量最高的是花卉、水果與果樹,它們比糧食作物的施用量分別高385.00%、245.00%和145.00%,而花卉的化肥施用量更是高達每季1155 .00 kg/hm2(王金林等,2018),在如此情況下,經濟作物面積的不斷增長就會使得農業生產中的化肥投入量越來越多,尤其是在耕地產出普遍低下的情況下,大部分農戶為了提高土地的效益產出,必然會選擇投入更多的化肥。云南省的土壤本身大多偏酸性,化肥的大量投入會使pH 值持續降低,鹽化、酸化變得更加嚴重(秦文俊,2014),田間土壤穩定性發生改變,含水量減少,物理性質變劣,土壤肥力與生產力不斷減弱,甚至發生土地板結,出現“肥越施越多,地越耕越差”的現象(Blake et al.,1994;張桂蘭等,1999;候彥林 等,2004;Bronick and Lal,2005;Kaiser and Ellerbrock,2005;Liu et al.,2008)。研究顯示,一些經濟作物如果樹、蔬菜的大面積增加,還會造成區域氮盈余的現象發生,影響生態系統中的氮循環過程(甄蘭,2007)。云南省目前每年因農業生產流失的化肥高達100.00 萬t 左右,據2007 年《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云南省農業污染源普查報告》數據顯示,該省農業污染源排放到環境的COD 占全省總排放量的11.31%,為8.12 萬t,其中,總氮排放量占全省總排放量的31.02%,為6.17 萬t,氮肥徑流和淋溶5.60 萬t,占90.80%,總磷排放量占全省總排放量的63.44%,為6635.32 t,徑流流失5338.05 t,占80.40%,這些大量流失的化肥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更為嚴重的是產生了大面積的農業面源污染,而經濟作物短成熟期的特征還會使得區域內的年均施肥次數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造成農業污染源一直在長時間序列上保持高強度的輸入,耕地的過度“非糧化”會使這種負面效應不斷擴大,尤其是在缺乏長期科學合理施肥指導的情況下,“非糧化”將對耕地的生態環境、營養質量、土壤理化性質等都產生較大影響,不利于“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目標的實現。
4.2 水生態環境
《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報告》數據顯示,中國的農業面源污染在各大污染源中排列第一,已成為影響中國水環境質量安全的重大影響因素,而在農業面源污染中,種植業的貢獻最為顯著,其產生的TN 與TP 已經分別高達污染物排放總量的1/3 和1/4(胡鈺,2012),農藥與化肥中未被作物吸收的N、P 等化學元素富集在土壤中通過地表徑流、地下淋溶等途徑進入附近河流,最后匯入湖泊,給湖泊水質帶來嚴重危害,造成水資源污染、地表水富營養化等(胡宏祥等,2005;李志宏等,2008;朱梅和吳敬學,2010;陸沈鈞等,2020)。云南省高原湖泊眾多,分布有滇池、撫仙湖、程海、瀘沽湖、杞麓湖、異龍湖、星云湖、陽宗海、洱海等九大高原湖泊,這些湖泊不僅是中國分布最密集的五大湖群之一,同時也是珠江水系、長江水系、瀾滄江水系的重要支流,近年來,隨著農業生產強度的不斷提高,農業環境污染已對上述高原湖泊的水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尤其是經濟作物種植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使得水環境的污染負荷率不斷增高(劉俊和陳紅,2009;趙祖軍等,2018),如研究發現大蒜的大面積種植是影響洱海流域水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盧中輝等,2017),除洱海外滇池流域周圍種植的大量經濟作物如蔬菜、花卉等也對該湖泊的水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與影響(陸軼峰等,2003;高明和楊浩,2006;王磊等,2010)。以“非糧化”現象最為顯著的玉溪市為例,該市范圍內分布有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等湖泊,據云南省生態環境廳公布的2018 年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上述湖泊中除撫仙湖達到了水環境功能要求,水質為優,處于貧營養狀態外,其余2個湖泊都處于中度富營養狀態,并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化學元素超標現象(表11),湖泊水生態環境的惡化與玉溪市耕地“非糧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三大湖泊流域的總面積為141422.57 hm2,而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就占了30.33%,且種植的大多為高投入、高污染的蔬菜等經濟作物(趙祖軍等,2018),數據顯示,三大流域的農作物中經濟作物的污染流失強度最高,為32.37-35.24 kg/hm2,其中露地蔬菜的總氮流失系數(22.5 kg/hm2)與總磷流失系數(1.38 kg/hm2)更是明顯高于其他農作物(趙祖軍等,2018),前人針對不同湖泊的研究也顯示,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即耕地非糧化率的不斷上升是導致星云湖、杞麓湖水質長期保持劣質的重要因素(楊逢貴等,2013;許杰玉等,2015;趙祖軍等,2018;鄭田甜等,2019)。

表11 2018 年玉溪市高原湖泊水環境狀況
4.3 大氣環境

圖5 云南省各州市缺水程度圖(據楊學智等,2019 修編)
農業源溫室氣體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排放量占到了全球人為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GHG)排放總量的30%,對氣候變暖的影響不容忽視(IPCC,2007;Lin and Fei,2015;Bennetzen et al.,2016;鄧悅等,2017),數據顯示,全球約有1/5 的溫室氣體來自農業排放(FAO,2016),而到2050 年,農業可能是最大的排放源之一(Timperley,2019),由此可見,減少農業源溫室氣體的排放對于減緩全球氣候變暖起著十分重要的關鍵作用。作為農業大國,中國農業溫室氣體在其全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占據了較大比例,同時農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一直在增加(冉光和等,2011;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對氣候變化司,2013;尚杰等,2015;張曉萱等,2019)。根據世界銀行和世界糧農組織的報告,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自2000—2014 年持續增加,其中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了16.10%(FAO,2016)。農業溫室氣體的產生主要與農業種植養殖、農田土壤、農化品碳排放、農業廢棄物、土地利用變化等因素有關(Reicosky et al.,2000;Johnson et al.,2007;黃祖輝和米松華,2011),而農化產品如化肥、農藥的使用及其所隱含的碳排放在中國農業源溫室氣體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譚秋成,2011;齊曄等,2012),王寶義(2016)的研究顯示,在1993—2016 年中國的農業碳排放結構演變趨勢中,由化肥所產生的年均碳排放所占比例均接近或超過60.00%。中國種植業中的N2O 與CO2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51.85 萬t、15626.98 萬t 分別增加至2011 年的65.50 萬t 與31258.10 萬t,增加趨勢十分明顯,這其中,化肥的排放量貢獻率最為顯著,產生的N2O、CO2排放量在種植業中分別高達25.30萬t 與18731.83 萬t(尚杰等,2015)。農業中N2O、CO2氣體排放量的增加與當前農業種植中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的高投入以及耕地的生產管理方式存在密切聯系,尚杰等(2015)研究也認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主要與中國為保持糧食產量的穩定增長,化肥、農藥等農用物資投入的增加有關,尤其是隨著全國種植業結構不斷調整,蔬菜、果樹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使得農業溫室氣體中的N2O 與CO2排放量持續升高。
隨著云南省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農業生產中的化肥投入量也會不斷上升,研究顯示,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00%就會導致CO2排放量增加3.2839 %(West and Marland,2002)。自1995 年以來,云南省農業碳排放量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化肥、農藥是主要的碳排放來源之一(盧冬冬和郭勇,2015),由于云南省經濟作物的化肥施用量一般要高出糧食作物許多(圖6),因此,隨著整個區域內耕地“非糧化”面積的不斷上升,由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增加所產生的農業溫室氣體也會隨之增長。其次,化肥使用還會使土壤原本的質地、含水量、通透性等發生轉變,從而影響土壤的硝化反應和反硝化反應以及N2O 的生成和擴散速率,進一步對N2O 的生成與排放產生影響。其它耕地“非糧化”現象,如采摘園、農家樂等生態農業的發展造成的部分農用地和非農用地之間的轉換,旱田向水田之間的轉換還會對土壤原始層產生強烈擾動,顯著改變土壤原本的碳庫儲存量,影響土壤向大氣中排放碳的進程(曲福田等,2011)。綜上所述,云南省耕地“非糧化”現象的發生,不僅會對土壤環境、水生態環境等造成嚴重污染與破壞,同時還會影響CO2、N2O 等農業源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十分不利于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降低農業源污染和減緩GHG 排放等重大生態工程的實施,對云南省的生態環境保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美麗鄉村建設也會產生嚴重影響。
5 討論
當前,云南省耕地“非糧化”趨勢已十分顯著,這是不同社會要素與自然資源要素耦合的綜合作用結果,該省耕地資源稀缺且質量整體不高,耕地的細碎化更是使得全省的農業集約化利用水平整體偏低,這些因素都導致農業生產投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之種糧比較效益低下、農業自然災害頻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使得農作物體系中的糧食種植比例不斷下降,經濟作物面積逐步擴大。從效益來看,經濟作物的生產能夠帶來高額的利潤回報,對于農戶而言可以獲得可觀的經濟收入,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更是可以顯著提高GDP 的增長,這似乎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但人們卻往往忽略了耕地“非糧化”長期演變所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如土壤環境變劣、水生態環境污染、大氣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等環境負面效應,尤其是從文中可以看出,化肥等生產資料的投入與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即“非糧化”率顯著相關,是影響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投入量不斷增加的主要因素。云南省農業面源污染的形勢十分嚴峻,經過多年的治理,狀況雖已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各類生態環境問題,而“非糧化”面積的不斷擴大勢必會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復雜與嚴重,十分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
在如此背景下,只有從耕作制度、施肥管理、生產方式、農田環境管理等方面進行干預才能對耕地“非糧化”所造成的環境負面效應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結合當前資料,為進一步推進耕地“非糧化”的研究,系統科學地構建“非糧化”的理論研究機制,該文認為下一步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研究:一是從造成耕地“非糧化”的社會要素與自然資源要素方面入手,研究導致“非糧化”現象發生的不同社會與自然資源要素之間的耦合性與協調性以及影響不同地區耕地非糧化率高低的主導因素。二是建立科學合理的評估計算模型,定量化計算耕地“非糧化”所造成的生態價值損失與環境負面效應如土壤酸化率、污染負荷增加量、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程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等,同時研究不同生態補償機制,為耕地環境的保護與恢復提供數據信息。三是耕地的過度“非糧化”對糧食的保障也會造成較大影響,以云南省為例,其糧食單產在短時間內難以取得質的突破,近5 a 來都保持在4000~4500 kg/hm2的范圍內,遠遠低于全國糧食單產水平(圖7),在糧食單產一定的情況下,種糧面積的不斷減少必然會引起糧食產量的下降,工業用糧、飼料用糧的不斷增加,糧食缺口勢必會不斷加大,而長期“非糧化”造成的耕作層、水利設施、灌溉系統的改變,更會導致部分耕地恢復種糧的可能性幾乎變為零,在糧食自給率處于“緊平衡”的情況下,“非糧化”產生的糧食產量損失將會給糧食安全保障帶來巨大沖擊,因此,研究不同地區,尤其是評價一些糧食主產區的“非糧化”變化對全國糧食安全保障造成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四是耕地作為“山、水、林、田、湖、草”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度“非糧化”會對耕地及其周圍的相關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影響與破壞,長此以往,恢復生態環境的代價將變得十分巨大,因此,防止耕地過度“非糧化”,保護好耕地,劃定耕地“安全紅線”,制定嚴格的耕地占補平衡機制,是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保護和修復的重要環節,在此基礎上,就需研究者不斷探索與制定合理比例的“山、水、林、田、湖、草”均衡發展模式,以此來改善耕地“非糧化”所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為政府部門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國土綠化行動提供依據與決策支持。
6 結論
(1)云南省1989 年的糧作比例為0.809,2018年已下降至0.606,年均下降0.67%,全省16 個州市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耕地“非糧化”現象,根據它們的糧作比例變動強度,可將其分為5 個等級,分別為昭通(-0.098%~-0.550%)>大理、怒江、曲靖、保山、迪慶、麗江(-0.551%~-0.837%)>普洱、紅河、西雙版納(-0.838%~-0.995%)>德宏、臨滄、楚雄、昆明、文山(-0.996%~-1.492%)>玉溪(-1.493%),其中,昭通市的糧作比例變動強度最小,表明其種植業結構相對穩定,而玉溪市的“非糧化”趨勢則最為突出。
(2)耕地過度“非糧化”對土壤環境、水生態環境、大氣環境等都會產生嚴重影響,造成土壤污染、耕地肥力下降、水生態環境破壞、水質變劣、地下水位下降、農業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等環境負面效應,十分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亟須引起各方面的重視。

圖7 中國及云南省糧食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數據來源:1989—2018 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云南省統計年鑒)
(3)為進一步推進耕地“非糧化”研究,系統科學地構建“非糧化”的理論研究機制,應從不同地區的耕地“非糧化”主導因素、生態價值損失估算、生態補償機制建立以及對糧食安全保障的影響評價等方面加強研究,同時,不斷探索與制定合理比例的“山、水、林、田、湖、草”均衡發展模式,為政府部門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國土綠化行動提供依據與決策支持。
致謝論文工作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王佳月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審稿專家給論文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