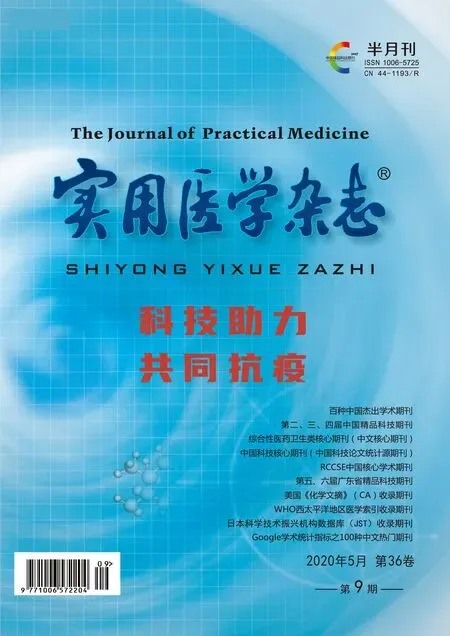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銀屑病相關性的實驗研究進展
徐曉蓉 龔堅 王婧 吳嘉明 劉巧
1江西中醫藥大學(南昌330004);2江西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南昌330012)
銀屑病是一種在遺傳背景下,環境因素誘發,免疫介導的具有慢性復發性特點的全身炎癥性皮膚病[1]。因其纏綿難愈、反復發作的特點,給患者身心帶來巨大的負擔,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銀屑病可發生于任何年齡,男女患病率相近,影響著世界人口的2%~3%[2]。銀屑病的研究成為當前醫學的熱點和難點。隨著對其發病機制的深入研究,相應的治療方法也越來越廣,傳統的治療仍然存在較多并發癥。近年來,腸道菌群失調和銀屑病發病機制的相關性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并提出調節腸道菌群紊亂可能成為治療銀屑病的靶點。LEE 等[3]研究表明,腸道皮膚軸參與了炎癥性皮膚病。本文將從腸皮膚軸為切入點,將腸道菌群與銀屑病相關性的實驗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腸道菌群與腸皮膚軸
1.1 腸道菌群人類腸道內棲息著大量微生物,其種類1 000多種,總數達1014,其基因含量超過了寄主的100倍[4-5]。這些微生物寄居在腸道黏膜表面,與宿主形成了互利共惠的關系,參與一系列對宿主健康至關重要的生理過程,包括能量平衡、物質代謝、腸上皮健康和免疫活動等[6-7]。腸道菌群組成結構復雜,主要包括3大類:益生菌(乳酸桿菌、雙歧桿菌等)、條件致病菌(腸球菌、大腸埃希菌和擬桿菌等)和致病性細菌(葡萄球菌、變形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和梭狀芽胞桿菌等)[8]。微生物之間平衡受到破壞,即腸道菌群失調會產生較多有害菌,腸道屏障功能和通透性增加,導致機體免疫功能受損,在這一過程中有可能對皮膚功能產生負面影響[9]。腸道菌群產生的游離酚和對甲苯酚是芳香氨基酸的代謝產物,被認為是腸道環境紊亂的生物標志物。這些代謝物參與循環,優先在皮膚中積累,損害表皮分化和皮膚屏障的完整性[10]。同時腸道失調會使上皮通透性增加,進而激活效應T 細胞,破壞它們與免疫抑制調節T 細胞的平衡;而促炎癥因子會進一步增強上皮通透性,形成慢性全身性炎癥的惡性循環[10-11]。
1.2 腸皮膚軸皮膚和腸道是血管密集、神經功能豐富的器官,具有重要的免疫調節、防御、神經內分泌功能。作為人類與外部環境聯系的主要接口,這兩個器官對維持生理平衡至關重要[10]。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腸道和皮膚之間存在密切的雙向聯系,胃腸健康與皮膚的平衡穩態有關[10,12]。胃腸道疾病常常伴有皮膚癥狀,胃腸道系統,尤其是腸道微生物群,也參與了許多炎癥性疾病的生理病理過程[13]。SCHER 等[14]發現銀屑病患者腸道菌群多樣性的減少與炎性腸病患者腸道菌群失調的模式非常相似。可見,腸道與皮膚有著緊密的關聯性。“腸-皮膚軸”學說為腸道微生態與皮膚疾病相關性研究提供了依據,腸道菌群紊亂在銀屑病的發生、發展中有較大影響[15]。
2 腸道菌群與銀屑病發病機制
在對銀屑病及胃腸道不適患者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銀屑病患者出現胃腸道不適癥狀及并發炎性腸病的幾率均高于健康人群,反之亦然[16]。另一項研究顯示,7%~11%的炎性腸病患者同時患有銀屑病,這可見銀屑病與胃腸道炎癥的關系尤為密切[17]。在對銀屑病及炎性腸病的腸道菌群的研究中發現,某些有益菌(如普拉梭菌)在銀屑病和炎性腸病中均減少[18-19]。同時,銀屑病患者腸道炎癥相關自身抗體和炎性細胞浸潤顯著升高同炎性腸病相似[14];而且腸道菌群的差異與宿主基因型有緊密的聯系,銀屑病和炎性腸病患者的易感基因存在一定的交叉[20-21]。由此推測,銀屑病與腸道菌群紊亂導致的全身炎癥反應和免疫問題相通,腸道菌群紊亂參與到銀屑病伴發的全身性病變。另一方面,某些遺傳和環境因素以及免疫途徑共同參與了這兩種疾病的發病機制,例如:在銀屑病的發展中起主要作用Th17 細胞及其細胞因子,同時也參與了炎性腸病的生理病理過程[22]。腸道菌群可以通過改變T 細胞反應來控制咪喹莫特誘導的銀屑病皮膚炎癥,這提示腸道菌群影響了銀屑病的發病機制[23]。這為銀屑病、炎性腸病、腸道菌群三者之間關系提供另一種可能解釋。
有研究[24]發現,銀屑病患者腸道菌群多樣性和相對豐度明顯減少。其中雙歧桿菌屬、布勞特氏菌屬、糞球菌屬等在銀屑病患者腸道中顯著降低。同時,銀屑病患者糞便中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CFA)的含量較健康人明顯減少;SCFA可通過促進調節T細胞在結腸環境中的誘導和適應度來調節T 細胞群的數量和功能[14]。SCFA對Treg細胞發揮調控Th1/Th2、Th17/Treg等免疫平衡的功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SCFA缺乏或缺陷與細胞能量、營養代謝、物理屏障、免疫炎性反應等相關。厚壁菌門的某些屬種可通過SCFA的G 蛋白偶聯受體43(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R43)上調Treg 細胞。而T/B淋巴細胞、DC 細胞、巨噬細胞、Nk 細胞等免疫細胞與銀屑病發病密切相關。HUANG 等[25]采用16S rRNA 對35例銀屑病患者和27例健康者的糞便進行測序,發現銀屑病組與健康組的菌群存在差異;重度銀屑病患者的菌群與輕度銀屑病患者的菌群不同,與健康對照組的菌群也不同,這證實銀屑病患者存在明顯的紊亂菌群。由此可見,基于微生物群對銀屑病的進一步研究,可能為銀屑病的發病機制提供新的認識,也為銀屑病的防治提供更多的依據。
3 腸道菌群與銀屑病治療干預
腸道菌群紊亂參與了炎癥性和免疫性疾病的生理病理過程,因此糾正腸道菌群失調、保持腸道微生態平衡是預防和治療銀屑病的新靶點,目前治療措施包括以下幾方面:
3.1 益生菌及益生元益生菌是一類通過調節腸道微生態平衡對宿主產生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在免疫調節、代謝過程和神經內分泌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6]。長期以來,通過引入活性生物體(益生菌)來選擇性地增強腸道微生物群,或通過給予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益生元)來積極地促進生長,從而控制腸道微生物群。益生元在特應性皮炎、痤瘡和傷口愈合方面的應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7]。益生菌、益生元對皮膚具有免疫調節作用,通過降低皮膚細菌負荷和拮抗侵襲性共生,增強皮膚屏障修復功能[28]。IRFAN 等[29]在一項為期6 d的動物試驗中,發現乳酸桿菌益生菌-65 改善了咪喹莫特誘導的小鼠銀屑病皮損嚴重程度,還降低了銀屑病相關的促炎細胞因子,如IL-17A、IL-19、IL-23的表達水平。由此可認為乳酸桿菌不僅可以緩解臨床癥狀,并且可降低促炎細胞因子的水平。CHEN 等[30]團隊也證實了這一觀點,他們評估戊糖乳桿菌GMNL-77 對咪喹莫特誘導的銀屑病小鼠模型的影響,與未經處理的對照組小鼠相比,經過益生菌處理的小鼠明顯較少出現紅斑、鱗屑和表皮增厚。MAGDOLNA 等[31]總結口服益生菌對銀屑病的影響,發現目前有3種不同的益生菌都顯示能改善病情,但現有的數據有限且參差不齊,因此很難提出在銀屑病患者中適當補充益生菌的方案。
以上實驗說明,益生菌、益生元對緩解臨床癥狀有積極作用,可作為銀屑病的一個戰略性治療策略,但還需要大樣本的臨床證據來支持其在銀屑病的治療作用。
3.2 糞菌移植技術(FMT)FMT是增加患者腸道有益菌、改變腸道菌群紊亂的結構、重建腸道內環境最直接的方式;當前正被用于恢復腸道菌群的平衡。腸道菌群失調參與了銀屑病的發生和發展,改變腸道菌群可能是這種疾病新的治療策略。一項為期6個月的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試驗,該實驗在循證醫學指導下探討FMT是否比安慰劑更有效地減輕銀屑病關節炎患者的疾病活動。YIN 等[32]對1例重度銀屑病患者進行FMT治療評估,發現治療后患者皮損累及體表面積、銀屑病面積和嚴重程度指數、生存質量指數、胃腸道癥狀等明顯改善。由此,提示FMT 可能是治療銀屑病的一種新療法,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
3.3 飲食干預飲食對銀屑病的影響是患者高度關注的環境因素之一。國家銀屑病基金會醫學委員會對55項研究的4 534例銀屑病患者進行系統評價,提出可以通過飲食干預補充其治療方法,以降低疾病的嚴重程度[33]。飲食對銀屑病至關重要,它包括許多促炎化合物(如飽和脂肪酸、血紅素、鐵)和抗炎化合物(如膳食纖維、一些多酚)。LADAN 等[34]對銀屑病患者飲食習慣、皮膚反應和感知等方面調查,發現銀屑病患者攝入的糖、全麥纖維、乳制品和鈣明顯減少,而攝入的水果、蔬菜和豆類更多;還指出堅持地中海飲食和銀屑病嚴重程度之間在統計學上呈顯著的負相關。而YUKO 等[35]研究發現高脂飲食會加重咪喹莫特誘導的小鼠銀屑病樣皮炎。銀屑病是一種全身炎癥性皮膚病,TAKESHITA 等[17]提出并鼓勵有必要向銀屑病患者提供綜合護理。因此,對銀屑病患者進行飲食建議和管理選擇,不僅控制和預防他們的病情,而且有利于他們的整體和長期健康。但是,目前飲食干預來調節腸道微生物組成的機制仍不明確。
總之,當前使用糞便移植治療銀屑病可緩解臨床癥狀,而益生菌、益生元則可以減輕咪喹莫特誘導的小鼠銀屑病炎癥,促進腸道黏膜屏障恢復,且在臨床應用方面也取得一定療效。飲食干預也對銀屑病的治療有著重要作用。而目前關于改變腸道菌群的治療效果不盡相同,其具體機制仍待今后進一步研究。
4 總結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銀屑病與腸道菌群兩者的關系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之一。筆者闡述了腸道菌群的生理功能及病理特點,著重探討腸道菌群失調在銀屑病發病中的可能作用機制以及通過改變腸道菌群治療銀屑病的可能方式。雖然腸道和皮膚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但是腸道微生物是否通過腸道皮膚軸參與銀屑病的發生和發展有待進一步證實。腸道菌群與銀屑病的研究是將來發展的一個新方向,以腸道微生物作為靶點的治療策略還需要更多的臨床數據與進一步的基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