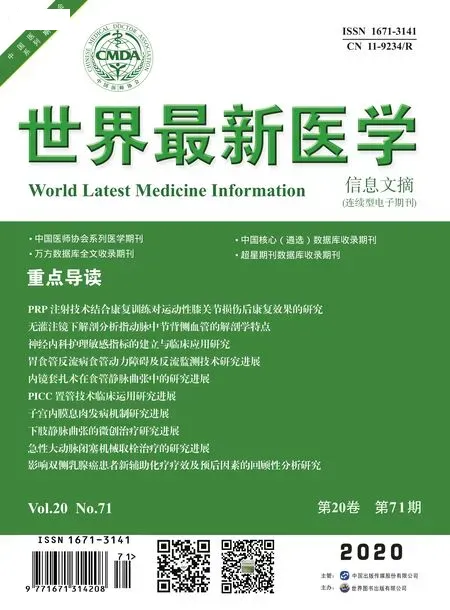壯醫對新關病毒肺炎的認識與防治概述
黃愛書,滕彩芳,李月桂,李鳳珍,何椋,羅容冰,黃振宇,廖小婷,農謹榕
(1.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 南寧;2.廣西國際壯醫醫院,廣西 南寧;3.廣西大學商學院,廣西壯族自治區 南寧)
0 引言
壯族先民常年住于嶺南之地,《古今醫案按》言: “瘴者,障也,天地自然之氣,為崇山峻嶺,障蔽不舒而然也。”[1]因其獨特的氣候和環境,該地多雨、潮濕、悶熱,森林茂密,蛇蟲腐敗可致病微生物和病媒蟲害的滋生,故嶺南容易發生“瘴毒”,其在人體虛弱趁機侵犯后發病,故壯醫稱“百因毒為首,百病虛為根”[2]。關于“瘴毒”的來源,宋·周去非《嶺外代答》[3]提到“蓋天氣郁蒸,陽多宣泄,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說明“瘴毒”是一種氣候、地理環境共同作用引起的自然因素。以及《后漢書·南蠻傳》載“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者,十必有四五”,表明瘴病嚴重影響人類的生命健康。
從2019年12月份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于我國以武漢為中心,逐漸向全國蔓延至大部分地區。隨著疫情日益嚴峻,我國新增確診人數達數萬人,嚴重危及人們的健康,工作、學習、生活。為避免疫情迅速擴散,并于2020年1月份武漢封城,之后全國啟動重大公共衛生事件1級響應。疫情的擴散程度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出臺各種措施抗疫,其中堅持中西醫并重的要求,發揮中醫智慧,彰顯中醫力量,成為戰疫的一支主力軍。到第六版診療方案[4],中醫對患者的分型已和西醫一致,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癥,針對不同類型的患者使用中藥治療。COVID-19疫情能否盡快有效得到防控,治療和預防是重要的一部分。目前疫情雖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我國每日確診數量仍有增加。在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壯醫風濕科)、學科帶頭人李鳳珍教授的指導下,筆者團隊總結了壯醫對COVID-19的認識與壯醫往年所積累下來的預防傳染性疾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簡單易操作,副作用小,以供老百姓防控COVID-19參考。
1 壯醫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認識
壯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其中90%以上聚居于廣西,廣西地屬嶺南,山深林密,多雨濕熱,易染瘴毒。凡瘴毒之氣所致的突發性疾病稱為瘴病,壯醫藥在預防、治療等均有地方特色和優勢。據《后漢書·馬援傳》記載:“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許多防瘴的民俗在民間流傳至今,其中,以壯鄉靖西端午藥市最具有代表性,列入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壯醫的“瘴毒”,是指南方山林中因濕熱蒸郁能使人致病的有毒氣體,多指熱帶原始森林里動植物腐爛后生成的有毒氣體。壯醫認為,凡瘴毒之氣所致的突發性疾病稱為瘴病[5]。壯醫把瘴病分為陰瘴即冷瘴、陽障即熱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主癥為惡寒發熱或無熱、乏力、干咳,具有發病急、傳染性強、變化快等特點。故本病當屬壯醫“瘴疫” 范疇。瘴毒之氣侵犯人體后,多阻滯氣道,使氣道不暢,進而累及三道兩路,出現惡寒發熱或無熱、乏力、干咳,或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瀉等。瘴毒侵襲后,是否發病,還取決于兩方面:一則“毒”力的大小,二則人體正氣的強弱。毒與正氣兩不相立,正氣可以祛毒,毒可傷正,毒正相爭,正不勝毒則發病。其年老體弱,或多病體虛,正氣不足者,病情多危重,易快速發展為呼吸困難、休克等危重。而身體強壯、正氣充足者,或感瘴毒輕者,可僅表現為低熱、輕微乏力等癥狀。內因是正氣虛、外因主要是瘴毒,病機特點為虛、毒,其中,毒在初起時以寒、濕為主,寒濕郁久方化熱。壯醫辨證為陽證與陰證,陽證:癥見發熱,或高熱、咳嗽、痰黃或稠、乏力、頭痛、全身酸痛、口干、口苦、心煩、尿赤、便秘、舌質紅、苔黃或黃膩、脈滑數。陰證:癥見不發熱、或低熱、微惡寒、頭身困重、肌肉酸痛、乏力、咳嗽、痰少、口干、飲水不多、或伴胸悶、無汗或汗出不暢、或見嘔惡、納呆、大便溏泄、舌淡紅、苔白膩、脈浮略數。因此,預防方法以芳香辟穢、化濁解毒為主,兼顧補氣提陽,壯醫治療原則以調氣、解毒、補虛為主。藥以芳香辟穢、化濁解毒為主,兼顧補氣,多采取內服、外治結合,注重預防。
2 壯醫防治法
2.1 鼻飲法
鼻飲法,壯族先民用來預防瘴病和中暑等急性疾病。有史料記載[6], 如《漢書·賈捐傳》:“ 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以鼻飲”,且《嶺外代答》亦有相關理論:“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水,置鹽及山姜汁數滴于水中,施小管如瓶嘴插諸鼻中……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此記載說明,鼻飲是把鹽及姜汁等混合于水中,后將之通過瓜瓢側方的小孔用蔥管導入鼻腔,疏通鼻腔,具有“涼腦快膈”的作用,壯醫認為此法,疏通“龍路、火路”的氣機,祛除瘴氣,使天、地、人三氣平衡。
根據COVID-19的急性病程特點,可運用此方法快速解寒濕毒。此方法歷史淵源,簡單,易操作,療效可,起到良好防病作用。
2.2 刮、刺、灸法
著名《肘后備急方 》作者葛洪記載了嶺南用刮、挑、刺、灸外治法治療瘴病,經過歷代醫療實踐 ,效果靈驗,且具有簡 、便 、廉 、效 、速的優勢 ,故得到廣泛認可及臨床運用,COVID-19病情變化快,臨床表現形式多樣,可根據病情需要而定。
2.2.1 刮法
清·林森指出治療痧病有三法即“焠”法、“刮”及“刺”法,“焠”法和“刺”法相當于針刺放血療法,而“刮”法與壯醫刮痧療法類似。特列瘴氣一章錄載《嶺南衛生方》[7]的多篇文章,解析“今東南人有刮疹之法,以治心腹急痛。蓋使寒隨血散,則邪達于外而臟氣始安。此亦出血之意也”。“細究其義,蓋以五臟之象,咸附于背。故向下刮之則邪氣亦隨而解。”此法在壯族民間常用,牛角、牛骨、陶瓷片等可作為刮痧工具。刮痧部位以患處及患處周圍為主,如頭痛可刮頸部,發痧刮背部等。刮痧操作先以潤滑劑涂在皮膚上,所用的潤滑劑除了植物油或酒為佳。用刮痧工具從上向下刮,或沿著皮膚紋理和肌肉走向刮療,直至皮膚出現暗紅色或紫紅色的斑點、斑塊。在刮痧過程中,要注意用力均勻柔和,用力適度。此法可通龍路、火路的氣機,調和氣血,提高人體抗病能力,具有“補虛”作用,體現了壯醫的“補虛”原則。COVID-19癥狀表現為全身酸痛可用此法,以達到扶正驅毒的療效,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
2.2.2 壯醫針刺法
關于針刺法,歷史久遠,《素問·異法方宜論》就有記載“: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攣痹,其治宜微針。故九針者,亦從南方來。”說明南方霧露氣候,人民生活習慣,疾病多以攣痹為主,適宜針刺,故針刺法歷史久遠,而且《嶺外代答》記載:“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里,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并足而立,刺兩足后腕橫縫中青脈,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亦表明壯族先民早已用針刺法治療瘴病,經過長期醫療活動實踐,發揮了比較好的療效,創造了有其獨特的系統理論,壯醫針刺療法[8]是以壯醫理論為指導, 通過針刺人體特定穴位或反應點, 調整臟腑、骨肉的功能, 調通三道兩路,達到天、地、人三氣同步,以治療疾病的一種特色外治法。其中刺血療法也是常用法,用刺血療法治療熱瘴,將瘀滯人體內的瘴毒隨血排出體外,同時通龍路、火路,使臟腑恢復正常功能后,可調動人體免疫機制提高免疫抗病能力,與壯醫的解毒、補虛原則相似。根據COVID-19患者病情早期雖多為寒濕特點,但病情變化迅速,病程急,期間隨時演變為濕熱,達到扶正的效果的同時驅邪作用。
2.2.3 壯醫灸法
灸法治療病瘴體質羸弱者:《赤雅》[9]對灸法載有相關描述:“炎方土脈疏,地氣外泄,人為常襖燠所爍。膚理不密,兩疏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脘郁悶虛煩,下體凝冷”。指出灸法不適合熱瘴。
壯醫灸法使局部溫熱或者輕度灼痛的刺激,具有溫經散寒,調氣血(噓、嘞)的作用。壯醫香灸療法(香灸)操作方法:用特制的壯香灸,點燃熄滅明火后,用珠火在穴位或部位上灼灸或溫熨。選大椎、風池、肺腧、神闕、關元、氣海、胃脘、足三里,每日施灸一次。注意事項:距離皮膚不能太近,以免燙傷。合并出血性疾病或有出血傾向者;孕婦、身體極度虛弱者禁灸。
流行病學報告表明兒童患病較少且癥狀較輕,中老年患病較多且死亡率較高[10-11]。說明小孩為純陽之體,《黃帝內經》提到“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說明人過半百則陽氣衰,抵抗力弱,人至老年陽氣漸衰多見虛寒冷,故常有畏寒、手腳冰涼的虛寒體質者,為易感人群,根據COVID-19發病的季節,辨證符合寒濕者,可選此方法,亦是調三道兩路,補虛扶陽,平衡陰陽,解寒毒、濕毒的防治目的,陽證不適合此法。
2.3 壯醫藥線點灸,
藥線點灸是壯醫傳統自然療法[12],已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通絡止痛、散結消腫、溫經通痹、退熱等功效,壯醫認為其可通龍路、火路,促進人體氣血的循環,使人體陰陽平衡,從而提高自身抵抗力,藥線制法:將苧麻浸泡于藥酒中,點燃后熄滅明火,運用炭火星,直接灼灸患者體表的特定穴位或部位,以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嶺南衛生方》記載:“大椎或第五椎,隨年壯,二穴皆能止瘴癘寒熱”“瘴病即久……宜灸膏肓并大椎骨下及足三里”。 壯醫根據“瘴病”的辨證,根據證型選穴,進行藥線點灸治療,對COVID-19進行辨證選穴而定,常用穴位:風池、風府、大椎,肺腧等,通龍路、火路,以達到調氣血,解毒作用。
3 壯醫敷貼療法
壯醫敷貼療法[13]是將壯藥貼于人體某個部位或者穴位上,通過藥物的刺激,通過調節天地人使三氣同步,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藥物根據病情而定。敷貼藥方:吳茱萸、透骨消、蒼術、通城虎、七葉一枝花等藥物。操作方法:將相應的壯藥共碾成粉末,后將生姜汁調,選穴為:大椎、肺腧、膻中、天突;每次2-6小時,每日1次,10-14天為1療程。注意事項:嚴重皮膚化膿感染者,不宜行該療法,敷藥后過敏者停用。COVID-19病情辯證多數符合寒濕特點,可選:吳茱萸、透骨消、蒼術等藥物,調通龍路、火路,增強體質。
4 內服法
在壯醫理論的指導下,進行陰陽辨證,根據壯醫“毒虛致病論”[14]、“三道兩路”學說[15],壯醫認為三道兩路為人體很重要的部位,三道即氣道屬于現代呼吸系統方面谷道即消化系統方面,水道為泌尿系,根據此次COVID-19癥狀,主要涉及氣道、谷道,臨床表現為發熱、高熱、咳嗽、氣喘跟氣道息息相關,臨床表現為腹痛腹瀉、嘔吐,致患者食欲下降,則說明病情波及谷道,按照壯醫原理采取“調氣解毒補虛”治療原則。
4.1 單味藥物治療
單味治療瘴病的藥物有薏苡仁、鐵冬青、青蒿、黃花根、金銀花、楊桃、蚺蛇、辣椒、青蒿等等。 《后漢書·馬援傳》中有記載:“出征交趾,土多瘴氣……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援在交趾,常餌意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說的是東漢時期,戰亂時期,受瘴毒影響,危及生命健康,壯族給服用薏苡仁防治瘴毒的方法。鐵冬青和金銀花,這兩味藥,具有清熱、解毒、防瘴的功效,現如今仍是嶺南常用涼茶的主要成分,適合用于熱障部分,COVID-19高熱者,可適量加用鐵冬青、金銀花以清熱解毒作用,發揮壯醫的解毒原則。
4.2 復方藥物治療
隨著對瘴病及藥物療效的了解,在單味藥物的基礎上進行組方即復方藥物治療,如《永福縣志》載有:“俗有青草、黃茅之瘴,觸之者投以苦辛之劑即愈……冷瘴以瘧治,熱瘴以傷寒治,啞瘴以傷寒失音治……治瘴不可純用中州傷寒之藥”等。 《嶺外代答》有青蒿散治療瘴疾有極其靈驗效果的描述:“昔靜江府唐待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瘴疾服之有奇驗。藥用青蒿、石膏及草藥”,若瘴疾患者“服之而不愈,是其人稟弱而病深也,急以附于丹砂救之,往往多愈”。《嶺南衛生方》記載了瘴病在陰陽表里未分之際用嘉禾散治療;感受瘴毒出現的內寒外熱、咽隘間煩躁不解等癥狀時用冷湯治療;出現上寒下熱、腿足寒厥等癥用沈附湯治療;如見頭疼身痛用草果飲治療;如冷瘴的治療,首先用姜湯或陳皮半夏湯送服感應丸,次日專服和解散,根據COVID-19病情重者,單位藥物力度較弱時,可對病情予辨證后進行選擇多味藥物進行組方,加強對抗病毒的作用。
能早期迅速控制氣道癥狀,縮短病程。
5 居家調護
勤洗手,注意衛生,南方濕氣盛行,窗戶通風,保持干燥,飲食清淡,適當運動,練習壯藥繡球操、三氣養生操,蹂風車、打扁擔、舞拜、打磨秋、打滾石,壯醫還創編了具有獨特保健功效的壯拳,老少皆宜,體現了壯醫“未病先防”的治未病壯醫理念,增強體質,及注意隔離,謝絕集體活動,COVID-19感染患者當中,以體質虛弱者為主,注意養正氣,所謂“正氣內存邪不可干”,練習壯藥繡球操、三氣養生操,加強鍛煉有助防病,COVID-19傳染性強,居家隔離避免交叉感染。
6 結語
壯醫民族醫藥作為祖國的傳統醫藥的重要部分,發揮好壯醫對本次疫情的作用是我們醫者的職責,長期實踐表明,療效佳,值得推廣與應用,共同抗疫,讓老百姓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