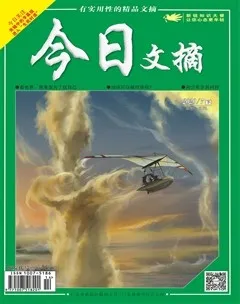老陳的理發鋪

老陳的理發鋪,其實根本稱不上是店鋪,只是在小區入口的空地處搭了一個小棚子。今年因街道要求拆除違章建筑,便連棚子都沒了、用了一把大遮陽傘替代。只是墻上的那面鏡子還在,鏡子這邊是“老陳理發”4個字,另一邊掛著“每位5元”的布標,這便是他的全部家當。
除了刮風下雨天,老陳一般每天下午兩點準時出攤兒。這個老小區里大都是幾十年前平房改造后回遷的居民,也大都是老鄰居,大家愿意聚在老陳這里待著說說話。老陳也住小區里,平時出攤兒,就隨手提來一個皮箱,上面印有“興隆理發店”字樣,至于熱水瓶啥的,早來的“老伙計”們都給他灌滿開水預備好了。
老陳是科班出身,初中畢業就被分配到著名的興隆理發館當學徒,學徒期3年剛過,由于經營不善,加之觀念陳舊又趕上南方鋪子如溫州發廊的興起,國營的“興隆”不久就倒閉了。
理發店倒閉之后,屋漏偏逢連陰雨,老陳的妻子又生了場大病,生活越發拮據的他,在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下,加入了出租車司機的行列。那時出租車行業十分景氣,司機陳師傅這一改行就是15年。5年前老陳正式退休,在家賦閑沒幾日,就坐不住了,百無聊賴的他有一回收拾舊物時,猛然發現了床下積了灰的“皮箱”,于是重操舊業,做起了理發生意。
老陳理發鋪的顧客基本都是“老”主顧、回頭客,50歲以上的老大爺占絕大多數,剪的也多是簡單的寸頭或光頭。不過偶爾也有例外,有一次3號樓的王大爺帶著小孫子來剪頭發。王大爺平時節儉慣了,原先都是自己給孫子剪頭發,隨著年紀越來越大,手越發不聽使喚了,這次把孫子的頭發剪得里出外進活像個小刺猬,兒媳婦不高興了。王大爺既生自己的氣,還又心疼錢,就找老陳來了。
老陳二話不說,把小家伙的頭發修剪得圓圓滾滾,看上去虎頭虎腦,還堅決不收王大爺的錢。從那以后人家就讓老陳給孫子剪發了。后來,老陳的大皮箱旁又多出來一個小紅皮箱,那里面是一套新的剃頭家伙事兒:推子、剪子、刷子和毛巾一應俱全。如王大爺這樣的再帶著“孫伙計”們來剪頭的時候,他就換用這套新的,給小朋友專門理發。慢慢地,帶孩子來找老陳理發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
5年以來,除了刮風下雨,老陳一個月也總有一天是不出攤兒的。剛開張時,隔著馬路對面的居民樓里有一位老劉頭,是老陳這個小鋪商的常客,經常是吃完午飯睡上一會兒,拎個茶缸子就來,一聊就是半天。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老劉都沒來,大家都以為人家是出門了。直到一天下午,有一位40多歲的男子找到老陳,說他是老劉的兒子,原來前一段時間老劉中風了,還挺嚴重,已經不能下樓了。最近老爺子鬧著要刮臉剃頭,于是兒子就來找老陳了。
據老劉的兒子說,中風后的他脾氣暴躁,吐藥片、罵護工是常事兒,頭發、胡子更是如蓬草一般。老陳去看望老劉那天,他的情緒倒是十分穩定,安靜地坐在輪椅上。老陳一邊忙乎手里的活兒,一邊勸慰老劉:“兵荒馬亂的年月,我們這行兒手藝都沒有失傳。這說明人呀,到什么時候,都得想法兒把自己個兒弄得干凈利索了,老哥呀,你是體面人兒,咱可得好好活呀。”老劉的兒子送老陳出門前,老陳把老劉家的月份牌從3月5日,撕到了6月2日,嘴里還念叨著,日子還是得一天天地過。就這樣,老陳每月都會去找老劉,給他刮臉、剪發。上個月老劉病故,老陳隨了一份厚禮并停業3天,以示哀悼。
據說這片老小區也快拆除改為一座大型購物廣場,老陳心里有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只是還在堅持著每日內容,還是擺放著那張“每位5元”的布標。
(趙卓藝薦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