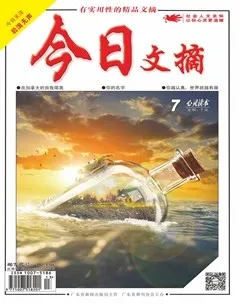我們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動物如何共處?

疫情陰云之下,人們對野生動物的情感變得更加復雜,也增加了緊張和恐懼。但即便取締野生動物非法交易,人和野生動物的共存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城市里的動物鄰居
我是一個研究動物的人,今天聊一聊動物的故事。
大熊貓、雪豹等動物,生活在遠離城市的森林和荒野,但我們都很熟悉。我們卻經常忽略一些生活在城里的和我們做鄰居的動物,其實,城市里有很多我們叫不出名字的動物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比如上海的標志性動物貉,一丘之貉的貉,它就生活在我們身邊。再比如在深圳,豹貓生活在鬧市區的華僑城,旁邊就是世界之窗。實際上,今天的北京、成都、西安、南京、上海……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大量有關人和動物的故事。
為什么我們對那些荒野之中的動物那么了解,而對身邊的這些動物卻一無所知?我們到底錯過了什么?
我小時候的家在北京的中關村,我在這里曾經發現過幾十個鴛鴦家庭。鴛鴦在中國的分布,跟一些國家級和世界級的風景名勝區基本上是重合的,從西湖到婺源,從北京的圓明園到江南的園林,都可以看到它們。
我順帶分享一些辨識水鳥的粗暴秘訣,腦袋是綠色的,就叫它綠頭鴨;腦袋是紅色的,就稱紅頭潛鴨。如果它有點像雞,是黑的,不妨叫它黑水雞。如果你看到一只鳥,感覺好像是打亂了的調色盤一樣,那就放心大膽地喊鴛鴦,通常都是正確的。
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鴛鴦會結束在南方的越冬,回到北京。它們會在這個時候求偶。鴛鴦是在樹洞里面生活的,它們會飛到岸邊高大的柳樹上去考察洞穴,公鴛鴦總是非常紳士地站在一邊,等著雌鴛鴦一棵一棵樹地去考察。到了五月份,它們“結婚”了,結束了群體生活;六七月份,母鴛鴦會帶著小鴛鴦第一次游泳,第一次認識這個世界。
結婚之前,公鴛鴦都顯得非常強壯,油光锃亮,雄赳赳氣昂昂的,而結婚之后它們就憔悴了。我在北大的行為生態學課上,也講過同樣的故事。一個男生悠悠地說,老師,我覺得這反映了婚姻對于一個成年雄性的打擊。作為一個已婚的成年雄性,我不敢表示贊許。我想這是自然演化里邊最神奇的故事之一。
結束北大的學習生活之后,我到了上海工作。晚上在校園里,只要你保持安靜,經常可以聽到刺猬在地上拱來拱去發出的“呼啦呼啦”聲,它們沒有任何顧忌,也從來不想隱蔽行蹤,它們的刺讓它們覺得可以很安全地生活在城市里。
刺猬扎人嗎?這取決于我們怎么對待它。平時它們的刺都平平地貼在身上,比如在覓食的時候,或者是在母刺猬喂奶的時候。只有當它們受到了威脅或者傷害的時候,刺才會全部立起來。
不少人相信,刺猬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偷,會去果園里偷完水果,再扎在刺上帶走。當我去跟蹤刺猬觀察它的時候,發現它的糞便里是大大小小的金龜子和甲蟲的甲殼,里邊可能還有蝸牛殼,或者蜻蜓和蝴蝶的殘肢,刺猬實際上是敏捷的城市捕食者。
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觀察刺猬,就想搞清楚,在什么地方刺猬還能夠大量地存在,在什么地方刺猬已經消失。我發現在它們所生活的小園子中,最重要又最難得的東西,竟然是一點點清水。
為什么呢?因為每年三月份,刺猬會結束冬眠,冬眠的時候它們的肝臟會積累大量的毒素,所以等它們醒來時,最要緊的是大量飲水,促進身體的生理生化反應,把這些毒素降解掉。
這個時候,如果能夠找到清澈的水源,它們就能夠在城市里面生活下來,而如果在找水時,碰到的是鋪滿厚厚水泥的堤岸,是硬化的湖泊,那它們可能一口水喝不上,就毒發身亡,永遠地離開了城市。
所有動物都有一個基本生存空間,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動物的需求結合起來,在城市里,給它們安排一個適合生存的基本空間。清澈的流水,零星點綴的綠地,自由的灌木叢,旺盛的植被是基本元素,這也是我們在城市里生活得更美好所需要的元素。
如何與動物共處
我開始嘗試把這樣的空間在城市里變成現實。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發現忽略了一個關鍵環節:這樣的保護,可能并不是居民所希望的。很多時候和野生動物的共存,也會給人們帶來困擾甚至沖突。
2012年,我到美國進行博士后工作的時候,第一次體會到生物多樣性給人們帶來的困擾。剛到美國的第一個星期,晚上11點半,突然家門口傳來非常有規律的“嗵嗵嗵嗵”的聲音,沖過去發現,一個完全不曾設想到的場景正在我的眼皮底下發生。
浣熊用它靈巧的小手扒開門之后想把腦袋伸進來,但是伸進來的時候它需要把手縮回去,一縮手,門就撞上了。我以為沖過來四個人圍著它,它會退縮,直到它抬起頭的時候,我才明白它為什么一點兒不害怕。浣熊知道自己清澈目光的殺傷力,它也知道當它抬起頭用這樣的目光盯著我,同時用它的小手輕輕地扒拉我的褲腿時,我會做什么。最終它成功地把大肥屁股擠了進來。
我告訴自己,我是一個專業的野生動物研究人員,應該盡可能減少跟動物的直接接觸。這個想法非常強烈,但是我的身體非常誠實,我沖到廚房拿來了貓糧和水遞給它。
第二天我坐在辦公室里很不是滋味,我覺得我代表的是中國的野生動物研究人員,竟然在這個院子里面喂了浣熊。我對面的研究人員叫Tavis,我問他說,Tavis,咱們院有浣熊你知道嗎?你喂過它嗎?
Tavis很認真地抬起頭盯著我,隔了很久說,我有一個三歲的女兒,你希望我女兒怎么看我?
所以我跟Tavis一個一個辦公室去認真地核實這件事,沖進去第一句話就問:你不會喂了這只浣熊吧?而我們得到的是一連串肯定的回答。那一天我們決定,號召所有人一定要停止喂浣熊的行為,可以用笤帚甚至能想到的任何方法把它趕走。
但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只剛剛出生不到半年的浣熊,它第一次進到人類世界就嘗到了甜頭,它沒有辦法拒絕那些高鹽高糖高油脂高熱量的食物,所以當遭到集體拒絕之后,它練就了飛檐走壁的本領,順著高壓線進入到辦公室的閣樓中,打翻垃圾桶,打開冰箱。
兩星期后,它誘發了我們實驗室的大停電,現場慘不忍睹。這只浣熊在沿著輸電線爬進實驗室的過程中觸電身亡。
我們的行動晚了。當野生動物知道了人類的城市多么迷人之后,就有可能踏上不歸路。而如果我們第一天就能夠勇敢地拿起笤帚,能夠抵抗它的目光,它的命運就會改寫。
還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入侵的灰松鼠每年都會造成價值數百萬英鎊的森林的損失,并且正在摧毀歐洲本土的生態系統。在柏林,三千多只野豬到處沖撞,甚至造成人員的傷亡,并且還把豬糞噴灑在了從柏林一直到巴塞羅那廣闊的歐洲土地上,當地人對此苦不堪言。
城市是生物多樣性的樂土。隨著生態的恢復,生物多樣性會開始侵占人的生活,開始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那個時候我們又應該怎么辦呢?
城市的核心使命是滿足人們的生存需求,只有理解每一個人的需求,才可以更好地規劃城市。同時我們又不應該因為人的需求,就把動物全部殺光或者趕走。全部殺光的結果就是留下一個到處都是陷阱和毒藥的城市,破壞城市之中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
如果有一天,鳥類和人有沖突,青蛙和松鼠給人類帶來困擾,人類又該怎么做?
我們正在把所有人的意見匯總起來,和我們發現和掌握的生活在城市里的野生動物數據一起,建立一個開放的數據平臺。這個數據平臺可以顯示出什么地方缺一個池塘或者一片灌木叢,也可以顯示出什么地方出現更多人和野生動物的沖突,需要我們重新規劃社區景觀來進行調整。所有結果會開放給城市的園林、綠化、野地恢復部門。
我覺得二十年后的城市不僅需要生物多樣性,更需要把每個人多樣性的意愿融入到城市的生態建設里。在我心里一直有一個對這個世界的判斷,無論是生物多樣性,還是其他多樣性,多樣性不應該是我們的追求目標,恰恰是這個世界的本質。
(戴天養薦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