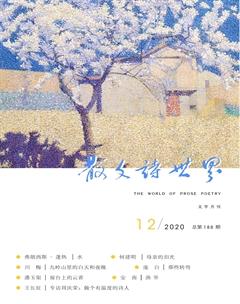專訪周慶榮:做個有溫度的詩人
周慶榮,筆名老風。1963年生于蘇北響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我們-北土城散文詩群”主要發起人,《大詩歌》主編、《星星·散文詩》名譽主編、《詩潮》編委、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湖州師范學院中國散文詩研究中心研究員。1984年開始詩歌寫作,出版的散文詩集有《愛是一棵月亮樹》《飛不走的蝴蝶》《愛是一棵月亮樹》《風景般的歲月》《周慶榮散文詩選》《我們》(中英文典藏版)、《有理想的人》《預言》《有遠方的人》《有溫度的人》。曾獲2014年度《詩潮》詩歌金獎、2015年《芳草》第四屆漢語詩歌雙年獎、2016年《星星》第二屆散文詩大獎、第二屆劉章詩歌獎、第七屆中國“冰心散文獎”和2019兩岸詩會桂冠詩人獎。
一、詩歌要表達不可被覆蓋性的意義
王長征:周老師你好!寫新詩的人成千上萬,你為何選擇散文詩這個文體?散文詩和新詩有什么不同?散文詩需要單獨定義嗎?或者說散文詩和新詩除了分行有別,與散文又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或者說散文詩傾向于散文還是詩歌?
周慶榮:從上個世紀初20年代開始,從事散文詩寫作的詩人、作家,一直困惑著這個問題,屈指算來已有一個世紀。我曾經舉過例子,玉米和高粱肯定不一樣,與麥子也有很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屬性——莊稼。如果從莊稼種類的意義去論證它是否重要,本身這個出發點就有問題,誰能回答出麥子一定比高粱重要,高粱一定比玉米更重要呢。要想知道哪些具體形式的重要性?首先要了解它們和土地、陽光、水分、空氣、勞動者的關系,然后看它們能不能適應土壤生長,克服人為的懶惰,抵御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是否能夠努力生長,進入糧倉,解決人們的溫飽。如果玉米能夠幫助人們解決饑餓,玉米就是偉大的莊稼。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都在出現,如何恰切地表達人與世界的關系,與生命的關系,與時空的關系,與社會實踐的關系?哪種文體能夠表達這種問題和它的不可被覆蓋性的意義,那么這種文體就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散文詩如果定義的話,絕不是簡單的散文和新詩的拼湊,其根本屬性都是詩,散文詩是一種更加自由、以文章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詩。所謂的更加自由,在于散文詩在關鍵時刻可以展開,圍繞寫作目標有獨特的發現,有具體意向性細節的描述。它無需分行,可以差轉、空靈、留白。散文詩也有留白,其留白在文字背后的隱喻,成立的部分就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論,所以我們讀偉大作家的散文詩,一定要在文字背后尋找發現一些讓人掩卷思考的東西,這些東西需要留給閱讀者去完成。散文詩可以直截了當揭露生活本質,即通俗意義上講的思想性,除此以外,它的自由度則更廣泛一些,長期以來我們習慣談中國新詩,好像只有分行才是詩,這是錯誤的,也是傲慢的。
二、心中有詩意的人萬事萬物皆可成詩
王長征:詩人是為個人寫作還是為社會寫作?作為當代散文詩最優秀的詩人代表,你認為這樣的討論有意義嗎?
周慶榮:我認為兩者并不矛盾,因為個人必須要與個人之外鏈接,這樣才會豐滿。一個人生命過程獨具世界空間,但同時個人經驗也是屬于社會的,詩人的創作對讀者有啟發。如果離開個人經驗,客觀上就是為他人寫作,那么作者的經驗就會空乏。有人認為:“放下我個人的經驗為讀者寫作”,那對不起,越是這樣,詩人的作品對讀者的影響、對讀者的啟發和教育意義就會越差,所以這兩個問題不應該成為矛盾,那些以任性絕對自我,把“我”看成是大于世界大于我之外,那就是《狂人日記》中的狂人,狂人可能有狂人的理解,但有著一般人的欲望。我還是秉持把個體經驗能夠熏染社會,能夠對他人有所啟發,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
王長征:有人說,現在所有題材在不斷地趨同。比如,詩性的小說,像沈從文的小說如詩一樣。還有小說性的詩,近年來,很多人在搞一些實驗性的作品,用分行詩或者詩句來寫小說,同時也有詩性的散文,散文性的詩,包括現在的分行詩也不像以前一定要講究格律,很多人覺得文學作品不僅在語言形式上,界限上都存在模糊化,你怎么看待這種情況呢?
周慶榮:對于心中有詩意的人萬事萬物皆可成詩,不能說是皆為詩。比如你一個人深夜站在黑暗中,感覺風刮在樹的枝頭,本身就可以產生詩意的聯想。詩意小說或者小說中蘊含著詩意,以及各種各樣邊界的一種模糊,恰恰是人們閱讀的范圍在擴大。像《荷馬史詩》《浮士德》等名著就是詩體小說。這種詩體小說人們依然把它當成詩歌去讀的,它有情節,有敘述,但它還是抒發情感,以詩意的呈現為主。雖然它所具備小說的力量,故事的力量,卻還是和經典的小說有所區別。我以前讀的《哈達爾詞典》,它類似于一個小說,但我從小說的詞典里讀出了散文詩的元素,因為它有很多句子思想深刻,它不是宗教的,不是哲學的,它只能是詩歌的,這本書一定不是詩。我們要從這些要素里面看出散文詩的一種更大的可能性,因為以文的形式更能走進閱讀。一首詩一旦分行,很多人對詩歌感到陌生可能都不讀,但他看到不分行的文章,覺得“這個我讀得懂”,感到不同于一般的平鋪直敘,紀實敘事,這里面有內置的詩意,所以邊際的模糊是必然的,這是個進步。隨著人們人們閱讀范圍的不斷擴大,要求大家走出各自的小天井,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在寫散文詩,當然隨筆也寫,由于時間關系就沒有去寫小說,假如有時間我也可以寫小說。這些一定要有門戶之見嗎?因為我熱愛散文詩我就排他嗎?你熱愛玉米,我熱愛麥子,不是否定高粱的理由。我們應該賦予它們平等生長的權利和自由。那么詩歌是什么呢?在現實的尊嚴下,你可以杜撰出一種精神尊嚴,用杜撰這個詞,就是一種能動的創造。
三、詩人要有所準備,迎接更大的遼闊和更多的新生事物。
王長征:請教一個關于網絡文學的問題。以前網絡文學好像是不入流的文學范疇,近幾年人們好像在不斷地重視它,一些專業作家進入到網絡文學提升了網絡文學水平。一提到網絡文學,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網絡小說。像網絡詩歌,很多人并沒有把它歸納到網絡文學,網絡詩歌是歸到詩歌的。現在很多省份每年都有網絡作家論壇,從沒有人談一談網絡詩歌,甚至官方組織的網絡文學研討會,前去參會的都是網絡小說家,為什么沒有網絡詩人歸進來呢?
周慶榮:網絡是新生事物,它是一種人類預言式的進步。網絡的出現,使得人類對更高級的文明這種事實和可能性有一個深刻的認知。當照相藝術出現的時候,傳統的表達世界畫面感的藝術家們紛紛反對,因為攝影技術對事物的形成畫面太快了,太快就否定了畫家的創造性,后來當攝影慢慢注入了人的藝術創作,當攝影成為有效的藝術語言,人們最起碼尊重了。因為人類文明的河流流到這里,它不轉彎也是河;它沒有漩渦也是河水,同樣流入大海。在人類的生活空間,下一步還會出現哪些新技術、新現象都是未知的。作為新時代的人,我們應該有什么呢?擁抱、接受、完善、豐富以及人物化、人本化。它一定和人文精神、以人為本的與人相關聯的東西,這些要加以評判它是否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詩歌不能忽視網絡傳播,網絡創作,網絡呈現,不管它快與慢,詩歌是需要才華性寫作,天賦性寫作,小說可能要過十幾年。如果哪位詩人告訴我,一首短詩寫了20年,那它一定不是詩歌。網絡有它的及時性,有場景聚焦對人的智慧、人的精神、人的藝術細胞的調動,瞬間的激發性,以及詩歌本身所具有的這種感染性。我們不能用網絡文學中一些失敗的、平庸的、一種應景的去界定,去定義什么是真正的網絡文學。比如說我認真寫的一首詩發送到朋友圈,它就是網絡詩歌,難道這個詩歌和我以前寫在紙上,然后再把它打印出來就有區別嗎?所以我覺得網絡文學不僅僅是改變了傳統寫作手段,也增加了人們的寫作條件,它告訴人們平凡人也能成為詩人,有成為文學家的可能,它完成了日常訓練,應該以予高度尊重。至于寫詩的,因為網絡文學經常把詩歌忽略,好像網絡詩歌這個詞不存在,不管你承不承認,網絡詩歌依然在那兒,就像詩歌存在于萬事萬物中,存在于無數人的心中。
四、詩人要找到創作的“引信”
王長征:現在很多刊物,如果把作者全部隱藏起來,發現大部分作品相差無幾,難以分清“個人風格”,你怎么看待當下同質化寫作?
周慶榮:所謂同質化是有類似近似值,表達的題材,敘事的方式,包括語言的習慣有很多相似。說明大家都在讀書了,你讀過的書我也讀過,為什么你能這樣用,我就不能這樣用呢?其實絕對的相同是不存在的,除非剽竊、抄襲。在個人經驗和普遍性經驗,沒有找到一個凸起的部分,這是個人經驗的敘述,詩人被平均經驗給遮蓋了,這就導致在寫作內容上的一種同質化。表達形式,尤其是散文詩,大家一開始缺少自信,好像必須羞恥,必須化妝,必須加以抒情,甚至必須美,必須短小精悍……這樣散文詩從形式到寫作方式上近似值過多。假如我們轉向對目標事物的本質探究,那么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萊特,道理就變化了。面前同一株棉花,有人把它當作花,有人把它當作溫暖,有人把它種到西伯利亞那些正凍得瑟瑟發抖的人群旁邊,這個語境和意義是不一樣的,所以說同質化不要怕,因為一個真正的寫作者無需何人提醒他,一定能寫出他獨有的發現、帶有自己體溫的東西,這才是寫作共性的偉大。之所以偉大,因為它帶有共性的震撼力。
王長征:周老師,剛才你提到借鑒問題,初學寫詩者喜歡借鑒,已經成名的詩人也喜歡借鑒,網絡上經常會爆出關于某些詩人的抄襲事件,那么在你的理解里,抄襲和借鑒怎么定性?
周慶榮:我從來不評論,因為我沒有時間去研究這個人作品的出處,我只主張詩人找到一個引信,就是雷管,里面怎么爆炸,煙花里面是什么形態,那是它自己的事。我得找到一個可以激發自己、完成自己創造的一個引信。在讀到傳統的夸父這個神話的時候,我寫了《夸父謠》,我就顛覆:憑什么我要追太陽呀?我背著太陽跑讓太陽追我行不行?這不是說放大自己,而是陽光照耀萬事萬物,人是萬物靈長,他不追求光明就沒有意義,只能說《夸父謠》是我寫作的引信,我特別注重發揮引信的作用。很多人讀了波德萊爾、愛默生、惠特曼、紀伯倫、泰戈爾,讀著讀著,那些彎彎繞繞的語言都有人家的痕跡。一位優秀的詩人要把任何歷史的、哲學的,其他廣泛的經驗化為屬于自己的東西。我這么多年讀了很多書,說得不謙虛一點,讀得非常寬泛,包括哲學的、藝術的甚至建筑的、歷史的、國外的經驗。我對自己有個要求,讀任何東西,絕不允許馬上寫東西,因為有閱讀痕跡,一定要學會化解,避免重復與雷同。
王長征:你怎么看待詩歌的趣味性和想象力?
周慶榮:每個人的趣味各異,酸甜苦辣咸。對于我來說是苦的,以苦為美的人就是甘甜的,所以趣味本身不是趣味的字面意義,有趣的趣,風趣的趣,它是生動的。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為人們審美的一種風格或者取向,這種志趣、情趣,而不僅僅有趣。因為趣味也可以用荒誕、詼諧、幽默、自我解嘲去表現。因為很多藝術流派自我解嘲,是從冗長、枯燥、無奈、沮喪中找出一種突圍方式,然后形成一種有趣的形式來幫助自己走出某種困局。實際上,一個有趣味的人有能力走出生活的困境,走出生活的沉重。至于想象力,人類的偉大在于能夠突破自己,能夠有一種把遙遠的放在眼前,把未來的提到眼下,把兩者完全不相干的事物并列,把一棵草和另外一棵草,不是當成一種委屈的匍匐,而是想象到他們手拉在一起。通過這些想象和敘述,幫助我們重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想象力是基于現實、實踐的需要,想象才能有用。當然我所說的使用而不是實用,在表達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五、寫作是一種自我鼓舞
王長征:古代的文人講究氣節,仗義執言,很有原則性,現在的文人相對來說,面對種種誘惑似乎更容易妥協,你認同嗎?
周慶榮:我不認同。因為每人身上都有了不起的智慧、靈性,同時也一定擁有卑鄙、齷齪、絕望,沮喪,黑暗、告密。寫作是一種人類生活,一定不要把它寫成偽道德書,一定要寫成生活。雖然我的生活空間很小,但是我舉目四望,蕓蕓眾生就是這么回事。詩人體驗越豐富,到最后就越能夠守得住寂寞,越能夠在無數真實中萃取出來需要的那份真實。
王長征:你的詩歌不僅有一種詩歌文本的意義,還有一種公共話語的意義,你在寫作時有擔當感嗎?這個擔當感就會使文本產生一種更深的意義和厚重感。這些東西是現在年輕作者所缺乏的嗎?
周慶榮:嚴格的來說,我的讀者可能有60%是不寫詩不讀詩的。他們之所以愿意去讀我的作品,是因為傷心、沮喪、絕望的時候,我把嘆息留在無人處供他們閱讀。思來想去還是要把一切冷的東西轉化為自己可能需要的暖,如果你連自己都暖不了,連這個嘆息都規避不了,那么誰給你權利讓跟你同時生活、存在的人群一起痛哭流涕?你沒有這個權利。從這個角度來講,并不是說我忽略了嘆息也是真實的,痛苦也是真實的,絕望也是真實的,或者說苦難,這些都是人必須要體驗的內容。對我來說,把這些苦難盡收眼底,在寫作方向和文字的氣質以及內核上,我要讓人有能夠走向種種真實的希望和通道,這不僅僅是寫給別人看,而是通過寫作渡自己。有了這種自渡,渡人才能為可能。
王長征: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關注一些比較深刻的主題。你怎么看?
周慶榮:年輕人是個相對的群體,年輕人也會長大,臉上都會有皺紋。人處于三維空間,時間是四維空間,很多東西需要時間去驗證。年輕人可能更注重生命內容的生動性和真實呈現。任何文學作品,一定帶有作者的主觀意愿,如果沒有情感,就是一個冷面人嗎?不是這樣的。我希望饑餓中的人一出生就在一個裝滿稻谷的糧倉邊,一輩子不挨餓。我希望他省略所有的播種耕作、治理病蟲害、澆水的過程,但是當你這樣表達的時候,那你是不是就委屈了那些好不容易享受莊稼收成的人?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這些勞動過程對他們來說不就是委屈了嗎?所以說,就看你怎么去呈現,真正的抒情力量,可能是在減去了抒情形式的過于夸張才能讓這種抒情讓人覺得可信。
六、每位詩人首先是人
王長征:詩歌是你的第二職業,或者說是個人愛好,兩者之間有什么聯系,你怎么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有沒有那么一瞬間,你覺得他們之間有巨大的關聯?
周慶榮:職業解決了生存需要,我把它理解為生活的真實,比這更加真實的是自己精神的脈象。兩者之間肯定有矛盾,像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都有一種深刻的理想主義,有樂觀也有悲觀的,所有這些都焦慮著,有時候反差能自我化解。現實生活中一個又一個事實的介入,這種矛盾不可避免。我把閱讀、寫作當作是一現場的有機觸動,幫助我去和解,這個和解并不是妥協,斗爭也是一種和解,比如說遇到很多人性的貪婪、功利、人性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守信用,我需要找到支撐,幫我走出困境。
王長征:一個人的身份是企業家,可不可以稱之為“企業家詩人”?還有“草根詩人”“民間詩人”,或者“官員詩人”“學院派”這些不同的身份。你怎么看待詩人身上這種標簽?你反對個人標簽化嗎?
周慶榮:所有的標簽都是人為賦予的。我更看重不管從事什么職業,首先是寫出來的詩歌,不管用口語的還是學院體,用鄉村主義與還是用意識流,那是藝術的豐富性。所有這些豐富性最終歸為一點,就是詩歌這個藝術能不能產生作用,產生什么意義?所有的技術和標簽都是為詩歌實現其真正的閱讀意義。我不主張“我就寫我的”,否則這個詩人寫的詩對社會又有什么貢獻呢?所謂的標簽,每位詩人首先是人。比如,我認識了高粱、麥子油、菜花,油菜花在蠶豆邊上,那么我也不能否認蠶豆呀。如果詩歌寫作讓我們人都不像人了,詩歌還有什么用?我對某些人那些亂七八糟的哲學是不加評論的,不加評論不是說我沒有態度,不是說我不敢斗爭。我見過很多自以為是的人只能敬而遠之。我寫散文詩,一開始也有很多人覺得分行應該怎么樣,后來時間長了,只要你的文本里有那么一點意思沒有被別人覆蓋,別人最終會承認你的。
王長征:你的寫作狀態,是提前有計劃,還是隨機性的?你認為50年之后,詩歌的表現主題會是什么?我們經常提到小說中的魔幻現實主義,你覺得魔幻現實主義跟詩有結合的可能嗎?這種結合會是一種什么的樣子?
周慶榮:詩本身已經有魔幻的味道,所謂的魔幻就是一般稀松平常的現象在真正的詩人面前變得非常有意味,非常有延展性,會產生“趴在一個被忽視的角落里產生的一種幻想”。你說它魔幻不魔幻?魔幻就是神奇,就是點石成金。魔幻不應該被作為一種寫作流派,它具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很多詩人都具備這種能力。
從個人寫作來說,除了少量的作品我有規劃,比如寫《詩魂》《我們》,為什么我把它變成一個散文詩劇,把屈原、岳飛等人放在一個舞臺上演,這本身就是對以詩歌為代表的中國歷史長河里文化現象作一個探究和梳理。這些梳理雖然有些牽強,但這些詩人和詩歌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緬懷并且發揚光大。對這些詩人,他們曾經的命運在今天可能依然被重復,也感到一種旗幟鮮明的態度。比如岳飛,他只懂打仗,不懂得背后放箭,不懂得爾虞我詐。當下同樣面臨很多問題,詩人要寫任何朝代的東西必須和當下進行鏈接。這些是有某種規劃,更多的是有感而發。比如生活當中遇到過一些事我可能以一種象征隱喻的方式通過詩把它們轉化,也是做了一個詩歌筆記,記錄下這個時代。
七、知識分子要有所擔當
王長征:有些詞使用頻率越來越少,比如說文化人、知識分子,而是更傾向于意見領袖,你對自己的標簽怎么認定?在“人學”方面怎么自我評價?
周慶榮:我還真沒有進行過多的思考,希望每個人都是讀書人,都是知識分子。我們不要因為概念的寬泛化來否定這個時代還是有認真的讀書人,也不要從知識分子被洪水化,因為大家都有知識了,干嘛還要后面加一個分子呢?我們所說的中國真正的文人是在精神獨立性、體內的故事和人的一種風格。去年在北大演講,我得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的認同,我必須找個角度,北大的人在當下應該怎么做,不是隨大流。搞國際關系的人搞外交很容易縱橫捭闔,我旗幟鮮明地講,首要的任務不是縱橫捭闔,不是叱咤風云,而是不斷提醒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祖國要呵護好每一個子民,永遠奮發圖強。天下興亡,匹夫繼續有責。為什么講繼續?因為很多人都麻木了。在這里,我提出為什么準備一百次嘆息,一千次忍耐,一萬次堅持,以及一生的善良。人不是說自我欺騙,而是必須要學會自我鼓舞,給自己鼓勁,說得通俗一點,只有自己救自己,自己治療自己,不要指望別人去發善心去救你。這是我們和詩歌寫作關系不大的,之所以現在很多人的詩歌不接地氣,看上去就像學院派但是讀多了倒胃口,因為有好些東西讀來讀去對我們沒用。
八、讀者都會培養、訓練出自己的甄別力
王長征:你怎么看待閱讀代溝和閱讀層次?
周慶榮:任何情況都會出現,因為書太多只能有所選擇。年輕的時候準備談戀愛,肯定閱讀各種青春文學。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的人注定閱讀的豐富性,我們讓一個經濟學家去背唐詩宋詞,讓一個研究導彈的科學家天天去研究西方的相對主義,那導彈怎么辦?導彈會受委屈,因為這些東西都很正常。
王長征:你怎么看待讀者的依賴性?如果有人讓你推薦一些優秀的詩人或者詩作,你會從哪幾個方面考慮?要照顧讀者的依賴性嗎?你推薦的考量方式是什么?
周慶榮:依賴性是每個讀者在一定環境下都會有甄別、選擇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普通人補充自己精神或者知識的某種需要。你說的依賴性的確存在,很多人沒有主動去選擇和甄別,人都有一種趨同性。比如說,聽別人的引導和公共輿論,看到這一階段哪些詩作火了就找到這個人,但是并沒有認真進行探究好在哪里,是不是自己所需要閱讀的東西,這個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人其實都有惰性的,都想走捷徑,想省去勞動的一部分。我們要相信到一定程度,每人都能培養、訓練出自己的甄別力。第二,你所講的推薦哪些書有效,我推薦最多的是前南聯盟的一位小說家叫帕維奇,他寫的《哈扎爾辭典》,我推薦給很多人。
王長征:你從哪種角度來推薦這本書呢?
周慶榮:很難說理由,這本書和我個人產生了某種關系,我感到愜意,可以掩卷深思,讓我經常想著每個人是否應該堅持,如何看待自己有限的甚至平凡的生存。這本書一方面本身和宗教的宣揚是有關聯的,但已經遠遠超出宗教本身。它走到了人的一種堅持和人實現自己堅持的勇氣和能力。那些過分口水的、暗淡的、云山霧繞的書,都不在我的推薦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