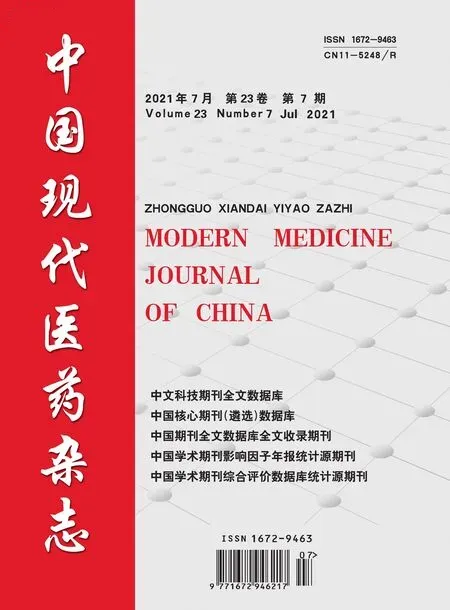內皮功能障礙在腦白質病變中的作用機制
劉璇 冷慧層 尹榕
作者單位:1 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九四〇醫院神經內科,甘肅 蘭州 730050
2 寧夏醫科大學臨床學院研究生院,寧夏 銀川 750004
腦白質病變(WML)又稱腦白質疏松(WMH)或腦白質高信號(WMHs),最初是由加拿大神經學家Hachinski 等[1]提出的一個影像學名詞。影像學上表現為磁共振T2 加權或液體衰減反轉恢復(FLAIR)序列上的高信號[2]。WML 是腦小血管的缺血性改變,表現為星形膠質細胞增生,少突膠質細胞損傷以及髓鞘丟失[3]。因其發病隱匿,早期大多無法察覺。隨著疾病進展,會引起精神、記憶、運動功能、認知障礙以及大腦皮層萎縮。WML 的嚴重程度可能代表了小血管的整體病變范圍,從而影響腦梗死的預后[4],引起血管性認知障礙(VCI)。目前WML的危險因素和發病機制尚不清楚,主流觀點認為其由高血壓或慢性低灌注引起的白質缺血所導致[5,6],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實驗模型中,慢性低灌注白質區域的主要微血管病理改變是內皮細胞損傷[7]。在人類WML 中,已報道了內皮標志物的表達降低以及血漿蛋白滲入小動脈壁引起白質損傷的證據[8,9]。
1 血管內皮
血管內皮是覆蓋血管內表面的單層細胞,人體內的總面積約為350m2[10]。血管內皮能夠通過產生多種因素調節血管張力、細胞粘附、血栓阻力、平滑肌細胞增殖和血管壁炎癥。內皮是一種動態器官,是血液和腦組織之間的物理屏障,在控制血管功能方面具有多種關鍵作用,由于其發生功能障礙,在許多血管疾病的潛在機制中也發揮重要作用。血管內皮細胞被認為是血腦屏障(BBB)的核心組成部分[11],也是血管內環境穩定的主要調節者,因為它們與循環細胞和血管壁中的平滑肌細胞相互作用[12],調節腦血流(Cerebral blood flow,CBF),控制血漿滲透性,并影響血小板和白細胞的粘附和聚集。
2 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在WML 中可能的作用機制
內皮細胞功能的改變是小血管病理生理變化發展的前奏,WML 的病理改變可能始于內皮功能障礙,有研究表明,人腦微血管內皮功能障礙的表現主要包括BBB 損傷、血管舒張受損、血管硬化、血管反應性受損、神經血管單元(NVU)結構及功能損傷等[13]。但上述過程中哪個占主導,哪些是可逆的,尚無定論。內皮功能障礙作為WML 的始動因素,對BBB、NVU 以及CBF 調節的正常生理功能產生嚴重不良影響,也可以促進腦白質病變的發展以及臨床并發癥的發生。
2.1 內皮功能障礙與血腦屏障損傷BBB 是一種有效防止有害物質和大分子進入大腦的屏障,主要由周細胞、內皮細胞、緊密連接蛋白、毛細血管基底膜及星形膠質細胞末端組成[13]。從結構上看,內皮細胞(CECs)是BBB 的核心組件,具有特定的功能[11]。內皮細胞緊密連接蛋白的破壞及功能障礙將破壞BBB 完整性,導致血液成分外滲,引起腦白質的彌漫性改變。一項澳大利亞的研究表明,與正常白質相比,內皮完整性的降低與WML 嚴重程度的升高獨立相關,并且與WML 區域的內皮和BBB完整性顯著降低有關[9]。一項磁共振成像研究發現,正常白質BBB 滲透性增加的區域是WML 易于形成的區域;此外,還發現在正常白質中以及WML區域邊緣均發生病理性BBB 變化,提示WML 是一個彌漫性的病理過程[14]。Qin 等[15]觀察到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通過周細胞中的NOTCH3/NF-κB 信號通路誘導其分泌MMP-9,從而加速血管內皮的損傷,引起BBB 通透性增加,促進血液成分向血管周圍間隙滲漏。這一過程在WML 的發展中也起一定的促進作用,如血液中的纖維蛋白原通過損傷的BBB 后被裂解成纖維蛋白,激活小膠質細胞并募集周圍的巨噬細胞,促進炎癥反應[16]。此外,纖維蛋白原也可阻止少突膠質細胞前體細胞成熟從而抑制軸突的形成和修復,并進一步結合淀粉樣蛋白β,阻斷其清除并促進淀粉樣蛋白β 斑塊的形成和周細胞損傷[16]。這些過程都會導致WML 的加重。研究結果支持了BBB 功能障礙參與腦小血管病(SVD)相關的WML 發病機制的觀點,內皮功能障礙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鑒于BBB 是由內皮細胞組成的,血管炎癥反應和內皮細胞的破壞會導致BBB 分解,增加其滲透性,并允許潛在的有害毒素和免疫細胞進入大腦。反過來,這一結果又會改變小血管的結構與功能,從而導致腦白質病變的形成。
2.2 內皮功能障礙與炎癥反應炎癥是抵抗有害物質入侵機體和維持體內穩態的有效防御機制。近年來,“炎癥性”的概念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它是指機體中的慢性無菌性低等級炎癥,并參與了各種與年齡相關的慢性疾病的發展[17]。研究表明血管炎癥標記物與WML 之間有很大的相關性[18]。雖然目前的研究還無法確定炎癥是WML 導致的還是由WML 繼發的,但基礎研究表明內皮功能障礙相關的炎癥反應是參與小血管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機制[18]。促炎細胞因子損害內皮細胞和BBB 的功能,并誘導粘附分子和招募白細胞的趨化因子的表達,導致炎癥、內皮功能障礙和缺血損傷[19],加速了WML 的發展。
內皮活化的特征是E 選擇素、P 選擇素、細胞內粘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ICAM-1)和血管細胞粘附分子-1(Vascular 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VCAM-1)增加或重新表達[20],可通過測量釋放進入循環的這些生物標志物來評估內皮功能障礙。此外,在基于社區的人群中,較高的ICAM-1 水平與3年和6年后WML 和腔隙性梗死的進展相關[21]。粘附分子在激活時由內皮細胞表達,它們能夠與循環中的白細胞相互作用[22],作為白細胞-內皮細胞相互作用的結果,內皮細胞和白細胞(如單核細胞)都變得越來越活躍。因此,ICAM-1 似乎是腔隙性腦梗死和白質病變的一個重要標記物。另一個被廣泛研究的炎癥標記物是同型半胱氨酸,它被認為會誘導內皮損傷,是動脈粥樣硬化的危險因素[23]。現有的研究表明,在與年齡相關的“缺血性”白質病理學中,與周圍正常的白質相比,炎癥是WML 的一個明顯特征,其中微膠質激活增加與血腦屏障的改變可能具有促炎作用[24]。因此,炎癥過程除了對慢性缺血和衰老有影響,還可能導致缺血性腦白質的病理損傷。
2.3 內皮功能損傷與神經血管單元功能障礙NVU由微血管(內皮細胞-基底膜基質-周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末端)、星形膠質細胞、神經元及其軸突,以及其他可能調節“單元”功能的支持細胞組成[25]。NVU 各組分之間的信號通訊不僅確保CBF 的精細調節以滿足代謝需要,而且在大腦發育、營養和修復以及BBB 功能中發揮重要作用[26]。上述細胞及功能成分的異常都可能在WML 的發展中起推動作用。星形膠質細胞作為神經元與腦血管之間的媒介,在神經血管單元中具有重要功能。神經元活動后,星形細胞向內皮細胞發出信號,增加局部血流并確保能量供應[26,27]。在生理和病理條件下,腦內皮和神經血管單元內星形膠質細胞之間的特定相互作用可以影響BBB[28]。Bailey 等[29]的研究還提供了膠質-內皮相互作用和BBB 泄漏發生改變的證據。功能異常的血管內皮會損傷星形膠質細胞末端并影響其正常功能。Rasmussen 等[27]發現星形膠質細胞足底的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AQP4)重新定位及功能異常,造成BBB 損傷而引起WML。AQP4 被用來評估星形膠質細胞的極性,而星形膠質細胞極性降低引起的BBB 功能障礙可能是WMH 的開始[30]。有證據表明,星形膠質細胞分泌的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在腦白質缺血性損傷的恢復過程中促進少突膠質前體細胞成熟[31]。功能障礙的內皮細胞通過分泌內皮細胞釋放因子,影響少突膠質細胞的存活,使其易于受損[32]。有研究在人類WML 的組織病理學模型中進一步證實,功能紊亂的內皮細胞可阻斷少突膠質前體細胞的成熟,從而損害軸突髓鞘形成和髓鞘修復[27]。因此,CECs 不僅在結構上是BBB 的主要成分,而且在功能上也是NVU 活動的關鍵環節。NVU 的功能障礙可能是神經損傷和神經功能障礙的基礎[33,34]。
2.4 內皮功能障礙與腦血流量受損內皮細胞已經成為血管穩態的關鍵調節劑,因為它不僅是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作為一種血管活性信號傳感器來調節和改變血管壁的功能,進而影響CBF。CBF 受損是內皮功能障礙的另一種表現[13],也是導致WML 的一大危險因素。腦室周圍區域的腦白質因缺乏側枝循環,對腦血流動力學的改變及大腦低灌注特別敏感[35],腦血流調節可能與腦血管反應性(Cerebrovascular reactivity,CVR)以及NO 介導的氧化應激相關。
2.4.1 與腦血管反應性相關的CBF 受損 CVR 是小動脈和毛細血管對神經元活動增加或代謝作出反應而擴張的能力[36]。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慢性高血壓的出現,大腦血流量的自我調節能力會喪失,導致大腦小動脈的流速和搏動性增加,這些血液動力學變化將導致血腦屏障的大腦內皮損傷,并通過剪切應力的增加改變其通透性[37]。Wenzel 等[38]通過大鼠研究發現一種內皮H+受體GPR4,和內皮Gαq/11 蛋白介導了CO2/H+對小鼠CVR 的影響。研究表明,CVR 降低可能預示著正常出現的白質向白質高強度的發展[39]。有報道無癥狀的老年WML患者的CVR 較低,提示WML 與腦血管功能失調及腦血流受損相關[40]。輕度卒中伴WML 的患者腦白質中CVR 較低而血管搏動性較高[41],提示與靜息腦血流量減少相比,CVR 降低及血管搏動性增加可能與腦白質病變的關系更密切。
2.4.2 氧化應激對CBF 的影響 NO 對內皮有保護作用,并促進血液流動,特別是在小血管循環中[42],血流量的自我調節依賴于內皮釋放的NO。在正常情況下,內皮一氧化氮合酶產生的NO 擴散到下面的平滑肌,刺激可溶性鳥苷酸環化酶,導致循環GMP水平升高,隨后平滑肌松弛和血管擴張[43],進而調節腦血流量。內皮功能障礙時,激活血管內皮的氧化應激反應,抑制NO 的生成,并使其生物利用度降低,微循環的腦血流自我調節受損,從而促進腦組織中神經退行性改變[44]。氧化應激反應會進一步加速內皮損傷,血管內還原物質減少和氧化物質增加是內皮損傷的關鍵因素[45]。缺血后的周細胞收縮和死亡也是由氧化應激介導的[46]。相關研究發現周細胞會顯著改變毛細血管直徑,從而潛在地調節毛細血管水平的腦血流量[47]。CBF 調節受損導致的大腦微循環缺血,在WML 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3 結語
WML 是大腦微循環的缺血性改變,病程緩慢,發病隱匿,早期不易察覺。因其發病機制復雜,目前的研究對其病理與生理方面的了解仍不完全。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內皮功能障礙在WML 的發病中起著重要作用,與血管內皮功能失調相關的BBB 損傷、NVU 結構破壞及功能障礙、氧化應激、CVR 受損等,共同促進了WMH 的形成。WML 是老年患者血管性認知功能障礙的主要病因,目前的觀點認為小血管疾病是動態的全腦性疾病,WMH不僅是常規核磁成像上可見的病變,缺血性腦白質束的損傷也可能對遠隔部位的正常腦白質區域的微結構產生影響。對WML 患者的早期發現及及時干預是減少臨床不良預后的關鍵,因此對疾病發病機制的研究在未來可能對WML 的預防和治療提供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