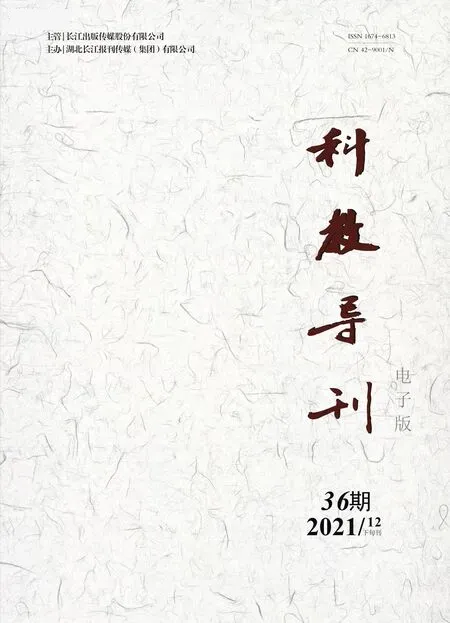《沒有個(gè)性的人》中性格喪失母題的研究
陳冬碩
(江蘇理工學(xué)院外國(guó)語學(xué)院 江蘇·常州 210003)
奧地利作家穆齊爾的長(zhǎng)篇小說《沒有個(gè)性的人》中,卡卡尼王國(guó)舉傾國(guó)之力策劃組織慶祝皇帝登基70周年的平行行動(dòng),這本該是擔(dān)任籌備委員會(huì)秘書的男主人公烏爾里希大展宏圖的良機(jī),然而小說主人公在故事情節(jié)的開始便做出了一個(gè)奇特的決定——做一個(gè)沒有個(gè)性的人。有個(gè)性與無個(gè)性是貫穿小說中各式人物圍繞平行行動(dòng)進(jìn)行的思想交鋒的論題,而性格喪失這一現(xiàn)象及含義也成為了這部未完成的作品的母題。
1 性格獨(dú)特性與穩(wěn)固性的喪失
“性格”一詞源于古希臘語,它的本義是“壓鑄的圖案或文字”并含有深厚的道德內(nèi)涵。亞里士多德學(xué)派的提奧夫拉斯圖斯以“具備美德”與“惡習(xí)難改”等標(biāo)準(zhǔn)評(píng)價(jià)一個(gè)人的性格。這一概念被法國(guó)哲學(xué)家、道德家拉布呂耶爾進(jìn)一步發(fā)展,在十八世紀(jì)的歐洲文獻(xiàn)中,“性格”被詮釋為“一種可以同時(shí)展現(xiàn)時(shí)代精神的個(gè)人的道德基準(zhǔn)”。伴隨著心理學(xué)的發(fā)展,“性格”一詞被賦予更多的心理學(xué)含義,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日常話語中,德國(guó)心理學(xué)家萊爾施(P.Lersch)和托馬斯(H.Thomae)將其定義為“人類單一個(gè)體所具備的深刻影響其行為舉止,并將其與其他個(gè)體區(qū)分開來的獨(dú)特性狀”,“一種持久的、憑借規(guī)范的準(zhǔn)則阻止沖動(dòng)的心理狀態(tài)”。[1]
從性格定義的演變不難看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性格具備兩個(gè)顯著特征:獨(dú)特性和穩(wěn)固性。性格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區(qū)別的個(gè)體獨(dú)有的心理狀態(tài)及思考、行為模式。性格雖被認(rèn)為可以改變,但它在一個(gè)相對(duì)較長(zhǎng)的階段內(nèi)作為指導(dǎo)個(gè)體行為的基準(zhǔn)處于一種穩(wěn)定的狀態(tài)。
正是性格的這兩種標(biāo)志性特征在《沒有個(gè)性的人》中被大大弱化了。小說開篇便以一種背離傳統(tǒng)的解釋對(duì)作為故事背景的卡卡尼國(guó)王的國(guó)民們的性格做出了如下表述,“……居民至少有九種性格,一種職業(yè)的性格,一種民族的性格,一種國(guó)家的,一種階級(jí)的,一種地理上的,一種性的,一種意識(shí)到的,一種沒意識(shí)到的以及也許還有一種私人的性格。”[2]性格在穆齊爾的筆下不再具有個(gè)體的特性,而是按照行業(yè)、民族、國(guó)家、階級(jí)等集體的范疇被分門別類。與前八種性格相比,最后一種性格尚帶有“私人”的性質(zhì),然而作家隨后指出,這第九種性格其實(shí)容前八種性格于一身,并很容易被這八種性格溶解。它被形象的比喻成一塊匯集許多涓流的小洼地,那些涓流流入洼地繼而流出,又同別的涓流一道注入下一個(gè)洼地。通過這個(gè)比喻不難看出集體的特征對(duì)于個(gè)體的特性發(fā)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穆齊爾同時(shí)也對(duì)性格的穩(wěn)固性深表懷疑。早在《沒有個(gè)性的人》第一卷發(fā)表的九年之前,穆齊爾便在一篇隨筆中反對(duì)將性格詮釋為持續(xù)穩(wěn)定的心理狀態(tài)。親身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經(jīng)歷使他相信,作為個(gè)體的人很容易隨著環(huán)境的改變從一個(gè)極端走向另一個(gè)極端并循環(huán)往復(fù)[3]。在小說中,幾位主要人物成為穆齊爾這一觀念的代言人。男主人公烏爾里希不再將在性格定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道德視作固定的規(guī)章,而是視作一種游走于各個(gè)要素之間的靈活的平衡。無獨(dú)有偶,經(jīng)常站在烏爾里希對(duì)立面的阿恩海姆于此點(diǎn)上卻與自己的對(duì)手不謀而合,他將人比喻成剝?nèi)ネ鈿さ亩嘀乃瑑?nèi)在柔軟而易破。而另一位人物,銀行經(jīng)理費(fèi)舍爾連連感嘆自己內(nèi)心的無定形性,它總是緩慢但永無休止地變換著形態(tài)。
由此可見,《沒有個(gè)性的人》中性格喪失這一主題首先寓意著性格中作為個(gè)體特有的典型性特征的消弭和內(nèi)心狀態(tài)不穩(wěn)定性的增加。當(dāng)性格中融入了過多集體的,共性的特征且易隨著外界改變時(shí),性格便更多的屬于一個(gè)群體概念而非某個(gè)單一個(gè)體,單個(gè)社會(huì)成員之間的差異變得愈加模糊。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主人公烏爾里希自稱為“沒有個(gè)性的人”并非因?yàn)樗痪邆淙魏涡愿瘢侵杆鶕碛械男愿褚殉搅藗€(gè)體獨(dú)有特征的界線從而無法確保他個(gè)人身份的認(rèn)同。
2 性格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失效
性格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小說中被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外界環(huán)境對(duì)個(gè)人性格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而從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角度出發(fā),作為習(xí)慣性心理活動(dòng)的性格同時(shí)也對(duì)改造現(xiàn)實(shí)發(fā)揮著作用。這種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對(duì)卡卡尼民眾九種性格的描述中也得以體現(xiàn),如國(guó)家民族、地理環(huán)境等外部因素成為劃分不同性格的標(biāo)準(zhǔn),而具有這種由外界標(biāo)準(zhǔn)劃分而成的相似性格的人則被歸為同一群體。小說主人公烏爾里希對(duì)于性格對(duì)外界的依賴了然于胸,他在審慎思考后得出,“一個(gè)行動(dòng)或一種個(gè)性的價(jià)值,甚至連它們的本質(zhì)和天性都有賴于它們周圍的客觀情況。”烏爾里希深知,性格并非孤立封閉在自我中,而是隸屬于人立身的環(huán)境的“總體”。[2]現(xiàn)實(shí)世界是展現(xiàn)性格的舞臺(tái),只有當(dāng)個(gè)體通過行為將個(gè)性展現(xiàn)給外界時(shí),個(gè)性才得以被其他人認(rèn)作為該個(gè)體獨(dú)有的特征。換言之,個(gè)體獨(dú)特的行為、思考方式只有通過與其他個(gè)體的比對(duì)才能得以印證,而這種比對(duì)的前提是在現(xiàn)實(shí)中將個(gè)性展現(xiàn)出來。
然而正是這種展示性格的過程在烏爾里希身上受到了阻礙。他有著獨(dú)到而深刻的思想見解,卻很難將他的想法付諸實(shí)踐。烏爾里希被描繪成一個(gè)“以驚人的敏銳看到自己的時(shí)代所寵愛的能力和個(gè)性,卻失去了運(yùn)用它們的可能性”[2]的人。無法運(yùn)使個(gè)性的原因在于烏爾里希奇特的生活方式,在故事開始,他便選擇了向自己的生命告一年的假,以一種徹底冷眼旁觀的姿態(tài)審視著外界,他在頭腦中不停醞釀著思想風(fēng)暴,卻失去了參與到現(xiàn)實(shí)世界任何事件中的興趣。他的人生并非參與到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而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深刻反思。
由此可以看出性格喪失這一主題還有著另一層寓意。性格的展現(xiàn)取決于個(gè)體與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有個(gè)性的人”積極投身現(xiàn)實(shí)世界并能在同外部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現(xiàn)個(gè)性,“沒有個(gè)性的人”與現(xiàn)實(shí)世界保持著距離,甚至格格不入。在這種意義上性格的喪失等同于性格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失靈,它只存在于主體的內(nèi)心而失去了改造現(xiàn)實(shí)的能力。對(duì)于性格喪失的這種詮釋可以追溯到中世紀(jì)德國(guó)神學(xué)家、神秘主義者埃克哈特。埃克哈特認(rèn)為每個(gè)人的內(nèi)在都具有一種接近神性的“根本”,它埋藏于多重世俗人性之下,常人很難領(lǐng)悟。人的性格與世俗生活捆綁在一起,成為人與上帝之間的阻礙,若想接近神性,則必須舍棄世俗的性格。[4]在埃克哈特的學(xué)說中喪失性格具有積極意義,穆齊爾自1900年起便對(duì)神秘主義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他曾深入研究埃克哈特的學(xué)說并為其打動(dòng),但在《沒有個(gè)性的人》中,他削去了個(gè)性喪失的神學(xué)意義,轉(zhuǎn)而將其描述為小說主人公的一場(chǎng)主動(dòng)脫離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人生試驗(yàn)。
3 時(shí)代特征及其對(duì)性格的影響
無論從集體觀念對(duì)性格的影響還是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同性格的互動(dòng)性來看,個(gè)體性格的形成或消弭均與個(gè)體身處的時(shí)代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對(duì)烏爾里希而言,他身處的環(huán)境宛如僵硬的墻壁,他將現(xiàn)實(shí)世界形容為幽靈出沒的世界,其與時(shí)代環(huán)境對(duì)立之深可見一斑,正是這種外部環(huán)境為他立志做一個(gè)沒有個(gè)性的人推波助瀾。烏爾里希身處的時(shí)代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gè)方面。
3.1 無序的碎片化時(shí)代
小說第一部分第八章節(jié)描繪了一幕對(duì)現(xiàn)代化都市生活場(chǎng)景的憧憬。這座大都市如一條巨大的流水線一般由無數(shù)細(xì)小的交通樞紐和交通工具維系,某一條線路上完成的運(yùn)作不過是巨大城市體系中一道細(xì)小的工序。市民的生活被割裂為工作、戀愛、休閑、家庭等部分,每個(gè)部分都因時(shí)空限制與其他部分孤立開來。行為的連續(xù)性和完整性被徹底打斷,市民們宛如一臺(tái)機(jī)器上的微小零件在不停地運(yùn)轉(zhuǎn)著。這一幕雖為虛構(gòu),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大眾群體的價(jià)值觀與生活愿景。
烏爾里希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這種碎片化的沖擊。他的居所,那座小小的“城堡”集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建筑風(fēng)格于一體,反而顯得不倫不類。在十七至十九世紀(jì)各種建筑風(fēng)格的雜糅下,住宅的整體風(fēng)格徹底瓦解。當(dāng)他因調(diào)節(jié)警察與路人的斗毆失敗而被警方拘留審問時(shí),他個(gè)人也被分解成諸如姓名、年齡、職業(yè)的不同標(biāo)簽,它們并不包含烏爾里希任何的人生經(jīng)歷與思想,僅僅是官方記錄中一串空洞的符號(hào)。經(jīng)歷過這次審問后,烏爾里希除了自我的分裂和崩解之外一無所感。
3.2 大眾社會(huì)
穆齊爾在小說第一章便描繪了一個(gè)反個(gè)體的大眾社會(huì)。文中的天氣并非由“冷”“暖”等個(gè)體感知性詞匯來描述,而是通過一系列抽象的氣象學(xué)與天文學(xué)術(shù)語播報(bào)。城市里充斥著一股籠罩一切的噪音與快節(jié)奏,使得個(gè)體的感官印象無法得以辨別。作家雖然點(diǎn)名故事發(fā)生在首都維也納,但同時(shí)寫道這座城市的名字并無任何特殊意義,只因它同所有的大都市一樣由不規(guī)則的、混沌的、失靈的無數(shù)事件的碰撞構(gòu)成。與這種去典型性的環(huán)境描寫類似,作家用全能敘述視角推測(cè)了小說中最先浮現(xiàn)的兩個(gè)人物的名字,但隨即又否定了這一推測(cè),并通過事實(shí)證明他們并非原先推測(cè)的阿恩海姆與圖齊夫人,兩人成了無名無姓之人,同其他無名的路人一道消失在城市的角落。就連那名原本作為個(gè)體突顯在交通事故中的遇難者最終也并未被確認(rèn)名姓,繼而被無名的男性角色歸結(jié)為每年因車禍喪生的人數(shù)中的一個(gè)數(shù)字。
這一在小說開篇描寫的大眾社會(huì)成為了整個(gè)故事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在這樣的社會(huì)中不僅個(gè)體的感官認(rèn)知消弭殆盡,就連思想理念也不再專屬于個(gè)人。個(gè)體頭腦中冒出的只有被輿論和社會(huì)氛圍影響的大眾化的想法,個(gè)體的創(chuàng)造力和多樣性被牢牢禁錮在群體法則之中。
3.3 角色強(qiáng)迫
“角色”這一概念在社會(huì)學(xué)中表示“在一個(gè)特定的社會(huì)群體中與角色扮演者的身份地位相關(guān)的社會(huì)期望的集合”,是一種“由社會(huì)定義的行為模式”[5]。不同的社會(huì)地位對(duì)這一地位上的社會(huì)成員的行為方式提出要求,角色的扮演者被期待依照其角色要求思考行事,只有如此他才被接納為社會(huì)群體的一員。
對(duì)烏爾里希的角色要求在他與父親的通信中便可明了。烏爾里希的父親深諳法學(xué)界與政界的游戲規(guī)則,并利用這些規(guī)則謀取了權(quán)力和名譽(yù)。他在寫給兒子的信中嚴(yán)厲的批評(píng)了烏爾里希在社會(huì)交際中的無作為。而在另一封信中,他請(qǐng)烏爾里希在其新加入的圈子中施加影響,以便他在與同仁施翁教授的競(jìng)爭(zhēng)中占得先機(jī)。從父子的信件往來中可以看出,社會(huì)關(guān)系在小說刻畫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占據(jù)顯著地位,無論作為擁有博士頭銜的學(xué)者,或是身為平行行動(dòng)籌委會(huì)秘書,烏爾里希都被要求建立起良好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并以此作為升遷發(fā)跡的手段。
然而在烏爾里希眼里這些角色要求與他自身的人生預(yù)想并不相符,他用舞臺(tái)隱喻闡明了二者間的沖突。他將自己比喻成舞臺(tái)上的戲劇演員,想按照自己對(duì)戲劇的理解表演,但劇本上的關(guān)鍵提示詞卻不令他稱心如意。此處,關(guān)鍵提示詞暗喻對(duì)于他角色行為的普遍性社會(huì)期望,在此矛盾之下角色要求變成了剝奪個(gè)人行為意愿的角色強(qiáng)迫。烏爾里希試圖用從一切職業(yè)中解放的休假方式抵制這種強(qiáng)迫卻收效甚微,因?yàn)榭v使他可以不按照對(duì)于他的角色期望行事,但眾人依然按照普遍的社會(huì)行為準(zhǔn)則對(duì)待他并對(duì)他的行為進(jìn)行解讀和評(píng)判。例如,接受警察審問時(shí)他被明確告知他作為博士發(fā)表的論文和學(xué)術(shù)聲譽(yù)在警局里并不適用,然而當(dāng)?shù)弥母赣H為皇室效勞,烏爾里希也是伯爵的朋友時(shí),警察對(duì)他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變,開始尊稱他“博士先生”。前后對(duì)比中“博士”這一社會(huì)角色已失去了與學(xué)術(shù)成就的關(guān)聯(lián),僅僅變成了奉承的稱號(hào)。“為皇室工作”“伯爵的朋友”也不再關(guān)乎烏爾里希父親和他本人,它們代表著大眾對(duì)其角色的接受——尊貴的社會(huì)地位、特權(quán)和名譽(yù)。雖然烏爾里希一直試圖反抗角色強(qiáng)加給他的期望,可他正是得益于社會(huì)對(duì)其角色的認(rèn)可才得以安然離開警局。
如果說碎片化時(shí)代對(duì)性格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瓦解了性格的整體性和穩(wěn)固性,大眾社會(huì)與角色強(qiáng)迫的形成則更多地導(dǎo)致了性格喪失了個(gè)體的獨(dú)特性。小說中的故事雖然發(fā)生在虛構(gòu)的國(guó)度卡卡尼,但不言而喻卡卡尼王國(guó)正是二十世紀(jì)初奧匈帝國(guó)的縮影,穆齊爾筆下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深刻地反映了作家所生活的那個(gè)風(fēng)云詭譎又光怪陸離的時(shí)代。主人公烏爾里希正是看清了他所生活的時(shí)代成為了個(gè)體喪失個(gè)性的推手,才主動(dòng)選擇了作為一個(gè)沒有個(gè)性的人,與外界保持距離并以清醒的頭腦觀察、反思這個(gè)世界。他的這一舉動(dòng)既是對(duì)個(gè)性喪失的一種反抗,也賦予了個(gè)性喪失以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