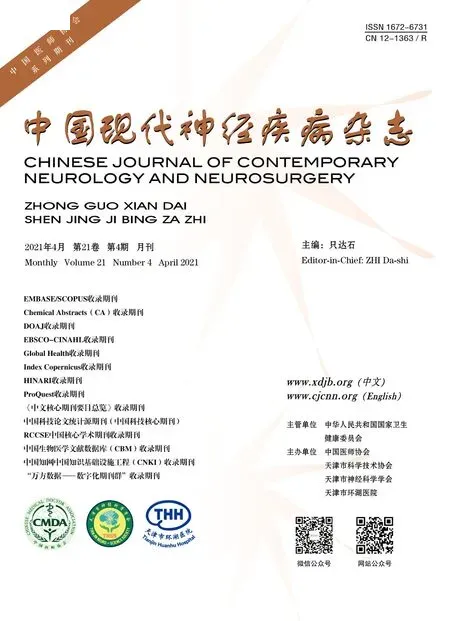神經病學和神經病理學與人腦組織庫建設的關系
王維治 王麗華
神經病學的發展曲折而漫長,自遠古時期的巫術至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體解剖學的發展,自神經病理學的起步至分子生物學技術和超微結構研究的發展,均伴隨科技的飛越,神經病學在2000余年的歷史長河中到達最輝煌的時期。人腦組織庫(以下簡稱腦庫)是利用甲醛溶液固定或冷凍人腦組織的資源庫,用于各種基于人腦組織的研究。腦庫建設對推動人腦形態與功能、發育、老化研究以及探討相關神經系統疾病發病機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將神經病學研究帶入嶄新的認知領域。本文旨在回顧神經病學發展史、神經病理學對于神經病學發展的推動作用,闡述腦庫建設對神經病學發展的意義,并探討我國腦庫建設的機遇和挑戰。
一、神經病理學是神經病學的基礎
神經病學的發展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神經病理學是其基礎。遠古時期,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近乎空白,常采用自然醫術和巫術克服和治療疾病。醫學之父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9年)認為,腦不僅與感覺有關,還是智力來源,這一觀點的提出改變了此前認為的心是靈魂、意識和思想中心的觀念,他的醫學觀點對西方醫學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1]。公元1世紀,古羅馬時代醫學家蓋倫(Galen,130-200年)從腦損傷研究角度確認了腦功能理論,被認為是人類早期神經病學發展史上的第2個偉大節點,他曾進行許多細致的動物解剖,意識到大腦與小腦的構造不同[2]。公元5~15世紀,宗教神學占據統治地位,解剖被視為禁忌,醫學再度回到巫術之中。文藝復興時期(14世紀中葉至16世紀末),人類逐漸擺脫了宗教神學的桎梏,開始對自然界進行系統觀察與思索,有一大批藝術大師對人體解剖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和畫家委羅基奧(Verrochio,1435-1488年)率先將尸體解剖應用于醫學院的教學;比利時醫師和解剖學家維薩里(Vesalius,1514-1564年)于1543年發表《人體的結構》[3],標志著人體解剖學的建立,其中有關于腦解剖結構的詳細描述;近代神經病學締造者英國醫師托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年)于1664年出版關于腦解剖和血液循環的著作——《腦解剖學》[4],奠定了神經解剖學的基礎,并于1667年出版《腦病理學》[5],成為神經病學的基本理論,這些著作對神經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年他首次采用“神經病學(Neurology)”這一說法,從而確立了神經病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6]。此后400年間的近代醫學被稱為實驗醫學時代,是醫學發展史上的嶄新一頁。18世紀,歐洲醫學家進行大量尸體解剖,從而對人體正常結構初步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病理學之父意大利病理解剖學家莫爾加尼(Morgagni,1682-1771年)于1761年出版《論疾病的位置與病因》[7],認為通過觀察解剖結構的變化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質和癥狀產生的原因,并確立“病灶(lesion)”的觀念,從而奠定病理解剖學的基礎,對醫學領域產生巨大影響[8]。
二、神經病理學是現代神經病學發展的強力助推器
19世紀是現代醫學發展的重要時期,其中現代神經病學的發展與基礎神經科學的建立與發展相伴隨。隨著顯微鏡技術的進步,神經病理學從器官病理走向細胞病理。新型儀器與工具的發明和應用,提高了診斷與治療水平,將神經病學推向嶄新的發展階段。1861年,法國外科醫師、神經病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皮埃爾·保爾·布羅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年)通過尸體解剖發現,能夠理解他人語言但不能言語的患者病變位于額下回后部,首次證實人類某一特定能力與大腦的某一特定區域相關[9]。此后20年,腦圖譜被逐漸繪制出來,并逐步探究出其與身體各部位之間的關系。1873年,意大利解剖學家、病理學家、神經學家和組織學家卡米洛·高爾基(Camillo Golgi,1844-1926年)采用硝酸銀灌入、重鉻酸鉀硬化組織的染色方法,首次觀察到完整的神經細胞及周圍相關結構,這是對神經病理學研究的劃時代貢獻[10]。19世紀末,西班牙病理學家、組織學家和神經學家圣地亞哥·拉蒙·卡哈爾(Santiago Ramóny Cajal,1852-1934年)改進高爾基染色方法并進行大量研究,提出神經系統的基本單位是單個神經細胞,至1891年將其命名為“神經元(neuron)”。臨床神經病學奠基人德國神經病學家莫里茨·海因里希·馮·龍伯格(Morits Heinrich von Romberg,1795-1873年)于1840年出版《人類神經疾病教科書》,是一本關于神經系統疾病病理學的著作。現代臨床神經病學的發展離不開讓·馬丁·夏科(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年)的貢獻,他在任職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神經病理學教授期間,發表許多關于腦、脊髓及其他的病理報告,擔任該院院長期間,相繼建立神經科病房、門診、病理學和常規實驗室并配備照相器材及其他教學設備。他以長期敏銳的洞察力仔細研究患者的臨床癥狀與體征,結合顯微鏡和尸體解剖,建立了系統的神經系統檢查方法,并開創性地對神經系統疾病進行命名和分類,被譽為神經病學之父[11]。
20世紀后葉,隨著整個醫學科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和超微結構研究的進步,現代醫學的發展進入全新時代,神經病學伴隨科技的發展也到達最輝煌的時期。英國工程師戈弗雷·紐博爾德·豪斯菲爾德(Godfrey Newbold Hounsfield,1919-2004年)發明的CT掃描儀是臨床神經病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極大地提高了神經系統疾病的診斷水平;20世紀80年代問世的首臺醫用MRI掃描儀使獲得高精確度、立體的體內結構圖像成為可能。20世紀40~60年代確定了基因的遺傳物質是DNA,1953年沃特森(Watson)和科立克(Crick)闡明了DNA的雙螺旋結構,為基因復制、表達、突變和遺傳信息傳遞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分子遺傳學的新紀元。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于1990年,參與國家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我國僅用6個月即完成了承擔的1%的人類基因組測序工作。
21世紀是“腦的世紀”,神經科學成為最活躍的研究領域。神經病理學、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從不同層面認識神經系統疾病的病因和病理學機制,干細胞技術為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提供新的方法,神經網絡及功能研究為神經康復治療帶來曙光。
三、腦庫是神經病理學和神經病學研究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腦庫是利用甲醛溶液固定或冷凍人腦組織的資源庫,可用于各種基于人腦組織的研究,如阿爾茨海默病(AD)、雙相情感障礙(BD)、肌張力障礙、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亨廷頓病(HD)、多發性硬化(MS)、帕金森病(PD)、精神分裂癥、癲、抽動穢語綜合征(TS)等[12-13]。腦庫是神經科學和神經系統疾病研究的基礎。1947年,英國神經病理學家約翰·亞瑟·尼古拉斯·科塞利斯(John Arthur Nicholas Corsellis,1915-1994年)團隊納入英國倫威爾醫院8000余例癲?、腫?、癡呆和精神病的尸檢人腦組織標本,以及1000余例健康志愿人腦組織標本,同時附有相關病例資料和病理報告,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英國倫威爾醫院腦庫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腦庫之一[14]。
盡管20世紀神經影像學的進步使得發現中樞神經系統微小病變成為可能,但仍無法取代組織病理學的作用[15]。21世紀,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神經變性病、炎癥性病變、腫瘤、精神病等腦疾病可采用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和細胞生物學等方法進一步行病理生理學研究[16]。目前已逐步建立相互補充、協作的腦庫網絡,包括歐洲腦庫聯盟(Brain Net Europe)[17]、英 國 腦 庫 聯 盟(UK Brain Bank Network)、澳大利亞腦庫聯盟(The Australian Brain Bank Network)、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神經生物樣本庫(NeuroBioBank,www.neurobiobank.nih.gov)等。2016年5月,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浙江大學醫學院等10所基礎醫學院共同成立了中國人腦組織庫協作聯盟,旨在為我國的腦科學研究提供寶貴的樣本資源和獨特的研究內容[18];2018年7月,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腦庫以神經病學為核心,以臨床醫學院的教學醫院為單位,組建了腦庫共同體[19]。
四、腦庫建設相關倫理和法律法規
腦庫建設涉及的倫理和法律問題眾多,我國的腦庫建設處于起步階段,尚缺乏明確的指示和準則。歐洲人權和生物醫學公約(Th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明確規定,每個人均有身體自主權,因此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腦組織捐獻志愿者必須對相關事宜知情同意,方能獲得道德倫理委員會的認可[20-22]。隨著神經系統疾病研究的不斷深入,腦庫建設成為神經病學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遺體、器官和組織捐獻等相關事宜的立法逐漸提上議程。2007年,我國制定首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以規范捐獻行為;201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將“參與、推動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列入法定職責;2020年5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在第二章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中對遺體和人體器官、人體組織捐獻做出明確規定,明確禁止人體買賣,隨后各地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分別出臺相應捐獻條例。2020年10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旨在促進生物技術的健康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規章制度均為腦庫建設與實施提供了法律支持,并依此制定了腦庫運行的生物安全規范以及標準化流程(待發表)。
五、我國腦庫建設的機遇與挑戰
我國腦庫建設的機遇與挑戰并存[23]。機遇主要體現在:(1)腦庫數量逐步增多。目前全國多所醫學院校的基礎和臨床醫學院均開始或已經籌備腦庫建設。(2)捐獻潛力巨大。我國神經系統疾病患者基數較大,隨著腦庫建設的推進,較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大量人腦組織的收集[24]。隨著我國遺體、器官和組織捐獻立法程序的完善、腦庫宣傳力度的增大、腦庫運行流程的逐步優化、國民觀念的轉變,未來將有更多的民眾參與腦組織的捐獻。與此同時,我國腦庫建設也面臨一些挑戰:(1)腦庫的管理歸屬性質尚未明確。神經病學成立之初,神經病理學歸屬于神經內科。由于腦組織病理結果的解讀需具備豐富的神經病學臨床知識,因此通常由神經內科醫師從事腦解剖病理學,而病理科醫師則從事腦解剖病理以外的系統解剖病理。因此,在臨床醫學系統,腦庫應歸屬于神經病學。(2)腦庫建設的流程尚未完善。既往收集的人腦組織標本均來源于臨床尸檢,近年尸檢率下降,除風俗習慣等社會因素外[25],還與臨床醫學系統尚未形成與中國紅十字會人體組織捐獻相對接的流程有關。目前,在遺體捐獻給基礎醫學院用于解剖教學、器官捐獻給臨床醫學院進行醫療救助這兩個方面已形成標準化流程[26],但組織捐獻用于醫學診斷與科研尚未形成與中國紅十字會對接的標準化流程。(3)資金支持缺乏。管理部門缺少對大體解剖病理學研究的資金支持,醫療大體解剖病理與之相匹配的司法鑒定解剖病理之間的費用標準相差達50倍,醫療機構常常為促進腦解剖病理學研究予以補貼,缺乏相應的資金支持使得這項工作難以推進。(4)腦庫建設人才短缺。腦庫建設和運行需相應的專業人才,如宣教人員、協調員、臨床神經病學醫師、解剖病理技術人員、病理診斷人員、人腦組織樣本管理人員等。因此,基于神經病學而發展起來的腦庫,應解決專業人員數量不足、入庫腦組織缺乏臨床信息、已入庫腦組織未被充分利用等問題。
神經病學各時期的發展均離不開神經解剖學和神經病理學的發展,影像學診斷技術的進步有助于發現中樞神經系統微小病變,但仍不能取代組織病理學檢查在診斷中的作用。腦庫建設對于推動人腦形態與功能、發育、老化研究以及探討相應的神經系統疾病發病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對探尋疾病新的治療方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國腦庫建設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機遇與挑戰并存,隨著相關倫理法規的完善、專業從業人員隊伍的壯大,我國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專業腦庫指日可待。
利益沖突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