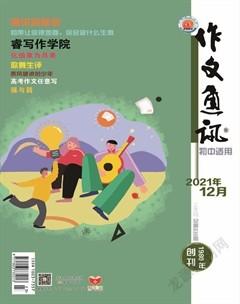寄情山水的古代文人
積雪草

千年以來,中國文化有兩條清晰明了的主線:一條是居廟堂之高,把家國重任置于肩頭;另一條是處江湖之遠,在山水游歷中體驗另一種生活狀態。
山水自然,是人類的發源地。研讀古詩詞,順著文字的脈絡依稀可見古人的足跡。南北朝時期的旅行家、山水派詩人的鼻祖謝靈運熱衷探險旅游,常縱情山水、揮灑豪情,創作了許多流傳后世的山水詩文。因為喜歡登山,謝靈運還發明了一種特制的木屐,類似于現代的登山鞋,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
謝靈運雖然在職場上不怎么靈光,卻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大咖”。他出身名門,又時常語出驚人,成語“才高八斗”便出自此公。有一次,謝靈運酒過三巡,感嘆道:“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石”和“斗”都是容量單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謝靈運的才華到底能裝幾斗不得而知,盡管聽上去有些狂妄,可他擁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粉絲這件事卻足以說明一切。這位厲害的粉絲是誰?正是詩仙李白!據說李白喜歡游山玩水,寫詩縱情,便是受了謝公的影響。
唐宋詩詞自然離不開山水的滋養,它們或磅礴豪放,或纖巧細膩;既有家國情懷的博大精深,亦有獨善其身的小巧玲瓏;有入世之抱負,也有出世之隱逸……杜甫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有卓然獨立且兼濟天下的豪情壯志;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如幽靜恬淡的夜空中灑下一縷月光,照出無限禪意;東坡先生的“大江東去,浪淘盡”,更是氣勢恢宏,豪氣沖天;柳宗元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意境如畫一般優美,一塵不染,萬籟俱寂。古代文人喜歡用自己的奇思妙想,通過文字在紙上造一座山,描幾片葉,霞光煙影,層林盡染,峰巒飛瀑,溪橋流泉……無限風光在筆端匯聚,繪成一幅幅旖旎的山水畫。

山水可寄情懷,山水可見禪意,山水可縱豪情。古人避世也好,歸隱也罷,無論是有意給自己松綁,還是無意承擔社會責任,山野林泉似乎都是最后的退路,是安放身心、涵養精神之所在。陶淵明歸隱田園,成為隱逸詩人之宗,使“南山”成為名山,同時也成為一種精神上的意象。
山水如藥,能療愈內傷,能慰藉情懷;山水闊大,能養育精神,能重塑品格。人們在山水中認識自我,重構自我,升華自我。山水文化不僅影響了古代文人,也深深地影響了古代畫家。
打開古代浩瀚的畫卷,山水畫自成一格。大多數山水畫家都流連于山水,歸隱于林泉。北宋三大家之一的范寬時常“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元代畫家黃公望更是“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筱中坐,意態忽忽,人莫測其所為”。大凡偉大的畫家,都有一種忘我的狀態———癡戀、思考、求索、癲狂……在山水中,終致抵達。
南宋畫家馬遠有一幅《寒江獨釣圖》,很有意思。闊大的畫面上,一葉小舟,一位白衣老者,身體略微前傾,坐在船頭垂釣,全神貫注地等著魚兒上鉤,一副憨態可掬的模樣。船頭略沉,船尾略翹,水紋淺淺蕩漾,空白處令人覺得江水浩渺,寒氣逼人。寥寥幾筆,功力不凡,簡潔中傳達出生命的厚度和禪意。
悠悠白云,寂寂古剎,山野林泉有神仙。這個“仙”字,是由“人”和“山”組成的。人在山中游,寄情山水,逍遙自在,可不是如神仙一般嗎?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丘一嶺,一潭一溪,都蘊藏著自然萬物的玄機。
古人風雅,以山為德,以水為性,在山水中重構自我。在這里,山水已不僅僅是山水,而是整個民族獨有的精神地標和文化溯源。古人的山水文化如一練清溪,汩汩流淌至今,滋潤后世,成為傳統文化獨有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