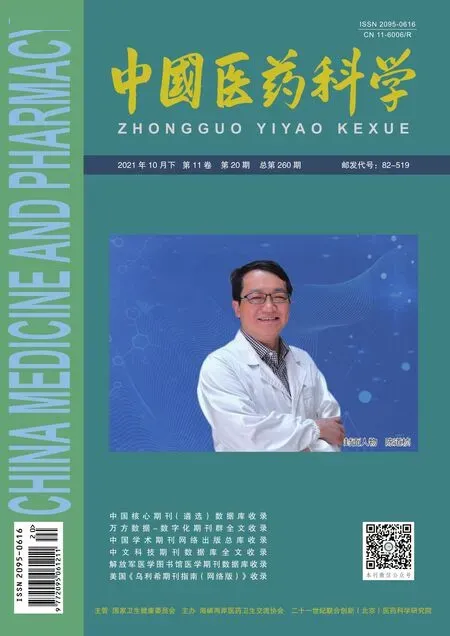子宮內膜息肉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
徐 靖 孫苗苗 張曉童 于 敏 南芳芳
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科,山東濱州 256600
子宮內膜息肉(endometrial polyps,EPs)被認為是子宮內膜間質和腺體的局部性增生,在子宮內膜表面形成無柄或有蒂的突起。EPs影響全世界7.80%~34.9%的婦女,總體流行率似乎隨著生育年齡的增長而增加[1]。雖然絕大多數EPs是無癥狀的,通過偶然的盆腔超聲診斷,可導致異常子宮出血、不孕和盆腔疼痛等癥狀。眾所周知,大多數EPs是良性的,但也有一定的惡變率,在2.73%~3.57%[1],且絕經后婦女的惡變率更高。隨著宮腔鏡技術的成熟,宮腔鏡下息肉切除術被推薦為最佳的治療方法,但術后復發率較高。現就EPs發病機制的最新研究進展予以綜述,旨在對其預防、臨床治療、防止復發、降低惡變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指導。
1 EPs的病因及發病機制
1.1 遺傳因素
既往細胞遺傳學研究表明,EPs的發生可能與染色體異常有關,是基質細胞中染色體重排的結果。近期Ding等[2]發現,苗勒氏管衍生器官的息肉可能帶有一些表觀遺傳標記,使其很容易重新編程到最早的發育階段。隨著下一代測序分析取得突破進展,Takeda等[3]發現,未經治療的EPs中致病性RAS突變的頻率高達45.7%,證明RAS突變可能在多發性EPs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1.2 雌孕激素受體失調
許多研究學者認為,EPs與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和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PR)的異常表達有關。EPs的形成可能與雌激素表達過高導致子宮內膜過度增生有關,而低孕激素狀態不能起到對抗作用致子宮內膜不能轉向分泌期,故引發EPs。Peng等[4]對絕經前婦女研究發現,與正常子宮內膜組織相比,EPs腺體中ER的表達較高,而PR的表達較低。Peres等[5]發現,EPs中ER和PR的表達均高于正常子宮內膜。Wang等[6]對絕經前患者進行宮腔鏡檢查后再放置左炔諾孕酮宮內緩釋系統治療,發現子宮內膜變薄,極大地降低了術后EPs復發的可能性。因為子宮內膜局部孕激素濃度較高,孕激素誘導子宮內膜上皮萎縮、蛻膜化和血管變化,使子宮內膜對卵巢類固醇激素失去反應。
細胞色素芳香化酶P450是催化雄激素轉化為雌激素的限速酶,類固醇生成因子1是孤兒核受體家族成員,在類固醇激素的生成中發揮著關鍵作用。Su等[7]發現,EPs中細胞色素芳香化酶P450、類固醇生成因子1的表達明顯高于鄰近的子宮內膜,證明在EPs的形成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1.3 細胞增殖與凋亡失衡
在月經周期中,有絲分裂活性和凋亡之間的平衡似乎在EPs發生發展的調控方面起一定作用。B細胞淋巴瘤2(B-cell lymphoma 2,Bcl-2)是細胞凋亡的抑制劑,而Ki-67是細胞增殖和有絲分裂活性的細胞標志物。Banas等[8]表明,EPs中Bcl-2的表達顯著高于正常子宮內膜。Peres等[5]發現,與正常子宮內膜相比,EPs中Ki-67的表達顯著升高。Adomaitien?等[9]發現,絕經后EPs的Ki-67表達高于萎縮性子宮內膜,但顯著低于絕經前良性EPs。
DNA斷裂因子40是細胞凋亡的關鍵執行因子,DNA斷裂因子45充當其抑制劑和伴侶蛋白。Banas等[8]發現,與正常子宮內膜相比,EPs的腺體層中DNA斷裂因子40、45的表達均較高,推測它們的過度表達可能在EPs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
在調節上皮增殖和分化中起重要作用的蛋白之一是p63,它也是女性生殖道基底細胞和儲備細胞的標志物。Nogueira等[10]發現,絕經后婦女EPs顯示了強p63表達,并且鄰近的子宮內膜幾乎總是p63陰性。Su等[7]研究也指出,EPs中p63的表達高于鄰近的子宮內膜和正常子宮內膜,推測p63可能與EPs的形成有關。p16是一種直接參與細胞周期的調節、抑制細胞增殖及分裂的基因。Stewart等[11]發現,基質p16染色見于所有EPs,提出基質p16免疫反應性是EPs的特征但非特異性,因為正常子宮內膜可能存在局灶性染色,這可能反應了EPs形成的發病機制。Gokmen等[12]觀察到凋亡抑制蛋白Survivin在他莫昔芬(tamoxife-n,TAM)暴露的EPs中低表達,而在其他息肉樣子宮內膜中高表達,說明TAM對細胞凋亡有直接作用的可能性。
1.4 細胞因子表達異常
Xuebing等[13]發現,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 轉 化 生 長 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TGF-β1)在EPs中的表達均顯著高于鄰近的正常子宮內膜組織。VEGF誘導血管生成,與壁厚的血管有關;TGF-β1與纖維化組織有關,是細胞外基質成分產生和沉積的最有效調節劑,兩者都是EPs的特征。然而,Zhu等[14]近期研究發現,EPs切除術后復發的女性表現出較低的TGF-β1水平。因此,目前對于TGF-β1在EPs中的表達情況日后仍需進一步研究。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是一種促進細胞增殖和抑制細胞凋亡的肽生長因子,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 1,IGFBP-1)是具有IGF-1高親和力結合的蛋白,且具有調控細胞增殖分化的作用。Elbehery等[15]發現,分泌中期IGFBP-1水平降低與EPs的存在有關,而EPs切除術后患者IGFBP-1顯著升高,這種逆轉可能解釋了EPs存在時子宮內膜容受性受損的病理生理機制。IGF-1的生物利用度由IGFBP-3調節。Doria等[16]發現,IGF-1和IGFBP-3水平的不平衡可能是EPs發生的觸發因素,并且強調了多態性在EPs發生中的重要性,IGF-1 CA(n)多態性的某些基因型具有EPs的風險比,而IGFBP-3 rs2854746多態性的部分基因型對EPs的風險具有負作用。
Rackow等[17]發現,EPs患者的子宮內膜容受性分子標志物同源框基因A10和同源框基因A11的mRNA水平顯著降低,可能影響受精卵著床降低妊娠率。
1.5 免疫、炎癥刺激
EPs的形成可能是子宮內膜局部慢性炎癥的結果。環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是一種在肥大細胞中參與前列腺素合成的限速酶,在EPs中的含量也明顯高于正常子宮內膜[18]。Pereira等[19]研究也同樣證明,并且指出其在絕經后EPs和惡變患者的水平甚至更高,但COX-2和EPs形成之間的因果關系尚未達成共識。然而,Kasap等[20]發現,COX-2的表達可能與EPs的形成無關。因此,COX-2與EPs之間的關系仍待研究。
核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是參與子宮內膜病理的轉錄因子,在許多細胞類型中都是促炎癥、促有絲分裂和抗凋亡因子。Bozkurt等[21]發現,宮腔鏡下EPs切除術后核因子NF-κB的活性顯著降低。Guo等[22]報道了EPs與慢性子宮內膜炎相關。
免疫系統的失調可能參與了EPs的形成。與非EPs的絕經前婦女相比,EPs患者的Th17反應上調和單核細胞促炎細胞因子的分泌增加,包括γ干擾素、腫瘤壞死因子、白介素(inter-leukin,IL)-17、IL-6和IL-23等,且循環CD4+T細胞中的維甲酸相關孤兒核受體C表達明顯升高,這表明了CD4+T細胞失衡與EPs的發生發展有關[14,23]。
1.6 蛋白酶的表達異常
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是依賴鋅的內肽酶,其表達受雌激素水平的影響,具有促進細胞增殖和血管生成的作用,在腫瘤侵襲和轉移中起到主要作用。Erdemoglu等[18]證明,MMP-2和MMP-9在絕經前和絕經后的EPs中均有表達,并且它們的表達可能隨著激素狀態而變化。Grzechocinska等[24]發現,MMP-2在EPs患者中高表達。然而,Peres等[5]發現,在EPs中未觀察到MMP-2或MMP-9的表達。所以,需要進一步研究以闡明MMP-2和MMP-9在子宮內膜增生的發病機制中的作用。
I型血小板結合蛋白基序的解聚蛋白樣金屬蛋白酶是一種新型鋅離子依賴性蛋白酶家族,其蛋白水解底物與女性生殖功能有關。Tokmak等[25]發現,與非EPs相比,EPs患者I型血小板結合蛋白基序的解聚蛋白樣金屬蛋白酶-9水平較低,推測其活性降低可能通過組織細胞外基質降解或增加血管生成導致EPs的形成。
1.7 他莫昔芬的使用
EPs形成的危險因素包括內源性雌激素和外源性雌激素的增加。Lee等[26]發現,接受TAM治療的絕經前婦女EPs的患病率為40.7%。TAM對乳腺組織具有抗癌作用,但對子宮內膜具有激動作用,并與增加子宮內膜異常發生率有關,包括息肉形成、增生、異型性和惡性腫瘤。
1.8 氧化應激
工業化、城市化和空氣污染加劇導致重金屬暴露增加。在人體中具有結合并激活ER的無機重金屬離子被稱為“金屬雌激素”。Y?lmaz等[27]表明,EPs患者血清中金屬雌激素水平較低,低血清鋅水平導致銅/鋅比值升高,高銅/鋅比值作為氧化應激的生物標志物,提示氧化應激在EPs的發病機制中發揮作用。然而,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有待確定。
1.9 子宮微生物群
健康女性和EPs患者的子宮內擁有豐富而獨特的微生物群。Fang等[28]發現,與健康女性相比,EPs患者的子宮微生物組存在顯著差異,表明在EPs患者中發現了子宮內菌群的改變。提示EPs可能會影響子宮內微生物組的組成,或者子宮內微生物組的變化可能是EPs的病因之一,這個潛在的關鍵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尚待探索。
2 小結
多數EPs是良性的,可發生在任何年齡段,但有一定惡變的風險。EPs的發生發展與遺傳因素、雌孕激素受體失調、細胞增殖與凋亡失衡、細胞因子表達異常、免疫炎癥刺激、某些蛋白酶的表達異常、他莫昔芬的使用、氧化應激及子宮微生物群等因素有關。隨著分子機制的深入研究,希望使其更加明確,同時應加大EPs惡變危險因素的研究,以期對降低EPs的惡變率提供理論指導。異常子宮出血、盆腔疼痛、不孕等癥狀對眾多女性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擾,并且宮腔鏡下子宮內膜息肉電切術后息肉易復發的特點對女性的生活造成了二次困擾。為提高廣大女性的生活質量,EPs發病機制的研究將更好的指導其臨床診療,預防其發生發展,而且EPs切除術后如何預防復發也將成為未來研究的重點。